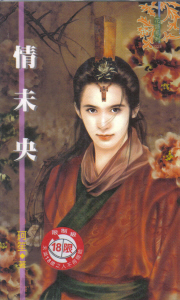清.情未央 十三党-第6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无力承受。这样不知名的恐惧,你明白吗?”
他与我并肩站着,他的目光也落在不可触及的远方。半晌,他的手垂在我肩上,他轻声说道,“馨儿,其实你很脆弱。”
我幽幽的呼吸,把头搁在他的肩上,他伸手一揽,我垂落颊边的头发丝丝缕缕的缠饶在他的手指上。“可是……在哪儿总有我。你还有我。”他在我耳边呢喃,我眼眶突然发起一阵酸热。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把所有表情堆在脸上,一定丑极了。
我牵着他的手,刚刚迈进府里的门槛,即觉得有一种凝重的气氛倏忽间袭来。“爷,不好了,不好了。”小李子神色慌张的跑过来,见我在这儿,略一踌躇,向前一顿。胤祥料知有什么得瞒着我的,示意他道:“这边说话。”我心里猛的产生一种预感,“不,小李子,你就在这儿说。”小李子咬咬牙,靠近了胤祥的身边,说了句什么,我只听见“小阿哥”三个字,心里一顿,待小李子说完,胤祥整张脸全然失却了血色,张着嘴像再合不拢了似的,眼睛突兀的睁着,我不禁皱眉,小阿哥?绶恩怎么了?!
“绶恩怎么了?”我伸手拉了下他的手指,又立即弹了回来,他的手指已冰冷如雪,僵硬如铁。我猛醒过来,“不,我去看看。”往跨院跑。他伸手要拦我,可是太迟了,我轻轻一推就脱了身,留他在后面声音哑着声音叫“馨儿”。
我怔住了,简直是晴天劈厉。我触目的是这满眼的红,满眼的鲜血。仿佛无穷无尽似的流淌了整个跑马场,也流遍了我全身上下。空气倏然间沉窒,容不得人喘息。弘吟往日骑的那匹棕色大马歪斜得倒在地上。血泊里一大一小两个身体,僵硬的停留在了生命里的最后一个姿势——弘吟蜷着身子把绶恩护在怀里,绶恩手向外伸着要抓住一线生机。弘吟手里还紧攥着马鞭,眼睛死死的闭着,小绶恩嘴巴微张着,绶恩,额娘来了,你醒过来看看我呀。
我浑身上下失了力气,止不住的哆嗦。脚底下突然一软,眼睛前面即是无尽的黑暗。“福晋”四面八方吵吵杂杂的,然后一双熟悉的臂膀托住了我。我勉力喘息着强压住那股难抑的伤痛,往后一看,他的眼睛牢牢的看向我的,他满目通红着。不,我还不能倒下去。我借助着他的力量,憋着劲儿站好。“说,这是怎么回事儿!”我的声音冰冷如铁,与此同时我的背后一阵一阵的冒着冷汗,头顶上木木的要失了知觉。胸肺里就剩下最后一丝气息在游走了。牙齿咯登咯登的乱碰在一起。
风雨来得太急,我无处躲避。然而这惨烈的一刻,上天不容我退却。
专管着跑马场的小太监唯唯诺诺的缩着头上前来,结结巴巴的道,“秉福晋的话,今儿一早,五阿哥来这儿骑马,偏这个时候,小阿哥也闯进来了。奴才们怎么哄都哄不出去,那马也奇了,平日最是温顺,今天偏就发起狂来,向着小阿哥就奔过去,提着蹄子就把小阿哥踏倒在地上。五阿哥慌了,忙勒着缰绳。谁知道这马竟把五阿哥整个儿的摔下马来,当时五阿哥就不行了,可是还把小阿哥抱在怀里,喊他。小阿哥当时本就奄奄一息了,没多久就也……没了气。侧福晋刚刚赶来只看了一眼,就昏过去了。”
我浑身筛糠似的抖起来,“你们……你们……你们把我的孩子还给我!”我气若游丝的喊完这句话,然后彻底的陷入了黑暗。天斜斜的阴着,简直像要塌下来似的。我倒在冰凉的地上,血的味道不放过我的,在我的鼻端盘旋。那是我孩子的血啊,我的两个孩子,一天之间,全没了,全没了。
我失去知觉的一瞬,全世界只剩下他惊慌的眼神。
我浸在冰凉的枯井里,暗无天日,曾经以为幸福可以在我手里停留,曾经以为在这个时代我可以过得幸福,曾经以为我可以和我爱的人无忧到白头,可是这个世界竟不留给我分毫的怜悯。只是一息之间,我成了一个可怜的丧子之母!我的儿子啊,弘吟那张脸反反复复的在我眼前出现,他厉声的质问我:“我也是你亲生的,我是你生身的骨肉啊,凭什么打我来到这个世界起就没有得到你一丝一毫的爱,为什么?我恨你,我恨你,是你这种恶毒的母亲让我生不幸福,死得痛苦!”我的眼泪刷刷的流了整个脸颊,孩子,你不要走,额娘错了,额娘把多年前的那场耻辱强加在你的身上,可是你是无辜的,你是我亲生的孩子,儿啊,你回来啊,你还没有给额娘一个赎罪的机会啊。
绶恩蹒跚着走到我的面前,睁着水亮亮的一双大眼睛,小手一拽一拽的,对我说:“额娘,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活!”
他们就站在我的面前,近在咫尺。我伸手把他们拦回来,所触之处却全是空虚,皆如空气。竟是幻觉!
他们都没了。哪怕指责也好,谩骂也好,他们都吝于给予了。水珠子一滴一滴落在我脸上,我蓦然从神志不清里醒转过来。对上他疲倦的眼睛,我无力的伸起手,抓着他同样冰凉的手指,丧子之痛是这世上最难忍受的,白发人送黑发人,叫我们怎么受得了?一个,是养了十几年并且心怀愧疚的儿子,一个是日日疼着的爱着的宝贝儿。这样的丧子之苦,只有为人父母的才明白,别人都一律不能懂。
为人父母?啊,托娅,还有托娅。我忙不迭的掀开被子,往床下跳。“馨儿。”他慌张的拦住我,他没有多说一句,而我已明白现在的他再经不起任何失去。我看着他的眼睛强笑了一下,声音嘶哑,“放心,我就是去看看托娅。弘吟这事儿,太伤人了。”
他抿着嘴唇把头点了几点,扶我下床。“托娅,她,还好么?”我有气无力的问。“已经醒过来了,就是精神还有些不济。”我点头,点头的时候却像整个脑袋牵着的疼。
东院。
门掩着,透着一丝逢隙。我轻手轻脚的凑近门边,里面尽是呜咽之声,一声比一声的凄厉,若孤雁低飞,若孤母唤子。我看了看身后的胤祥,以眼示意。他略想了想,点头。我走进去,回身把门带上。“托娅。”我一见她的样子立即勾起了心里同样的情绪,眼泪刷啦啦的流下来,走到她面前。“姐姐——”她抬起头,一双哭到红肿的眼睛悲悲切切的看着我,哽咽着唤我,正是这声呼唤让我难以自持,扑到她的床边,“哇”的放声大哭起来,与她抱头痛哭。
哭得昏天黑地,她喃喃的说:“姐姐从来不知道,弘吟没有一天把我当过他额娘。”我怔怔的不明所以,只是把头从她肩上挪下来,把手握住了她同样的冰凉。她目光空洞而又凄凉,轻轻的说:“我对他那么好,可是他心里,还是只有您一个额娘,姐姐。这个孩子是这么敏感,即便我如何瞒他,他终于还是知道了。”
“对我,只是敬。对母亲的亲近和爱,他尽数给了您。可是您不要他,他从小您就不待见他,您讨厌他,以致见不得他。”
托娅还是抓着我的手,絮絮的说:“姐姐,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您是他的生母,我不在乎我待他再好他眼里心里还是只有您一个额娘。我都可以不在乎,可是,可是,他死了……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您不要,我要啊,他是我惟一的孩子啊,可是,他死了……”
“姐姐,您知道他为什么会死吗?”托娅抬起眼睛看着我,我茫然。
“姐姐,您知道原本根本对骑马不感兴趣的弘吟为什么非要学骑马吗?”
我心里似乎明白了一星半点儿,却不愿承认,只是摇头。“那么,您总该知道是谁在那次游猎的时候对他说好好学骑术别给他阿玛丢脸的吧?”她幽幽的说,没有指责,只有心痛和疲倦。是我!是的,那次草原上游猎我亲口说的。
我顺下眼,竟不敢再看她。“姐姐,在您而言,这不值一提,可是您不懂,这是他从小长大您惟一一次算得上与他的亲近,您的话他能不做吗?这话听在他耳里简直比圣旨来得更厉害。那日以后,他没日没夜的在马背上翻上翻下,摔了一次又一次,我心疼他,我说,你别练了。这孩子那么固执,永远就一句话,‘大额娘说,让我好好学。’姐姐,您如今可有一点点的后悔,如若当初您没有让他玩儿命的学骑马,我儿子就不会死了呀!他就不会死了呀!您到底还知不知道,他是您亲生的儿子呀!”
“托娅,托娅,别这样。”我咬住嘴唇。
“姐姐,您要我怎么样呢?我知道不该怨您,我知道您心里不比我好过。可是姐姐,我……我忍不住啊。”
托娅说到这儿,终于号啕大哭起来,大口大口的喘息。我震在原地,五脏六腑都缴在一起,报应!报应!我不要那个孩子,我天天的月月的年年的不待见那个孩子,我曾经在他最初的人生里天天诅咒的那个孩子,如今他真的去了,连最后一面,都不愿让我再见。原来他不是枯草,他不是一钱不值的廉价之物,他在我心里一样是难割难舍的珍宝啊。
听到哭声,胤祥破门而入,把手足无措的我拉了出去。回身看了眼伏在床上哭得浑身颤抖的托娅,终于又把门关得严严实实的。我们渐行渐远,那哭声还萦绕耳畔,我脑子里一片浑浊,我害死了我的儿子,我害死了我的儿子!竟是我,害死了他。
无返(泪眼问花花不语)
雍正六年的春天在沉淀的悲伤里来临。这一年里,我变了,他变了,我变得少言寡语,我们多半只是静静的相对而坐,等我不自觉的怔怔垂泪的时候,他以他的指腹轻拭去我的眼泪,然后无言而去,余留一声长长的叹息。并非我们不想互相依靠着舔舐彼此的伤口,而是这伤口实在太深,以致根本不得触碰。
我也不敢再去看托娅,每看她一次,我心里就会生出更多的愧疚。弘吟的死,对她的打击,太大了。她日益苍老,我和她站一块,她倒比我显得更老几分。要知道,她才三十不到啊,可眼前的她眼角都有了密密的皱纹,脸色终日苍白,失了笑,那个永远笑盈盈的,一双眼睛像紫葡萄似的托娅,去而不复返了。
两个孩子的死,于我又何尝不是揪心之痛呢?我一点也不坚强,我是这样脆弱得经不起风雨的一个人,上天却偏要这样折磨我,丧子之痛接踵而至。而这样的精神重压下,我强撑自己必须坚强,坚强是惟一的路,我绝不能倒塌,绝不能崩溃,若有一日,我真的卸下这副重担,无所顾忌的沉湎到自己冗长的悲哀里去,他,又要怎么办呢?
碧落也死了。无声无息的,像她来得一样轻无声息。我甚至都不知道她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只是这府里伤痛太多,再多一个,也恐怕了无知觉了吧。心早就痛到了麻木,也忘却了最初撕心裂肺的刻骨铭心。连弘皎都没有太多的哀伤,对这个只伴了他两年的结发之妻,他没有掉一滴眼泪。本来么,这段姻缘是强牵在一起,原就是一段不幸,如今依旧淡然。我无心去怜悯地底下的西林觉罗碧落,因为这世上怕没有人比我更值得同情。
沉抑的下午。
我捻着两股绵线,就着灯火粘合在一起,然后眯着眼睛,就着亮光从细小的针孔里穿过去。寂静突然的被打破,亮光折进来,胤祥站在门口,身影被下午的阳光拉得很长。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惊着了,手上的针戳着了手,不由咝的吸了口气,把手指含在嘴里轻吮,血的甜腥的味道在口腔里弥散开来。
我从床沿上站起来,慢慢踱过去,脸上挂着一成不变的笑——他说,我自那件事以后,笑容开始变得虚无——我走到他身边,这才看清了他的神情,眉头紧皱着,脸上带了一种让人无法窥探的深忧,素日平和的神情此刻换上深深的惧意。我鲜少见他这样,如今一见这副神情,心里也慌了大半。“怎么了?”我已是惊弓之鸟,经不起任何波折了。
他看了我半晌,欲言又止,终于藏下脸上那副情绪,“没有,没有。”转身又要走。
这样的场景已上演了许多许多次,而每次总是他转身,我望着他远去,听着他幽幽的渐远的叹息。可是今天,我明白的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我知道一定有什么发生了,不然什么事还能让他这样慌乱。“你站住。”我赶上前,拉住他的袖子,他不可置信的回身看我,两只手拉住我的手,道,“真不敢相信你终于可以挽留。”
我低垂下头,许久,抬起头,喃喃:“到底怎么了?”他的脸上忽而又失了颜色,幽幽说道:“皇上给惠儿指了亲,蒙古喀尔喀智勇亲王丹津多尔济之子。已放了定了。”我站立不稳,不由踉跄。
他伸手要扶我,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把他的手推开,并且迅速的冲出去,“来人,我要进宫。”门边的小丫头,向门里看了一下,唯唯诺诺。我大声的说:“怎么?本福晋说话你们都当耳旁风了是不是?我说我要进宫,你们都聋了不成?”
“馨儿,不要胡闹。”他走出来,站到我面前,刚好遮住地下的我的影子。“我胡闹?”我抬头一下逮着了他的视线,“我孤家寡人一个,儿子,儿子没了。女儿,女儿也叫人夺去作公主了。可是我还是她娘,她是我的骨肉,你要我眼睁睁的看着她重蹈和亲的悲剧,作壁上观是不是?我不是你,你可以眼睁睁的看着孩子们因为你,一个个失去自由、失去幸福,成为你怡亲王的工具,成为和人结亲的木偶。你做得到,我做不到!”
我歇斯底里,声嘶力竭。明明知道,和惠成为公主,弘皎的婚姻不幸,弘吟、绶恩的猝然离世,都怪不得他。我知道他心里的痛不比我少,我知道我该安慰他,和他一起担着这份痛,然而就允许我任性这一次吧——惟一的一次。虽然我每说一句,都好像踩在自己心里似的,我用自己的伤痛伤害他,也伤害自己。却在这样□裸的伤害里,得到一种近乎疯态的快感,我朗声的笑,笑得泪流满面,笑得整个人蹲在地上蜷作一团。
“你……”他指着我。我看着他脸上阴晴莫测,看着我一席话说完,他整张脸都变成了青色。
“我什么呀?”我抬头,泪流满面,倔强的不肯低头。他的神情在倏忽间软化,蹲下身来,与我平视。“我带你进宫。”他用手轻托着我的下巴,我咬着下唇泪眼朦胧的点头。
马车上,我手和他的手交叠在一起,我轻到几乎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说:“对不起。”他的身子一僵,极不自在。我也不晓得他究竟是听见了还是没有,不过我想即便是没听见也一定能明白我的意思。刚刚在他心上划下的伤痕,还深切的存在于我的心里。他把我的手放在他粗糙的手心里。同样喃喃,“何必呢?你的心,就不会疼么?”
养心殿外。
“烦请公公通报。我有要紧事须得与皇上商量。”我面无表情。
“福晋,王爷,皇上这会子正在午休呢,不容人打扰。”
“这样……那我们……”胤祥把我往回拉。我拽开他,说道:“让我见皇上,他不能这样,不能这样。”“福晋,这……”小太监面有难色。我彻底挣脱开拉着我的胤祥,索性不管不顾的向里面大声的喊:“四哥,您还是我们的四哥吗?在馨儿的心里,一直敬您如父,无论您是谁,是从前的雍亲王,还是如今的雍正皇上,您都是四哥啊。四哥,您不能这样,您怎么可以把我的孩子作为您和亲的工具呢?难不成您从前疼她爱她都是作假的吗,就为了今天‘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把她嫁出去和亲,是不是?”
笑话。我的女儿都到了穷途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