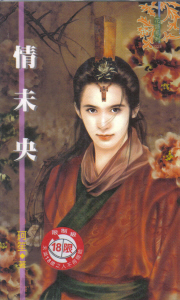清.情未央 十三党-第6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呵呵,嫂嫂若不嫌弃,那我这作妹子的来给您取一个吧?恩……不若,就叫‘荷沁’可好?”
“公主赐名,我哪有嫌弃的道理?”
几日下来,弘皎和这位荷沁小姐见面就看不对眼,依着和惠的话说,是一对冤家。和惠与荷沁倒像是一见如故,姑嫂二人感情日益好起来。终于到了和惠出嫁的日子,皇上虽说了是今后不必归牧,可出了嫁的女儿总得去夫家看看的,这一趟蒙古是去定了。而归期也是在小半年后了。
风把惠儿的衣裙吹得哗哗作响,塞布腾骑着高头大马把惠儿迎上花轿,今天的惠儿真美。人比花娇,肌肤胜雪。若在外人看来,没准儿还真的以为这是一对佳偶呢。迎亲的对伍绵延得望不到边,送嫁的人群站在两侧,甚是壮观。惠儿笑着与我拥抱,笑着和她阿玛挥手告别,笑着走到她哥哥面前,弘皎看着他的妹妹,蓦然间把她紧紧搂在怀里,不松手的喊“惠惠”、“惠惠”。惠儿从他怀里挣脱开,笑着流泪:“哥哥是成心让我嫁不了人么?”然后笑着与荷沁紧紧握手,“嫂嫂,哥哥可就拜托你啦。”
玉树以长嫂的身份把惠儿扶上去,错落间,玉树和塞布腾衣袂相触,擦间而过。塞布腾浑身僵住了,返身死死拉住她。人很多,拥在一块儿,别人也看不清楚,可是我们离得这么近,是想看不清都不行。这一个动作下来,我变了脸色,胤祥变了脸色,弘皎变了脸色,弘昌也变了脸色。
我手掩住了嘴,把惊呼声强咽回去。这像什么样?玉树已经有了四个月的身孕了,这会儿叫塞布腾拉着动弹不得,嘴里急急的说着一通蒙语,胤祥见势不好,连下去,黑着脸说了句什么,塞布腾这才松开了手,怔怔的回望了眼玉数的身影。我心里猛烈的敲打着,这个答案再明显不过了,塞布腾根本不爱惠儿。这又是一段无爱的婚姻。
我泪眼朦胧的看着马车窗口挥动着手绢的惠儿,心里无以复加的揪痛。
忧重(谁人心事谁人知)
天下没有哪个父母能对儿女的悲剧袖手旁观,更何况,谁都知道惠儿是我最疼爱的孩子,我就她这么一个女儿,对她的疼爱远远超过了对她的哥哥弟弟的,只要她开口,我恨不得把心把肺都掏给她。自惠儿嫁出去以后,我几乎夜夜都梦到我可怜的女儿瘦骨嶙峋的站在我面前,对着我泪眼婆娑。
我好像又害了小时候心绞痛的毛病,每天夜里醒过来心里那一块固定的地方都锥锥的痛。难道说,每个孩子都会在母亲的心里占据一块固定的地方,每每孩子陷入苦痛与不幸时,那专属于她的那个角落就会千百倍于她原本的伤痛而疼不可抑么?
我从梦里哭醒,然后再在他的怀里哭着睡着,再肿着眼睛第二天醒过来。不出一个月,我已瘦了一大圈下去了。他忧心忡忡的看着我,每日叫人不是给我炖鸡汤就是喝参茶的进补,可是谁都知道,心里的伤是最难医的。我想,我怕是要害了忧郁症了。可是每个人在精神彻底崩溃之前总还有一丝不舍和顾忌,我必须抓住我仅存的理性来继续我艰难的人生,为了陪在他左右。
雍正六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波折轮番的滚过来,足让人措手不及,伤痛也在这样的年月里在心里溃烂,无法愈合了。玉树生了个儿子,取名永喧,说起来算是胤祥的长孙,可是在这种悲伤漫天的气氛里怎样的欢喜都无法掩盖它原本的阴郁。
托娅到底是个坚忍的女人,用足一年的时间才总算从丧子之痛里缓过来,做回了我过去的可亲的妹妹。可是我却总觉得她重回脸上的笑意较之原先是那样的虚无了。她紫葡萄一样的眼睛再也回不来了,如今对着我的这双眸子就像是一口深井,落下去一粒石子,也总会波澜不惊的湮没。
忆秋往我们这府里跑得越发得勤了,这个我亲眼看着长大的大女儿,终于在这一天成了我有力的依靠。可是,她毕竟也有她自己的小家,她有她自己的喜怒,她有她自己的孩子。忆秋这个孩子,生了两个女儿之后原是又怀了个男胎的,可那时候正好我们府上她两个小弟弟同时殁了的噩耗一到,悲伤过度,落了胎。打那以后再没有消息了。岁月在她的脸上逐渐刻下痕记,教会她在悲痛面前学着了隐忍。生活就是一道道的槛儿,你说你遥遥望着总说跨不过去,可真临了头,除了跨过去外,又有什么旁的法子呢?
这么脆弱的际遇,就像是只要再多一个槛儿就能让人立马疯了去。可是上天丝毫不懂怜悯,在弘暾和映雨婚期在即的时候,弘暾突然一病不起。府里上上下下的全慌了,就怕这府里再留不住什么。我也格外紧张起来,我坐在弘暾弥散着药味的屋子里,看着映雨倔强的固执的坚持,侧跪在弘暾床边上,给他一勺一勺的喂药,我看着这样的场景,拼命的咬着牙眨眼睛才把泪意强忍回去。
“额娘。”映雨喂完最后一滴药,给弘暾细心的垫好一个靠垫以后,转过来对着我。自弘暾病后,映雨一日不离的守在他床边,换汤喂药皆不假手于人。本来就纤弱的人更是瘦了一大圈,在看床上的弘暾,脸已经白得失了血色,嘴唇甚至乍一看都是紫的。“他好一点了么?”我压低了声音问映雨。
映雨转了转眼睛,还是忍不住教眼泪刷刷的淌了下来。“还是不行。吃东西都吃不进去了,吃了过一会儿又会吐出来,我、我都不忍心,看着他那副样子,他好好的一个人给这病折磨得还像人样吗?他每次当着我面再难受都把吃的东西咽下去,怕我伤心,他连吐都不在我面前吐。”
“映雨,别说了,别得招大额娘担心。”床上的弘暾气若游丝的说,只这一句,说完都得喘上好几口。我眉头皱得紧紧的,前几日还是一个俊朗的翩翩少年不到几日就病成了这副样子。弘暾得的这个病,叫绞肠痧。会没完没了的肚子疼,一疼起来就会要人命,大汗淋漓痛不欲生。不能进食,每每一进食又会犯病。只能靠流食勉强维持生命。
我不忍再在这儿呆下去,一闭眼睛,几乎忍不住话里的颤音,说道:“好吧,快快的好起来,额娘还等着你们办喜事。”转身看见桌案上映雨抄的整整齐齐的《金刚经》:
第一品 法会因由分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
第二品 善现启请分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
……
一页又一页,一张又一张。不知道神灵在天上可看到这是一个少女凄凄切切的,最后一丝希冀。在这个风雨漂泊的湍急的河流里,她是可怜的扁舟,在风雨飘摇里,没有什么可以抓住的依靠,只剩下最后的对上天的恳求。
我寂静的转身,一个小人怔怔的站在门口。“甘珠儿,你怎么在这儿?”我疲倦的问。“额娘。”七岁的甘珠儿已不像从前不谙世事的淘气了,我很抱歉,在这个孩子的童年里,我除了让他看到兄长的离去、漫天的眼泪外,再没有什么瑰丽的色彩可以留给他的记忆。可是如今的我也不免疑惑,生在这个家里的孩子真的有幸福可言么?童年的幸福可以绵延一生么?又或者,真正在人生日后的风雨里,童年无忧的幸福才是极大的讽刺,丢给他们一个无可挽回的创痛。
我压下疲态,蹲下身来,拍拍他的小脸,“甘珠儿,不要到这儿来吵你二哥哥,跟额娘走吧。”“额娘。”他叫住我,我停下来看他。“额娘,你看。”他打开攥得紧紧的小手,一个小玉牌出现在我眼底。
“这、这是怎么来的?”我拿起来,仔细的端详,迎着光亮,很是晶莹剔透。可是一看懂上面复杂的字样,我立即变了脸色,那上面正反八个字:生死有命,不可强求。我浑身打起颤来,一叠声的追问,“哪儿来的?哪儿来的?”
甘珠儿让我吓怕了,向后瑟缩了一下。我平下气息来尽力哄他,“乖,告诉额娘,这是打哪儿来的?”
“是……是我刚刚偷跑到西门去,一个化缘的和尚给我的,问我我们府有没有病人,我说‘有啊,我二哥。’那和尚就把这给了我,我想打发小厮给他银钱,他却走得见影了。我只识得上面有什么‘生’啊‘死’的,别的都不认得了。”我把那块玉牌攥在手里,像握着一块烫手的山芋。“扔了,扔了。”我气息纷乱。“额娘,你说什么?”
“扔了,我叫你扔了!”我大声的喊,甘珠儿让我吓得一顿。
生死有命,不可强求……生死有命,不可强求……生死有命,不可强求……难道这是注定了的无法逃过的劫?难道是刻在血管里和血液一起流淌的封印?
时隔半年,我日盼夜盼的和惠终于回来了。她站在我的面前,穿着一身轻飘飘的衣裙,喊了声“额娘”然后扑到我怀里来,嫁了人的惠儿更添了成熟的风韵。可是我知道她并不幸福,你看看这还是我养尊处优的小公主吗?骨瘦如柴,面色苍白,和我说上三句话就要喘上好一阵子,脸上浮起的红晕犹若画上去的,在万里雪地里独绽一支梅。
我心疼的把她抱在怀里,抚摸她苍白的脸颊,眼泪忍不住的滴落在她乌亮亮的头发上。“怎么瘦成这样?”我问她。“额娘别担心我,大约是在蒙古水土不服的缘故。阿玛,你说是不是?”和惠抬起头,问坐在她正对面的胤祥。我随着她的目光望过去,打从和惠一进来,他的表情就变成了一副木偶似的一动不动,眉头紧锁着,拳头紧紧攥着。任谁都不能接受,自己最钟爱的女儿,在短短半年之内,因为生活和婚姻的不幸变得骨瘦如柴。我们美丽漂亮、生动可爱的小女儿,在一切苦难和不幸的重压下,终于日益憔悴,和从前美丽的日子一起,再不复返了。
我吸吸鼻子,强作欢笑,“这个丫头自找罪受,水土不服还在蒙古待那么长时间?以后说什么额娘也不让你再去了,你皇阿玛把你的公主府建好了,日后就在京里,隔三五天就回娘家来看看阿玛额娘,听见没有?额娘可不想再见到这副鬼样子了,额娘要把我的惠儿再养回从前那样白白胖胖的,像小时候小手肉嘟嘟的,全是肉,让人看了就想咬。”我在她身上假意拍打了一下。惠儿也陪我一起强掩欢笑,瘪着嘴“哟”的痛叫一声。我把她搂得紧紧的,笑得眼泪直流,笑得嘴角发酸,笑得脸上僵硬到再不能把这个笑强装下去。
缘错(黄土垄中卿薄命)
荷沁怀孕了,我心里渐渐松了一口气。虽然表面上看过去弘皎和荷沁是一对冤家,可是舒巧的悲剧是不会再重演的了。和惠很高兴的拉着荷沁问长问短,把手放在荷沁未显怀的肚子上,嘻笑打趣。与和惠正相反的是,弘皎自从和惠回家以后就异常的沉默,见了和惠也再不多言,甚至在和惠的面前都有一种仓皇而逃的感觉。和惠拧着眉站在风里,怔怔的看着他的背影,然后也向相反的方向远去。
我每日亲自熬药,把大半天都泡在厨房里捣鼓药。这日晚上,我从房间里出来,把配好的药抓到小厨房去,一样一样摆开来,搬个马扎,手里拿一把蒲扇扇火。药味儿从吊子里飘出来,呛得我直咳。这药味儿又苦又怪,简直是难以下咽。可我偏要受足了这药的苦,大概是在心里全一个“同甘苦,共患难”的想头吧。
我端着熬成的一小碗药,从厨房里走出去,远远见一个影子在天井里坐着,头向着头上仰望,那个纤纤身影我是再熟悉不过的,是惠儿。我把药碗放在小石桌上,蹑手蹑脚的走过去。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细思量……”风嗖嗖的从身边一吹,我看着眼前这个场景居然大夏天的打了个哆嗦:和惠头上戴着个白色的发钗,身上穿一件白裙子,全身一动不动的,眼睛直直盯着天上一轮残月,嘴里颠三倒四的就只是这么几句,颠来倒去的说,然后念得低低的笑,再吃吃的哭。
我刷的一下扑过去,蹲在她面前。“惠儿啊,别吓额娘啊,你这是怎么了?”
我这才看清惠儿脸上满脸的泪,她见了我慌张的在脸上抹了两把,道:“没什么,额娘。只是突生伤感罢了,女儿的性子额娘是知道的,就是有那么点儿多愁善感,倒吓着额娘了,罪过罪过。”我又怕又恼的拍打她的肩膀,真的生了气:“惠儿,你是要吓死额娘才算完啊?”
“额娘,额娘,我错了。”惠儿像个做错事的小孩子,瘪着嘴从椅子上站起来立在我面前。我放柔了语气,“惠儿,以后,可不兴再这样了。这种伤春悲秋的句子,日后不许再念。以后这身衣服,这个发簪也都不许再戴,听见没?”
“惠儿遵命。”和惠俏皮的一吐舌头,我知道她在我面前刻意做个轻松的样子,也就不点破这一层。在她身边的石凳上坐下来,幽幽的说:“塞布腾对你好么?”
和惠害羞似的扑倒我的怀里,双手揽着我的腰,把脸埋在我身上。“额娘怎么问我这种问题嘛,怪羞人的。”“这有什么?给额娘放个话,就咱母女俩知道,连你阿玛都不告诉,好不好?”
“母女俩大半夜的不睡觉这是说什么悄悄话呢,还得瞒着我?”门口一个声音蓦然响起来,我“哟”了一声,“你怎么出来了?瞧我这记性,光顾着惠儿了,把药都忘了,你赶紧趁它还没冷喝了吧,我给摆那外面桌子上了。”他略跛的走过来,浑不在意的摆摆手,“惠儿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
“阿玛,在蒙古草原上我就养成这么个怪习惯,天天夜里盯着月亮看,您看它真是个神奇的东西,一会儿圆了,一会儿又缺了,看着看着就觉得连人生都参透了似的。”惠儿撒娇似的跟胤祥说话。
胤祥还像看小孩子似的包容的看着她,“哟,咱惠儿这是什么话?看月亮还能当饭吃不成?怪不得人瘦成了这副样子。”走过去拍拍惠儿的肩膀,“丫头,回去睡吧。”
惠儿乖巧的点点头,向我们一福,转身就绕过墙边不见了。
“我宁愿她都说出了。她这样心里憋着,表面上还得做出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来我看着都心疼,当心憋坏了。”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就是睡不着。
“你消停会儿成不成?”他握住我的手,“看今天晚上这样子,八成是我们过虑了也有可能。惠儿还是咱们无忧无虑的惠儿嘛,能说能笑的。左不过是承了你的性子,有点多愁善感罢了,女孩子在这个年纪都带着点这样的性格,日后为人母了自然就好了。你这么没完没了的操心,她没事,你倒该生病了。”
他到底不是当娘的,惠儿骗得了他,可是骗不了我。我说,“你晓得什么,你是没瞧见她之前……”我说到这儿突然噎住,我能说什么呢?我告诉他,我看到惠儿一个人疯疯傻傻的对着月亮说胡话?不不不,这重烦恼压在我一个人心里就够了,我瘪瘪嘴,把话又咽了下去。他听我话说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