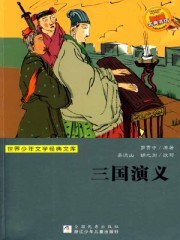新批判主义-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失去了任何人类客观正义和普遍道德的标准,唯一地把我们的思维固着于压迫…翻身、复辟…反复辟、隐藏…揭露、斗争…反扑、警惕…松懈、压制…打倒这样一些杀红了眼的政治策略之上,我们习惯于把任何事情,包括学术观点和艺术倾向,都上纲上线到与假想中的“阶级敌人”的一场战争。我们已经不会客观地看待一件事情本身,而只会思量它对我(或“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权力效应,是使我们受压还是翻身。这种流毒至今没有肃清,它甚至渗透进一些接受过西方启蒙精神薰染的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思想深处,作为一种隐藏在血液中的基因而在潜意识中支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就曾反对将他们的学说所发现的规律解释成恶意的预谋,《反杜林论》中花了很长篇的篇幅批判杜林用“暴力论”来解释经济事实的做法,他们更强调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客观发展趋势。而中国传统的道德历史观和对人际关系的“诛心之论”,使我们把人对人的控制直到对人心的控制视为日常生存的基础。在中国,官与民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即使只有三个人,也要设一个“小组长”来管理下级并对上级负责,形成几乎“全民皆官(管)”的“人盯人”的局面。稍微有点文化、识几个字的人,都在自己的自然生命之外,还附加了一条“政治生命”,它往往比自然生命更加重要。中国人的这种全民从上到下的政治化、权力化和霸权化今天几乎已经成为一个举世皆知的事实,以至于中国文学在世界上通常都被当作政治诠释的作品,而没有人当成真正的文学作品来欣赏。就连科学研究,一段时期也被我们当成了“阶级斗争”和权力斗争的战场。虽然最近二十多年来我们在各方面做了很多“拨乱反正”的工作,但这种霸权思维模式仍然在暗中限制着我们对文学、历史和哲学等等问题的思考。
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许多做思想研究的人对于外来思想的“霸权主义”如此敏感了。我们从来就没有客观冷静地看待外来文化,而是毫无例外地把它们视为一种“文化侵略”。我们对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的解读就是侵略和反侵略、殖民地化和反殖民地化的历史,这种两分法的对立观念从小学开始就被灌输进我们的孩子们头脑里,就像文革时期五年级小学生黄帅自发地喊出:“我是中国人,不学外国文!”这样的口号。虽然今天不学外国文(主要是占据霸权地位的英文)已经不被看作是有文化的中国人了,但霸权心态却在这样教育出来的中国人心目中仍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基本情结。吊诡的是,霸权心态的另一面就是奴才心态,只有奴才心态的人才最关心谁有霸权,谁是霸主,才最羡慕握有霸权的主子。所以,奴才心态的人只要有一丁点儿可能性,就想要充当一回霸主。例如,我们中国一百年来在军事上、政治上尝尽了被人欺压的苦果,不得不承认人家的霸权,但在文化上、精神上我们似乎还有可能反败为胜。于是,无数的文人为此趋之若鹜,孜孜矻矻地在这上面建构起自己排他的“尊严”,如果不能胜过人家,就觉得自己在别人面前“矮了一截”。我们就是不能用客观冷静的眼光看待中外一切学术,因为我们缺乏超验正义和超验真理的观念,我们认为那些观念都是西方来的骗人的鬼话,我们的文化人格不是建立在平等交往的法则上的,而是建立在霸权优势之上的。不当霸主,就会沦为奴才,这是我们从小就被教育的思维模式(“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而在国际交流和文化对话日益频繁的今天,这种心态只能使我们变得妄自尊大、气量狭小和猥琐不堪。
所以,我认为虽然所谓霸权主义在中西文化的传统中都有其深厚的根源,但把霸权思维当作唯一可能的思维方式,而缺乏超越霸权思维的更高价值维度,这却是中国传统思维相对于西方思维方式的一贯特色。当代西方某些国家尽管凭借强大的军事武力而取得了国际关系中的霸权地位,但他们使用这种霸权时毕竟还顾及到普遍正义和公理的要求,至少必须打着这种意识形态旗号,而不敢公然违反人类共同价值的普遍标准而诉诸赤裸裸的武力,这应当看作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结束以后的时代的进步。相反,我们今天如果不借用西方人所创造出来的这些普世价值标准,我们就几乎没有谴责他们的霸权主义的正当理由,顶多只能批评他们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并力图通过使自己变大变强来使对方不敢欺凌自己,这就还只是一种霸权思维。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大小强弱的差别而没有普世正义,那么我们对恐怖分子也就用不着加以谴责了,因为他们难道不正是“弱小者”吗?他们只不过是运用同一个霸权思维而在小范围内造成了以强凌弱的局面而已。我们今天能够以“人权”标准来谴责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恐怖分子的卑劣行径,正表明我们无形中已经接受了西方近代以来的普世价值,这恐怕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
然而,知识界一些人至今还深陷于这样一种糊涂观念中,即认为西方普世价值其实并不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性,而只是“西方成年白种人”在西方中心论的文化背景中为自己的强权捏造出来的虚假借口,他们以这种方式来欺凌和压榨弱小民族,所以我们在反对他们的霸权主义的同时也要揭穿他们的这套观念的虚伪性。这种看法表面上很符合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同时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谋而合。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种心态后面的文化心理,就会发现他们不过是中国传统“战国策”式的思维方式在现代的延续。这种思维方式看起来似乎可以把握事情的本质,实际上暴露了传统思维模式的狭隘性。当今世界早已不是二战时期的世界,否则两个超级大国的核武器恐怕已经把地球毁灭了不止一次了。今天即使有文明的冲突,也不是在几百年前的水平上进行,而是在普遍人权的底线上进行,不然美国也不可能花大量的美元去研制“精确制导”以避免伤及对方的无辜平民,而恐怖分子也不可能受到全球大多数人类的同声谴责了。实际上,恐怖分子之所以滋生,也正是打的西方文化的“人权”牌,如果西方国家根本不尊重人权,或者只是虚伪地尊重人权,则恐怖分子就失去要挟的武器了。这甚至也从反面说明,从历史发展的前景看,人类普世价值将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取得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单纯军事霸权将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只有在这一前提下,各个不同的国家、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关系才有希望逐步摆脱赤裸裸的霸权主义而走向对话和宽容。但首先必须具备的条件是,这些民族、文化和国家的知识分子作为先知先觉者,要能够充分理解和接受人类普世价值,抑制盲目排外的情绪化陷阱,走出传统霸权思维的桎梏,以开放的、平和的心态面对事情本身。
具体言之,中国知识分子在今天特别要把西方强势文化中的霸权主义因素和其中的普世价值因素区别开来,警惕文化保守主义利用民众的无知和盲目情绪而对一切西方思想加以排斥。我们对于中华民族在上个世纪由于西方列强的霸权主义所遭受的深重苦难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但是对于由我们自己的封闭和愚昧而造成的苦难,我们却反思得远远不够。而在今天,当我们国力有所增强,国际地位有所提高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好了疮疤忘了痛”,又开始妄自尊大起来。最为可悲的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中也开始流行一种政客眼光,即用一种怀疑和反感的态度来对待西方优秀的文化成果,以“文化霸权”为由否定其普世性。一百多年来的西学东渐并没有使我们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层,而只是断断续续地在表层上滑来滑去,而现在竟然有许多人已经大不耐烦了,觉得在西方的“话语霸权”之下充当追随者有损于自己的民族尊严。这些人中有不少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持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恰好相反,当初正是他们卖力地把西方最新时髦的理论和学说引进国内来,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西学热”。但由于他们引进西学的态度仍然是霸权思维的态度,他们以为自己掌握了西方话语就是掌握了“话语霸权”,所以一旦时尚改变,他们预计“国学”将上升为更具霸权性的话语,这些人马上改弦易辙,转而依托传统的话语来谋求话语霸权,觉得这样做似乎更踏实、更有低气。然而,平心而论,不论是西方的科学话语还是西方的人文话语,人家并没有拿枪逼着你们接受他们的东西,当初是你们哭着喊着跟随人家的最新时髦亦步亦趋,生怕落后一步就抢不到话筒。许多人写汉语文章一个中文注释都没有,全是密密麻麻的外文注释,不就是为了吓唬中国人吗?这种话语霸权不正是这些中国人造成的吗?他们靠这个升了职称,获得了学术地位,现在反过来批评“西方话语霸权”,其他人也跟着起哄,仿佛自己多么爱国似的,也太取巧了吧?
应当说,就“话语”而言,西方话语是当今世界上最不具有霸权性质的一种话语。虽然这种话语自认为具有普世性,但却并不强加于人,而是主张宽容,并且认为这种宽容正是其普世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这只是就主流和本质的方面而言的,并不排除在某些场合下也被某些人利用来达到霸权主义的目的。但西方文化发展到今天,已经展示出它有充分的思想资源来消除人类的互相隔阂,营造不同文化间对话的语境。自由、平等、博爱、科学、理性、民主、法制、人权等等,这些不仅仅是西方人几百年来所追求的,而且也是中国人一旦了解到也必然会梦寐以求的。虽然任何价值都有可以进一步质疑之处,但只有一种价值能够为这种不断质疑提供基本的话语平台,这就是西方言论自由和人权的价值,如果对此也加以质疑则无异于思想自杀。这种道理并不需要很高深的理论修养和很聪明的头脑,只要我们抛开固有的情绪化的成见,冷静地看待西方文化中那些并非西方社会所独占的价值,就足以理解到了。比如,我们有些人大力批判西方的“理性主义”或“理性霸权”,就是一种荒谬的论点。西方后现代对他们固有的理性主义传统加以批判的审查,固然具有完善这个传统并弥补其不足的作用,但中国人身处一个非理性的文化传统中,对“西方来的”理性主义也视若仇寇,称之为“西方话语霸权”,这就不仅仅是缺乏思维能力的问题了。这种说法颠倒了“霸权”一词的本义:霸权本来意谓着不讲道理、全凭武力和威慑进行统治,现在讲道理竟然也成了“霸权”的一种,难道反对霸权就是反对讲道理吗?这不是一种更强横的霸权思维吗?真正反对霸权的人至少必须让人家讲清道理吧?至少必须听听人家讲的有没有道理吧?西方理性主义当然有其片面性,但它至少给人们通过对话克服各种片面性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否则我们只能把自己封闭在自身中,倒退回一个如同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像狼一样”的不可通约的世界。如果说这种封闭性的要求也是一种“反霸权”的姿态,那么这种反霸权恰好本身就是最极端的霸权姿态,它是肯定一般霸权原则并导致人类永远处于霸权主义盛行的时代的,而近五十年来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超越霸权主义的全球共识(如互利原则、对话原则、谈判原则、理性原则)必将毁于一旦。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在反对西方霸权主义时要注意,不要把这种反霸权变成自己追求霸权的手段,同时不要把那些并非依仗暴力强加于人的思想观念、文化内涵、价值标准都当作自己反霸权的对象,凡是这样反对霸权的人,自己就是霸权主义的忠实信徒。
苏格拉底与孔子的言说方式比较
我在《论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一文①中曾说过:〃中国哲学对语言的追索可以说是一开始就自觉到了的;但也是一开始就采取了蔑视语言本身或使语言为政治服务的态度;从未把语言当作人与世界本体之间的必经中介;更谈不上将语言本身及其逻辑当作本体和客观规律了。〃为了进一步展开这一观点并说明其意义;我想在此以孔子的《论语》为例;将它与古希腊苏格拉底的言说方式作一对比。苏格拉底常被誉为〃西方的孔子〃;而且与孔子一样;也没有留下自己亲自撰写的著作;而只有由弟子们所记述的言论;在孔子;这是由于他〃述而不作〃;在苏格拉底则是由于;他认为自己的使命是通过谈话启发人们去关心和思考真理;追求智慧;两人都以口头对话的形式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且都把关注的重点集中于伦理道德问题;但他们不论是在伦理道德的内容还是在对话的方式上都有极大的区别。本文拟只就他们对话的言说方式来作一比较。
一、言说的标准问题
任何言说;如果要人有所获的话;都必须要有标准。孔子和苏格拉底可说是中西方传统言说标准的确立者。然而;苏格拉底把言说的标准最终确立于言说本身;孔子则把言说标准放在言说之外;从而最终取消了言说的标准。
拿苏格拉底的一篇著名的讨论美德的对话《美诺篇》来说;苏格拉底在与美诺的讨论中总结出了这样一条规则:〃一条原则如果有某种正确性;它不应该只是此刻;而应该永远是站得稳的〃②。如何才能〃永远站得稳〃呢?苏格拉底主张;应当抛弃〃任何一个用未经解释或未经承认的名辞来说明的答案〃③口例如〃美德〃;如果我们要谈论它;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美德?〃而不是〃美德是否可教?〃(或〃美德是如何样的?〃)因为;〃当我对任何东西;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如何能知道它的‘如何'呢?如果我对美诺什么都不知道;那么我怎么能说他是漂亮的还是不漂亮的;是富有的而且高贵的;还是不富有不高贵的呢?〃④也就是说;苏格拉底非常注重言说本身的逻辑层次;在言说中所使用的任何概念都必须建立在这概念的明确和严格的〃定义〃之上;否则一切描述都无以生根。这种要求是言说本身的要求;而与所言说的对象或内容无关。就是说;即使你言说的内容再好;如果不遵守这一原则;只会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出来的是什么;或者是陷入自相矛盾;这正是美诺在与苏格拉底讨论时语无伦次、处处被动的原因。苏格拉底提出的这一原则;也是后来亚里士多德建立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不矛盾律、并将〃实体〃作为最基本的〃是〃本身(即〃作为有的有〃)置于言说的首要地位的根据。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一形式逻辑的原则同时也是本体论的原则;或者说;言说的原则就是存在的原则;什么东西是最基本的存在;什么东西就是最根本的言说:苏格拉底虽未进到这一层;但他为言说规则的〃本体论化〃即客观化提供了前提;在他那里;言说的规则是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的客观规则;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
所以;当美诺回答苏格拉底〃什么是美德〃的问题说;美德就是男人懂得治理国家;女人善于管理家务等等时;苏格拉底讽刺他说:〃当我只问你一种美德时;你就把你所留着的一窝美德都给端出来了〃;并开导他道:美德〃不论它们有多少种;而且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本性;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