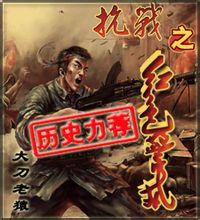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勤务》两本教材,讲述了游击战术。这样,当朱德和毛泽东会师时,也就一起切磋起游击战术。
一九二八年五月中旬,毛泽东在前委扩大会议上作战略报告时,正式提出了“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信》,第一次用文字表达了他的一整套游击战术: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跟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战术,大要说来,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这种战术的。如此这般,毛泽东从“军旅之事,未知学也”到朱聋子的“打圈”秘诀,从“十六字诀”到一整套游击战术,逐渐成了一位军事家。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打败江西两只羊”
朱毛会师,江西震动,南京震动。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日,蒋介石电令湘粤赣三省政府,“克日会剿朱毛”。三省政府接蒋介石命令,未敢怠慢:湖南派出李朝芳率一师兵马,向成杰率一师兵马;粤军由范石生、胡凤章各率一师;江西呢,派出了“两只羊”,即杨如轩、杨池生这两“杨”,各率一师兵马,参加“会剿”。内中,江西的“两只羊”,成了毛泽东反“会剿”的重点。毛泽东提出,对湘军、粤军采取守势,对赣军采取攻势。
杨如轩是云南人,在云南讲武堂受过训练。他在滇军中当过团长、旅长。一九二八年,他在江西担任二十七师师长兼赣东警备司令。
杨如轩率部扑向井冈山北端的永新县城。红军来了个“敌进我退”,把县城让给了杨如轩。当时,杨如轩手下有四个团。红军放弃了县城,且战且退,诱使杨如轩的两个团出城追赶,越追越远,城里只剩下两个团。这时,红军主力急行军,逼近永新县城西面的浬田。杨如轩听到报告,以为是从湖南败退的红军,派出一个团迎战。这样,县城里只剩一个团。杨如轩很得意,坐在县城里听留声机,以为红军不堪一击。忽地有人报告,西边的红军在向县城进军。杨如轩摆摆手说:“没有事,我已经派了一个团——七十九团去了。”过了一会儿,又有人前来报告,说在城西发现红军。杨如轩听留声机正出神,把来报告的人骂了一通。于是,下边的人不敢再报告。红军越来越近,进攻县城。直至一颗流弹打到杨如轩师部的屋脊瓦片上,杨如轩这才大吃一惊,扔下留声机,连忙逃命。原来,杨如轩派往浬田的七十九团,跟红军主力一交战,才一个小时就被消灭掉了,团长毙命。红军急速朝县城推进。杨如轩在卫兵的簇拥下来到城门口,那里挤满了逃跑的士兵和县城里的土豪们。杨如轩急不可耐,从城墙上往下跳,受了伤……“一只羊”被打得如此狼狈,抱头鼠窜,被红军传为笑谈。杨如轩带领残兵败将,联合另一只“羊”——杨池生,决心与红军再决雌雄。
杨池生也是云南人,也曾在云南讲武堂受训,在滇军中当过营长、团长、旅长、师长。此时,担任湘赣两省“会剿”井冈山前线总指挥。当杨池生在云南讲武堂受训时,朱德正在那里任军事教官,不仅认识杨池生,而且杨池生部队里不少军官也曾是朱德的学生或下属。“两只羊”依然朝永新县城扑来。红军还是“敌进我退”,放弃了永新县城。朱德亲自指挥战斗。红军又一次且战且退,敌军出城追击。红军退至龙源口,利用有利地形反击,激战一天,一下子全歼敌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红军乘胜追击,又重新夺回永新县城。在激战中,杨池生负了重伤。从此,“两只羊”一蹶不振。杨如轩被调往南京,在参议院中当参议去了。杨池生则到吉安养伤,后来也调往南京军事委员会当参事。
一首歌谣,在红军中传开:
朱毛会师井冈山,
率领工农打胜仗,
不费红军三分力,
打败江西两只羊。
“两只羊”的惨败,使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在红军中得到了拥护。红军打败了赣军,湘军和粤军也就望而生畏,不战而退,蒋介石发动的对井冈山的第一次“会剿”,就这样收场了。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永新一枝花”贺子珍 1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一天,袁文才摆了一桌酒席,请了红军的几位首脑。来者心照不宣,频频向毛泽东敬酒贺喜。那酒杯敬向毛泽东,也敬向毛泽东之侧的一位白净姣美而目光刚毅的姑娘。那姑娘是永新城里一朵出众的鲜花,人称“永新一枝花”,名叫贺子珍,年方十八,瓜子脸,乌亮的眼睛,光彩照人。
贺家原本祖居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世代务农。到了贺子珍曾祖父这一辈,有了些积蓄,买下二百来亩油茶林和二十亩土地。家中富裕起来,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也就上了私塾,识字知书,成了读书人。那时,可以花钱买官。有了钱,贺焕文想当官,也就捐了个江西省安福县知县。贺焕文的前妻叫欧阳氏,生一子,名贺敏萱。
欧阳氏去世后,贺焕文娶广东姑娘温土秀据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为“杜秀”。但中共永新县党史办公室提供的资料称“温土秀”。为续弦。温土秀长得俏丽,原是广东梅县一户大家的闺秀,因其父遭厄运,不得不随父迁往永新。温土秀生三子三女:三子为贺敏学、贺敏仁、贺敏振,三女为贺桂圆、贺银圆、贺先圆。
贺敏学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永新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后来成为红军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解放后任福建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贺银圆后来改名贺怡,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与毛泽东小弟毛泽覃结婚。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死于车祸。贺敏仁参加红军,当司号兵。在长征途中被错杀。贺先圆又名贺仙,和贺敏振一起,在永新暴动后死于战乱。
贺敏萱在战乱中逃到吉安清源山亲戚家中,在那里当了斋工。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在“文革”中被打成“假党员”。一九七一年死于安徽合肥。
长女贺桂圆,是因为她生于中秋,丹桂飘香,圆月当空,取名“桂圆”。后来,她自己取“自珍”为学名,即善自珍重之意。参加革命后,改为“子珍”,如今以贺子珍之名传世。贺焕文捐官当上安福县知县,却因为人老实,受人排挤,丢了官,回到老家永新。他在永新衙门当了个“刑房师爷”,却被一场官司牵涉进去,坐了班房。那时,贺子珍不过四岁。出狱后贺焕文看透尔虞我诈的官场,弃官经商,在永新县城南门禾水边上,开了一爿小店,名叫“海天春”,卖杂货,兼经营茶馆。他曾请了一位风水先生来预卜小店前景,风水先生意味深长地道:“屋舍虽破,两栋支撑;不进钱财,就出人才!”此话竟被言中……贺子珍在县城秀水初级小学毕业后,进入教会学校福音学校女生部学习。天主教的势力,早在十九世纪末,便已深入永新县城。福音学校虽说是教会办的,但教学质量倒是不错的。这样,贺子珍从那里毕业时,已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一九二六年春,十六岁的贺子珍成了母校秀水初级小学的国文教师。就在这时候,从南昌来了个大学生,名叫欧阳洛。他是永新人,在一九二二年考入南昌省立第一师范。在南昌,欧阳洛结识了方志敏、赵醒侬、袁玉冰等人,参加了他们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一九二五年,欧阳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欧阳洛回到永新,使永新有了中共的种子。他在县城办起了平民夜校,贺子珍和妹妹贺怡成了第一批学员,思想日渐转向马克思主义。哥哥贺敏学,也跟欧阳洛过从甚密。这年夏天,贺氏三兄妹——贺敏学、贺子珍、贺怡,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贺子珍担任了永新县第一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不久,她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北伐军经过永新时,永新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那时国共合作,贺子珍出任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部长,成为永新十分活跃的人物。这时的她,不过十六岁!
贺子珍教妇女们唱起了《花脚歌》:“我们妇女真可怜,封建压迫几千年,别的暂不说,裹脚苦难言。脚小鞋子尖,走路要人牵,破皮又化脓,害人真不浅。大家快放脚,真正好喜欢!”一九二七年三月,贺子珍担任中共永新县委妇委书记。不久,她被调往吉安县,担任国民党永新县党部驻吉安办事处联络员,又任中共吉安特委委员兼特委妇委组织部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冲击波,也波及远离上海的永新县城。永新的国民党右派在六月十日黎明时分动手搜捕中共党员,原永新县工人纠察队军事教官萧金然叛变,带领国民党军队捉人。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等中共党员和群众八十多人被捕入狱。
贺子珍在吉安闻讯,心急如焚。左思右想,搭救贺敏学等人的唯一办法,是求救于袁文才。袁文才是贺敏学的中学同班同学,跟贺子珍也很熟悉。贺子珍便跟中共永新县委联系,由她向袁文才写信求援。
贺子珍还给狱中的哥哥写了信,托永新的舅母在探监时秘密塞给贺敏学。贺敏学也把自己写给袁文才的一封信,塞在一把竹柄油纸扇里。舅母一边摇着这把扇,一边走出监狱。袁文才接到贺子珍、贺敏学的信,会同王佐,率部攻打永新县城。七月二十六日晚,他们攻进县城,占领了监狱,救出了贺敏学等人。不久,贺子珍也从吉安赶来永新,随着哥哥一起,和袁文才、王佐上了井冈山。贺子珍上了山,就得了疟疾,只好在山上住下来休养。稍好,她下了山,住在茅坪大仓村。袁文才的部队,正驻扎在那里。贺敏学也住在那里。十月三日,从宁冈的古城传来不寻常的消息:毛泽东率中国工农革命军来到那里。据传,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呢。消息是龙超清传来的。龙超清说,毛泽东还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有名气呢。龙超清向袁文才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说是过几天来大仓村跟袁文才会面,要送枪给袁文才。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永新一枝花”贺子珍 2
袁文才很高兴,吩咐部下把银元一叠叠装入竹筒,一百银元一筒,装了六筒,说是送给毛泽东部队。十月六日,五六个男子走进大仓村。他们的脖子上,都系着一根红布条。为首的那位,瘦高个子,脸晒得黝黑,那眼睛里布满血丝。他跟袁文才握手之后,袁文才开始介绍他手下的部将。袁文才介绍了贺敏学,最后介绍站在贺敏学旁边的贺子珍。
那为首的人物,便是毛泽东。他见到十七岁的贺子珍,以为这姑娘是袁文才手下部将的女儿。
袁文才道:“她是中共永新县委委员。”毛泽东连声说:“看不出!看不出!”毛泽东询问了她的姓名,一下子记住了:“哦,祝贺的‘贺’,善自珍重的‘自珍’!”毛泽东在茅坪住下。那里有座八角楼,原是攀龙书院的课堂,楼上用明瓦砌了八角形图案,使课堂光线明亮,也就得了“八角楼”之名。那里本是贺敏学住的,让给了毛泽东。袁文才的住处离八角楼不远。疟疾未愈的贺子珍常坐在袁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来来去去,总要路过袁家门口,跟贺子珍有时聊上几句。渐渐地,她和毛泽东的接触多了起来。
贺子珍的疟疾渐愈,被派往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那里是贺家祖居之处。贺子珍父亲在捐官之前,就住在那里。贺子珍在黄竹岭工作了一些日子。后来,又到九陇山那儿工作。真巧,毛泽东带着警卫路过九陇山,跟她相遇。毛泽东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两人天天都在一起工作。当毛泽东离开那里回茅坪时,她跟毛泽东同路去茅坪。
贺子珍佩服毛泽东的才智学识,毛泽东喜欢贺子珍的俏丽坚强。毛泽东把贺子珍调到身边工作——担任秘书。从此,贺子珍的职务是“毛委员的秘书”。在那炮火纷飞、戎马倥偬的年月,爱苗居然悄悄在两人心头滋长。据东方出版社二○○三年四月出版的《贺氏三姐妹》一书称,为毛泽东和贺子珍做大媒的是袁文才的夫人谢梅香见《贺氏三姐妹》,第一百二十五页。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的日期、地点,各种说法不一。
据谭政的回忆文章《难忘的井冈山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中说:毛泽东同志与贺子珍结婚就是在夏幽,是一九二八年四月至五月,热起来了,穿件单衣,结婚很简单,没有仪式,没有证婚人,从夏幽退出以后,两人就是夫妻关系了。夏幽,也就是永新县夏幽区。讲得更具体一点,是夏幽区的塘边村。那时,贺子珍率工作队到塘边村打土豪、分田地,住在一位老婆婆家。没多久,毛泽东也带一些战士来到塘边进行分配土地试点。他俩和中共永新县委的刘真、胡波一起召开许多次群众座谈会,毛泽东提问,贺子珍记录。毛泽东在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永新调查》。毛泽东在塘边村先后住了四十来天。
毛泽东来到塘边村的日期,谭政只说了个大概。当时在中共夏幽特别支部工作的徐正芝的回忆,则讲得很具体:“一九二八年古历四月二十七日,毛司令率红军来到我们塘边村。”徐正芝:《忆塘边的革命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一九二八年古历四月二十七日”,即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四日。
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一书说是“三打永新”之后,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塘边村“终于结合在一起了”。三打永新,是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由中共永新县党史办公室编印的《永新人民革命史》(一九八九年九月版),内中的《贺子珍》一文,则写道:“一九二八年五月的一天,天气晴和,阳光明丽,毛泽东和贺子珍在茅坪洋桥湖的八角楼上结婚了。”虽然关于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的日子的各种说法稍有不同,但大体上都是说在一九二八年春夏之间。袁文才跟贺敏学、贺子珍有着亲切的友谊,又跟毛泽东建立了战斗友情,何况他是当地人,自然,由他出面请客,为毛泽东、贺子珍贺喜,是最合适不过了。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东方出版社二○○三年四月出版的《贺氏三姐妹》一书中,却有这么一段毛、贺之间“爱情描写”:毛泽东道:“谢谢你的一片心。”“难道说一个谢字就能表达了的吗?”“你让我怎么样?”“我让你看看我的心,有多爱你。”子珍终于鼓起勇气将“爱”字说出了口。毛泽东沉思良久说:“我知道你的心,我也知道你是位好同志,好姑娘,我也很爱你,因为……”“因为什么?”贺子珍追问。“因为我……”接着他说出自己的身世:“我已结婚,妻子还在家乡,路途遥远,杳无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