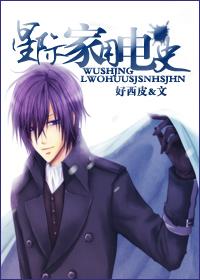乞丐的历史-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手段的缺乏,社会救济的有名无实往往又加剧了天灾的危害性,人祸与天灾互为因果,互为促动,成为一股把广大人民推向苦难深渊的邪恶力量。
天灾与人祸合力摧折了小农经济脆弱的卵巢,广大农民纷纷破产,饥寒交困、妻离子散、流离失所,还有一系列不虞之祸在等候着他们。因此,每当天灾人祸横生,流民便大量涌现,人民被迫走向流亡求生的自救之路,于是乎,行乞流丐便应运而生,流民与流丐,其差别只在毫厘之间。
流民现象大规模出现,并见之于文献记载,始于汉代。《史记》卷一百三《万石张叔列传》载:“元封四年中,并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这是史籍中有关大规模流民的第一次明确记载,自此以后的西汉各朝直至新莽,流民均连年发生,史不绝书。察其原因,天灾人祸是首要原因。如成帝阳朔二年秋,“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关”。鸿嘉四年,“农民失业,怨恨者众,伤害和,水旱炎灾,关东流冗者众,青、幽、冀部尤剧”。哀帝年间,“阴阳错谬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平帝元始二年,“郡国大旱,蝗,青州成甚,民流亡”。王莽代汉,“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青、徐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地皇三年,“枯旱霜蝗,饥馑荐臻,百姓困乏,流离道路,于春尤甚”;新莽末年,“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乃置养赡官廪食之。使者监领,与小吏共盗其廪,饥死者十七八”。(以上所引,均载于《汉书》卷十、卷八十一、卷十二、卷九十九下)
刘秀“复高祖之业”,建立东汉王朝以后,虽曾设法安辑流亡,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民问题。终东汉一代,农民的流亡从未中断:建武九年,刘秀派兵平定陇西,但“陇西虽平,而人饥,流者相望”;十二年正月,“小星流百枚以上,或西北,或正北,或东北,或四面行,皆小民流移之征”。天上是流星频现,地上则“中国未安,米谷荒贵,民或流散”。以天象作为流民之征象,虽是无稽之谈,却也反映出其时流民问题的严重。明帝时虽无流民的确切记述,但从其在位十八年间五次赐“流入无名数欲自占者人一级”的情况来看,流民问题不仅存在,而且比较严重,否则明帝便不会表现出如此的关切。章帝建初年间,“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自和帝开始,东汉的流民问题又迅速地趋于严重:和帝永元五年,“遣使者分行贫民,举实流冗,开仓赈廪三十余郡”,流民数量之多不难想见;六年,“阴阳不和,水旱违度,济河之域,凶馑流亡”;十四年,“赈贷张掖、居延、敦煌、五原、汉阳、会稽流民下贫谷,各有差”,流民已遍及全国各地,西北、东南,所在多有了。安帝即位之初,“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时饥荒之余,入庶流进,家户且尽”;“州郡大饥,米石二千,人相食,老弱相弃道路。”顺帝水建年间,连年灾潦、冀部尤甚。比蠲除实伤,赡恤穷匮,而百性犹有弃业,流亡不绝。“恒帝永兴元年,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延熹九年,“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及至灵帝时“黄巾”已起,社会动荡,“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关,北徒壶谷,冰解风散,唯恐在后”。东汉末年的献帝时期,“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刘)虞者百余万口”。(以上所引,见载于《后汉书》卷十五、《后汉书·天文志》、《后汉书》卷三、卷四、卷三十二、卷五、卷六、卷七、卷六十六、卷五十七、卷七十三)
魏晋六朝之际,天下大乱,南北分治,群雄并立,军阀混战,广大民众在动乱之中已是饱受流离迁徙之苦,加之天灾连年,更使流民大增。当时水、旱灾、风灾、地震、冰雹等自然灾害的接连发生,如惠帝元康四年(294)“京师及郡国地震”,五年“荆、扬、兖、豫、青、徐等州大水”,六年“关中饥,大疫”。七年“雍、梁州疫,大旱……关中饥,米斛万钱,八年荆、豫、扬、徐、冀等五州大水、地震”,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饥荒、瘟疫,则又在一定程度上促发了流民队伍的加速形成。
二天灾人祸(2)
纵观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在正常的王朝更迭之际,由于社会动荡,兵连祸结,天灾人祸在此时就愈显突出,流民发生的规模就愈大。而当异族入主中原之时,除天灾人祸外,又加以民族歧视政策,流民现象也十分显著。如元朝是异族入主中原的大一统王朝,终元之世,水旱荐臻,天灾频仍,蒙元享祚共一百六十三年,受灾竟达五百十三次之多。每当灾荒袭来,全国各地便呈现出一幅成千上万的人群流离失所的凄惨图景。而元朝统治者不加怜恤,却往往赋役如故,这就使愈来愈多的农民变成了“逃离奔窜,皇皇然无定居”的流民。(参见《元代流民问题浅探》,《郑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清代也有类似的问题,频繁的自然灾害致使人民纷纷流离,成为无家无地的流民。例如当时的北方地区,几乎是无年不灾,无处不灾,灾害的普遍性连续性为历代所罕有,其中黄河流域中下游尤为突出。道光三年到宣统三年的八十多年间,各种自然灾害波及直鲁豫三省区七千四百多县次,波及直鲁两省区六十七万多个村庄次。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农业经济的大破坏和人口逃亡,仅光绪二年至五年的黄河决口和水旱蝗特大灾害中,鲁直豫三省区死亡人口在九百万以上。在灾害过去之后,广大农民既丧失了恢复生产和防止新灾的能力,又重新陷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剥削之下,相当多的人不得不把“逃荒”视作出路。在保定以西河间以南,大率一村十家,其经年不见谷食者,十室而五,逃亡迁徙者十室而三,逃荒乞丐充塞运河、官道之旁,倒毙满路。茌平、东平等周边各州县,“十室九空”,“少壮皆逃亡”。山东各处多年亢旱,“田既无收,人因鲜食,故扶老携幼,结队成群,相率逃荒于奉锦各属,以觅宗族亲友而就食”。(参见《关于清代东北流民》,《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5期)
流民们抛开田宅家什,离开故土,迁徙他乡,一般说来,他们就此丧失了产业,也没有了职业,因此在他们中间转变为“无恒产”、“无恒业”的游民乞丐是极有可能的。诚然,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时期,尤其是新旧鼎革之际产生的流民往往在新王朝建元之初大量存在,而新王朝的统治者在绍统之初尚能颁布法令,招抚流亡,或安置流民,分给他们一定的田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希冀使流民重新成为王朝编户之下的齐民。但这些举措在实行过程中是大打折扣的,并不能使每个流民都重新回归故土,并成为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个中原因除了王朝政府举措本身的不完善,还有地主豪强的欺凌盘剥,地方官吏的营私舞弊等等,这样一来,流民中间许多人就转化成无田园可耕,无家室可依,无财产可置的赤贫者,他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落草为寇,成为与王朝政府为敌的“山贼草寇”,即一种民间自发的反抗社会的群体。另一条路就是继续流亡,在流亡之中行乞求食,以求得生存。
流民沦为流丐,历代均有。
唐代诗人皮日休在其《三羞诗·序》中谓:“丙戌岁(唐懿宗咸通七年),淮右蝗旱,日休寓小墅于州东,下经后,归之。见颖民转徙者,盈途塞陌,至有父舍其子,夫捐其妻,行哭立丐,朝哭夕死。”这是灾民流离生活的真实写照。
又,清代前期和中期,闽粤两省的一部分流民渡海到台湾谋生,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台求不到固定的工作,从而沦为游民或乞丐,据载:在康熙末年,闽粤两省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人口多向南洋等地流动。政府禁止前往南洋以后,游手无赖“群趋台湾”。雍正年间,福建官员奏报:福、兴、漳、泉、汀五府生齿日增,本地所产不敷食用,“粤东一带地广人稠,山多田少”,“所产米谷,不敷民食”,于是台湾成为闽粤人口流动的一个去向。向台湾移民的是哪些人呢?在早期,除了少数商人富有户以外,多数是游民。“流寓之人非系迫于饥寒即属犯罪脱逃”;“此等渡台民人,多属内地素无恒产,游手好闲之徒”。《台湾县志》曾经作过这样的分析,认为偷渡去台湾的多是无所依者、有所迫者、多所贪者和窘所施者。换句话说,是惰游失业、负罪逃弃、手无技能,倚奸为利之徒。这些人到达台湾以后,一部分人找到了职业,“上之可以致富,下之可以温饱”,成为农民、工匠甚至地主、富户。但是另一部分人本来就是“游手无艺、不事耕桑者”,他们难得固定的职业。乾隆中叶闽浙总督苏昌奏称:“偷渡过台之游民日众,昔年人少之时,依亲傍戚者无不收留安顿;近有人满之患,不能概为留,此辈衣食无依,流而为匪,非鼠窃狗偷,即作奸走险,无所不为。”台湾省乞丐队伍因而大增。(参见:《清代台湾的游民阶层》,《台湾研究集刊》1987年第1期)
游民,作为无业或没有固定职业的单身汉,他们的生活来源往往靠乞讨或强乞。所谓“游食四方”、“沿街强乞”、“日为流乞,夜行鼠窃”,是游民日常生活的一般情景。有时他们还聚众强乞,“要钱要饭”、“不索不休”,甚至有拦米、抢米、强借米者。
近代中国国难频生,社会动荡,人民苦愁离难,不遑生计,加之天灾肆行,流民较之于以往有增无减。乞丐队伍也就迅速膨胀了。1865年10月4日出版的《北华捷报》,对上海的乞丐大军,作了如下的描述:
二天灾人祸(3)
他们来自淮北,那里蝗虫为害炽烈。他们随身携带着地方官给予的护照前来逃荒——护照详细说明他们到此原因,证实他们的优良品行,宣称他们是好人,但是贫困地区的人。
一当粮食短缺——由旱涝蝗灾等引起,而政府又不能提供生活资料时,——这样得到许可的丐帮也就不鲜见了。因为食品不能给他们——既无钱购买,也没有交通运输工具——需要时穷人必须乞讨。
再如1931年长江大水,占灾区总人口百分之四十的人流离失所。据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调查,流离在外之人口,至少有五分之一的人以乞讨为生,其数目之大,实令人瞠目。这是流民转化成游民,继而转化为乞丐的一则典型事例。(参见《中国近代的流民》第11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由流民而乞丐,不独古代社会为然,当今社会中也是如此。当然,今天我们看到的流民多因社会转型、经济体制改革所引起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而导致,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流民是因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剧而由农业转离过来的,他们中大多数在流向城市的过程中都完成了由农民向工人或城市手工业者、劳务者的身份转化,并很快汇入到城市的社会经济生活之中。但其中仍有一部分因种种原因成为一种“盲流”,成为游荡于城市之中而又不为城市生活所容纳的游民,这一部分多以行乞为生,成为当今乞丐的一个重要来源。
要而言之,历史上频繁发生的天灾人祸导致了代代不绝的流民,而流民又成为乞丐大军的重要后备力量,就此而言,天灾人祸应视为繁衍乞丐的温床。
三差别与不平等(1)
我们的先哲在展望理想社会时,曾描绘出了这样一幅美妙的图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所有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分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是一个人人平等,人人有工可做,人人衣食无忧,太平安康的“大同”社会,然而,在数千年文明社会的发展史上,“大同”社会从来都只是一种理想憧憬,而不是一种现实存在。
事实上,文明社会,不论是在过去,抑是当今,都未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平等,在文明逝去的悠悠岁月中,与其说存在着许多平等、公正,还不如说不平等、差别是更为常见的社会现象。
人不是也不可能是彼此完全平等的,没有差别的。人首先在自然属性上就呈现出重大差异,有男女老幼之分,有高矮丰瘦之别,有智能愚贤之分,也有体质强弱之别。人因生理条件的不同而在性别、年龄、体质、智力、容貌等方面表现的差别,社会学上称之处自然差别。自然差别使人在实现个人理想、发展个人权利等方面的社会机遇和实现的可能性上各不相同。老弱病残之人较之于其他社会成员,显然在发展个人权利,实现个人价值方面要困难得多。
更重要的是,在文明社会中,人在社会分工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占有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数量、质量不同,享受教育的机会不同,参与社会交往、政治活动的机遇不同,而凡此种种,使人在社会身份、地位上呈现出重大差别,使人分化为富人,穷人,有产者,无产者,有权者,无权者,统治阶层,被统治阶层,剥削阶层,被剥削阶层,知识阶层,劳动阶层等等。于是乎,芸芸众生便分出三六九等,就归到了不同的层次与类属之中。
人的自然差别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人的社会差别则是后天的,是社会分化、劳动分工所导致的。
而决定人们社会地位和身份,决定人们生活命运的主要是社会差别。当然,自然差别也有相应的影响。
历代所见之乞丐,以老弱居多,以各类伤疾残废(盲、瘸、拐、傻、瘫等)居多,以遭灾的流民居多,即是显例。这样说,并不表明在传统社会中,上述“鳏寡孤独废疾”之人完全为社会所抛弃,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历朝的统治者出于安定社会、收揽民心之目的,出于“德治”理念的驱使,出于“王道”政治的价值追求,出于粉饰太平的功利目的,总是有一些“善政”出台,用以救济那些因生理缺陷而贫苦无告,无以自存的人。例如,南北朝时有“六疾馆”与“孤独园”,唐代有“悲田院”、“养病坊”,宋代京城有“福田院”,地方上有“居养安济院”,元代有“孤老院”,明代有“养济院”等等。然而,由于历代“鳏寡孤独残”,以及贫苦无告无以自存者人数众多,而朝廷所设置的这些保障机构一则规模小、经费有限;二则因为主事的官吏营私舞弊,故而使“悲田院”、“养病坊”、“福田院”、“养济院”之类的救济机构对于广大丧失生活能力的人所能起到的保障作用,就显得微乎其微了。这样说,并不是小视更不是无视中国古代社会保障机构的正面作用与进步意义,我们只是着重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当时条件下,社会需要保障的人数与社会能够提供的保障,其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举一个例子,明代由于太祖朱元璋的大力倡导,使各种“养济院”的数量与规模都超过了前朝各代,但即使如此,养济院在收养人员的条件、名额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明太祖是养济院的缔造者,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