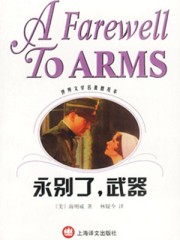怪异武器-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什么情况?”
“压在你心上的事。”
“没什么,”他说,“只是工作中的一两件事罢了。我得为这些问题拼命去干——这是我拿了工资该做的事。”
“是吗?”她不大相信地说,“别累倒了,而且也不要带回家来。家庭就是让你避开那些事情的地方。”
“我知道。不过烦恼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排除掉的。或许有些人一走出实验室就能把它抛在脑后,不过我不能。即使在家里,我也需要一个小时
※里奇是布兰森的昵称。
左右才能定下心来。”
“你可没有拿加班费啊!”
“我拿的工资是很高的。”
“你是应该拿很高的工资的。”她自信地说,“最好的脑袋就应该拿最高的工资。”
他轻轻地拍拍她的面颊:“是拿了,亲爱的——不过,有好多脑袋比我的更好。”
“胡说。”她把一只碗放在搅拌器下面,旋了一下开关,“你正在产生一种自卑感。你叫我感到意外。”
“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反驳说,“一个好脑袋是能够认出另一个更好的脑袋的。厂里有些人你必须亲自认识后才能信以为真。聪明人,多萝西,非常聪明的人。我巴不得跟他们一样能干呢!”
“好吧,如果你现在不如他们能干,不久就会碾他们一样能干的。”
“我希望如此。”
他站着,心里在仔细琢磨。会跟他们一样能干的,她刚才说。昨天这样说或许是有道理的。但是今天就不行。他的未来正在缓慢地、一点一点地、一个该死的项目接着一个该死的项目地掌握到别人手里,直到迟早有一天……
“今晚你是异乎寻常地安静,饿了吗?”
“不很饿。”
“要不了几分钟晚饭就好了。”
“好吧,亲爱的。正好来得及去洗一洗。”
走进浴间,他把上身衣服脱掉,然后擦洗身子,仿佛试图把精神上的黑影都清洗掉似的。
多萝西匆匆地走进来。“我忘了告诉你有一块温暖的干毛巾——怎么啦,里奇,你的胳膊上有青块。”
“是的,我知道。”他从她手里接过毛巾,擦去脸上和胸口的水,然后弯起胳膊,仔细察看胳膊肘周围的紫血块,摸上去感到疼痛。“今天早上,在梯级上摔下来。胳膊肘撞了一下,后脑袋也碰出了肿块。”
她摸摸他的颅骨:“不错,有很大一个肿块。”
“碰上去很痛。”
“那些梯级又长又陡。啊,里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也说不清,”他用毛巾又擦了擦,伸手去拿衬衫。“我正顺着梯级走下来,就像我走过的几百次那样。记不起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还在什么东西上面滑了一下,就这样脸朝下地冲过去了。有两个人正在梯级上走上来,他们看见我倒下来,往前一跳,就在我撞上的时候抓住了我。多亏了他们我才没有受重伤。”
“后来呢?”
“我准是有一小会儿撞得晕过去了,因为接下来我发现自己坐在梯级上,头脑昏沉沉的。两个人中的一个正拍打着我的脸,问我‘你好了吗,先生?’我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我谢谢他,然后就自个儿走了。不用说,我感到头晕得要命。”
“你去看了医生没有?”
“没有,没必要。几个肿块,就是这么一回事。”
她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眼中流露出明显的不安。“里奇,看来你可能是晕过去了,那可能意味着出了什么事,而——”
“没有什么事,我身体很好,就是掉到大峡谷里再弹起来也不妨。别为了几个肿块肿包激动。”
找到了领圈和领带后,他开始把它们套在脖子上。
“我当时准是心不在焉,或是粗心大意,踏空了一级或是什么的。它会叫我以后走路时多加小心。让我们忘了它吧,好不好?”
“可我还是——”她声音逐渐低下来,鹅蛋形的脸上露出了吃惊的神气,“天哪,什么东西烧焦了!”她匆匆跑回厨房。
他在镜子里打量着自己,一面小心地打着领带。瘦瘦的,苦行者似的外貌,薄薄的嘴唇,浅黑的眼睛,黑黑的眉毛和头发。左边太阳穴上有一块小小的白色伤疤。脸刮得很光洁,年纪在30岁左右,服装整洁。
这张脸看来不像是张杀人者的脸,太书生气。
但是如果双眼紧张地看着警察的摄影机,下面再挂一块身份号码牌,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拍摄的照片都可能是死囚牢房的合适候选人,特别是经过长长一个晚上的集中审问后,双眼迷迷糊糊,脸上邋里邋遢的,那就更像了。
“晚饭好啦!”
“来了!”他大声说。
他其实不想吃什么晚饭,但又不得不作出一些胃口大开的动作。头脑里充满的惊慌使他感到恶心。不过不吃饭会引起更多的尴尬问题。他将不得不硬把不想吃的食物咽下去。
“被定罪的人吃了一顿丰盛的、四道莱的饭!”
荒唐可笑?
面对自己的结局,谁也吃不了那么多。
上午9点他通过保安警卫。每一队警卫都对他点头表示认识。他像往常一样相继在三重门前忍受着令人厌烦的等待。从理论上说,在他每次进出的时候警卫都应该仔细检查他的正式通行证,尽管他们已认识他好几年。这条规定在直言不讳、性情暴躁的凯恩,被他的内弟第17次要求拿出他证件时发了一通脾气后就放宽了,现在警卫对熟悉的人点点头,而对不认识的任何人则会像猛虎那样狠扑过去。
走进大门后,他把大衣和帽子放在一只金属柜里,披上一件深绿色的、上面别着一块号码牌和辐射片的罩衫,穿过一系列走廊,再通过几个警卫,然后穿过一道涂了绿漆的门。进门后,他穿过一个长长的、装饰华丽的实验室和几个巨大宏伟的车间,最后来到后面一间用钢铁铸成的小屋。凯恩和波特两人都穿着绿色的罩衫,已经在那里了。小屋中央放着一样东西,他们正在讨论有关这件东西的某一问题,铅笔指着散放在工作台上的图样。
混凝土地上放着的那件闪闪发光的金属物体像一个十字架,形状介于巨大的汽车引擎和鼻子长长的高射炮之间。它的外形骗不了人。任何一个合格的弹道专家只要稍微观察一下,就能肯定地说出它的用途。它的底座旁边放着一小排导弹,它们一丝不差地泄露了天机:这些都是没有外壳的炮弹。
凯恩和波特讨论的对象是一个全自动高射炮的实验模型,由于使用一种新的液体炸药而使它的威力特别可怕。这种液体炸药可以用泵抽吸,可以汽化,可以喷射,也可以电动发射。在制图板上,这种玩意儿能在一分钟内把600个近炸引信导弹快速连射到7000英尺高空。但是在试验场上结果就完全不同;不到18秒钟,炮管由于被摩擦热所磨损和扩张,发射出来的炮弹在飞上去时会激烈地摇晃。
他们作了无数次修改,结果使他们仅获得4秒钟的有效发射。基本概念是第一流的,但在真正的实践中,毛病却比任何东西都要多。如果几星期或几个月的反复试验、争论和绞尽脑汁可以创造完美的话,他们将会拥有一个能把天空撕破的小玩意儿了。
目前他们正在试图找出如何解决发射速度的问题,他们已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这一问题并非绝对无望解决。作为最后的一招,他们可以用一种设计成能连续发射的多炮管高射炮来替代。但现在他们还不准备试用这最后的一招。
凯恩停止了和波特的谈话,转过身子对布兰森说:“这儿又是一个受到挫折的天才。告诉你,我们已经作出了确定的结论。”
“是什么?”布兰森问道。
“炮管内壁的衬层或炮弹必须用摩擦力较小的合金来制造。”凯恩回答说,“大家都说你是冶金方面的专家,发明这种合金是你份内的工作。因此开始加紧干吧。”
“如果我能做出来,那敢情好。”
“他们在缠着希尔德曼不放,”波特若有所思地插话说,“如果他的部门能使炮弹不摇晃,就像他们想要的那样,”他指指那门炮,“我们就可以把这破烂扔到河里去。导弹就会自动推进,我们所要建造的将只是一个十分巨大的火箭筒。”
“我不懂炸药这一行,因此我不知道它在这方面出了什么毛病。”凯恩说,“不过你放心,我们已对它作了试验,并且发现它在某个重要方面不能令人满意。”他围着高射炮走了四圈,大声抱怨说,“这个玩意儿是被它本身的效能害苦的。我们得想个办法,在保持所有令人高兴的事情的同时,排除掉令人痛苦的东西。为什么我不去作赌注登记人而让生活过得安逸些呢?”
“我们非得用多炮管不可。”波特说。
“那就是承认我们的失败。我不愿意承认失败,你也不愿意。决不投降,那样可不行。我喜欢这个丑陋的没用的东西,是我帮着一起建成的。它是我的生命,它是我的爱情。去他妈的批评不批评。”他试图在布兰森那儿得到情感上的支持。
“你会不会仅仅由于你心爱的东西给你添麻烦而把它毁灭?”接着,他看到布兰森的脸色煞白,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径自走开了。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转向波特,用感到意外的声调说,“我说错什么啦?真见鬼!我不知道他是想杀死我还是想从窗口跳出去。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他这种神气。我说错什么啦?”
波特盯着布兰森穿过的那扇门,毫无把握地说:“你准是踩了他的痛处啦。〃“什么痛处?我不过说——”
“我知道你说些什么?我两只耳朵都听着。显然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什么特殊的、碰不得的东西。或许他在家里闹矛盾啦,或许他跟他的妻子干了一仗,他要她去死。”
“他决不会这么做,我非常了解他。他不是那种在家里发火的人。”
“说不定他妻子是那种人。有些女人可以不为什么就歇斯底里大发作。如果他的妻子弄得他受不了,那将会怎样呢?”
“我的推测是他会闭上嘴,而不会火上加油。
作为最后的一招,他会一声不响的打起行李就走,永远不再回来。”
“是啊,我估量他是这么一个人。”波特表示同意地说,“不过我们可能会猜错的。谁也说不清另一个人在紧急情况下会做些什么。每场灾难都会带来出乎意外的反应。叽哩呱啦爱吹牛的粗壮大个儿会跳进洞里躲起来,而不大讲话的瘦弱小个子却会做出英勇的事情来。”
“让他见鬼去吧!”凯恩不耐烦地说,“让他去解决他自己的问题,我们来设法解开自己的难题。”
他们来到工作台上的图样前,重新考虑起来。
三、神思恍惚
布兰森五点钟离厂回家。真是糟糕的一天。是他所能记得的最倒霉的一天,一切都出了毛病,没有一件事是顺手的。他的好多时间似乎都用在小心提防,驱除恐惧,以及试图集中思想的努力上,然而总是不成功。
在任何研究机构中,能集中思想是基本的好品行。如果一个人的头脑里刻画着一个死囚的牢房,他怎么能集中思想呢?到现在为止,仅仅是由于两个不认识的卡车驾驶员随便谈起在伯利斯顿附近的某一个未具体说明的地方发生了一件未被发现的罪行,他的神经便几乎24小时一直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他们谈到的那棵树不一定准是他的那棵树,那些骨头也不一定准是他杀死的那个人的骨头。可能是其他什么人过去犯的罪行到最近才暴露——现在可能正在全力追击,搜捕另一个目标。
真可惜,他思索着,他当时没有勇气加入那两个卡车驾驶员的谈话并加以引导,直到他弄清他想知道的细节。这样做是否明智?是的——如果他们提供的情况最终能消除他的恐惧。不明智——如果它证实了他最担心的恐惧。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表示出的兴趣可能会引起疑心。那个在一起谈话的、爱抱怨的人可能会显示出一种危险的机灵。
“嗨,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先生?”如果他这样问。
他该怎么回答呢?他能说些什么呢?只能说些愚蠢的、不能使人相信的话——甚至连这些话也可能引起麻烦。
“喔,我曾在那儿附近居住过。”
“现在还住在那儿吗?是不是在伯利斯顿附近,嗯?你记不记得有个女人在那个地区失踪了?或者你能说出谁还可能记得吗?或许你对这件事有所了解吧,嗯?”
如果今天晚上这两个人又在小餐馆里,是不是最好不理睬他们,还是应该跟他们一起谈话并且使他们在谈话中讲出些什么来?他怎么也打不定主意。如果他是那种爱酗酒、爱吃喝玩乐的人,那么结论就很简单,和他们混在一起,买些啤酒,一边打着嗝儿,一边引导他们谈话。可是他不是那种人,他怀疑自己是否能装出那种完全不合他性格的样子来。
当他在转角处拐了个弯,看到一个警察站在那里时,他正在考虑的事情都从他头脑里溜走了。他从警察身边走过去,拼命想装出一副随随便便、漠不关心的样子,甚至还无忧无虑地吹着口哨。
警察盯着他,双眼在帽舌下的阴影处闪闪发光。布兰森迈着安稳的步子向前走去,感到,或是自以为感到对方的眼光灼痛了他的后颈。他不知道他这样过分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是否引起了警察对他的注意,就同一个顽皮的孩子由于夸大了自己的无辜而暴露了自己一样。
他神经绷得紧紧的,他知道一声带有权威性的吼叫“嗨,你!”就会使他拔脚奔跑。他会越过街道,穿过车辆,沿着偏僻小巷发狂似的飞跑着,脚步声在他后面噼噼啪啪地响着,哨子狂吹,人们大声喊叫。他会跑啊,跑啊,跑啊,直到筋疲力尽地倒下来。然后,他们就会抓住他。
没有响起使他拔脚奔跑的喊叫声。来到下一个转角时,他忍不住向后面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警察还在那里,仍旧朝他的方向凝视着。拐弯后,布兰森停住身子,数到十,然后再往后面看了看。警察仍在老地方,不过他的注意力现在已转向了别处。
他出了一身汗,如释重负,不一会儿,来到了车站。他买了一份晚报,匆匆地在报纸上寻找任何与他有重要关系的消息,结果一条也没有找到。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警方只是在认为适当时,而不是在此之前,才向记者发表声明的。而通常他们要到能说出罪犯的名字并要求报界协助搜捕时,才认为是适当的时机。
他要乘坐的那列火车轰隆轰隆地进了站,并把他带到了他要换车的车站。他下车来到小餐馆里,卡车驾驶员并不在那里。他不知道到底感到了宽慰还是感到了失望。唯一的另一位顾客是一个身材高大、脸无表情的人,他两脚分开,跨坐在一张高凳上,一脸厌烦的神色,凝视着柜台后面的那面镜子。
布兰森要了杯清咖啡,小口地喝着,过了一会儿,与那个大个儿的眼睛在镜子里对望了一下。在他看来,那个人似乎不是在随随便便地看他一眼,而是带着比通常更浓厚的兴趣观察着他。布兰森把眼光移开,过了一分钟,再转过去。那大个儿仍然在镜子里打量着他,而且并不试图隐瞒这一事实。
他有着一种十分傲慢的神气,似乎他习惯于盯着人家瞧,并公开向他们挑战,看他们是否敢作出什么反应。
一个铁路工人走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