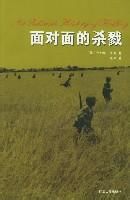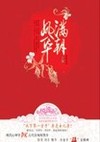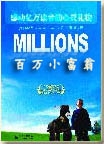面对面的杀戮-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若把战争比作游戏,则必定“按玩家各异的国民性”来进行。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124。辨认不同种族的特质方便了军事战略家选派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负责宣传的人也可以利用“盟军士兵不同组合在敌人心中造成的幻想恐慌”(如“凶猛的波兰人、捷克人、廓尔喀人和苏格兰高地人”)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心理战部分原则”,1944年5月,页4,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41/3。在本书探讨的三次大战中,就有一些种群据说特别骁勇善战。比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士卒就以残忍闻名。例见罗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别》,1929年首版(伦敦,1977),页164。斐济岛民据说因为“久居蛮荒之地,野性十足”而适合在太平洋作战。H。普赖迪,《椰树广场的战争:守卫南太平洋岛国基地》(惠灵顿,1945),页46及128—130。苏格兰人勇武超群、凡战必胜的印象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还存留在人们心中。谢尔弗德·比德韦尔,《现代战争研究:战士、战具与战术》(伦敦,1973),页146。另见弗雷德里克·基灵,《基灵书信回忆集》(伦敦,1918),页260,致威廉·丹克斯教士书,1915年11月31日。高地居民之所以善战,据说是继承了“凯尔特人的烈性子”。有一位作家在1915年时写道:“手举双刃阔刀从高地上掩杀下来,血洗克洛登[苏格兰东北部高沼地,英国历史上詹姆斯二世党人1746年二次反叛的最后战场——译注]的或许就是苏格兰人的祖先。刀剑向来是其最爱。”埃斯考特·林恩,《戎装保皇:一战纪事》(伦敦,1915),页151。难怪德国人一看到苏格兰褶裥短裙就总“玩完”。亚历山大·卡托,《与苏格兰军队在法国》(阿伯丁,1918),页21及42—43。某些印第安人被认为更嗜血些,也更容易受到赞誉。辛西娅·恩洛,《异族士兵:分裂社群的国家安全》(哈蒙茨沃思,1980)对此有详细讨论。当时的见解,见空军约翰·布罗迪少尉,“日记”,收布瑞亚坦·格林豪斯(编),《执拗者说:加拿大两飞行员一战日记》(渥太华,1987),页13;帕特里克·米,《在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当炮手的二十二年》(伦敦,1935),页198—199;哈罗德·皮特,《列兵皮特》(印第安纳波利斯,1917),页11及111—115;威廉·普雷塞,“一天才一先令”,页2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前线地区一次精神病学会议的报告”,1944年8月8日—10日,页13—14,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550;维维安·斯蒂芬森汉密尔顿中校,“书信文件集”,利德尔·哈特中心藏;埃德加·华莱士,《都是英雄:一战事迹集》(伦敦,1914),页198—206;A。威廉斯,“驻缅印度士兵的精神病学调查”,《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23卷3期(1950),页131—132;道格拉斯·温尼弗里斯,《神职人员在前线》(伦敦,1915),页130—131。1914年时,圣奈赫尔·辛格曾这样描述廓尔科人:
他们以夜袭出名。像豹一样潜静,敌人不察,直到大祸临头才知道晚了,再加上自制的阔头弯刀和西式兵器,更加无敌。其人视力极好——黑暗中跟猫一样——听觉又极灵敏,更加大了他们手到擒来的砝码。圣奈赫尔·辛格,《印度斗士:其精神、历史和对英国的贡献》(伦敦,1914),页61—62。另见页71—75及辛格,《印度军队》(伦敦,1914),页30。
与之情况类似的是本章开头提到的美国印第安人,他们也被认为“生来”就是打仗的料,所以巡逻时常被要求在前面“带队”。陆军罗伊·贝纳维德兹军士长及约翰·克雷格,《荣誉奖章:一位越战老兵的故事》(华盛顿特区,1995),页85;汤姆·霍姆,“美国印第安老兵与越战”,收沃尔特·开普斯(编),《越战读本》(纽约,1991),页193;托马斯·霍姆,“被忘却的战士:美国印第安士兵在越南”,《越战一代》,1卷2期(1989年春季),页63;哈罗德·伊克斯,“印度人给希特勒取外号”,《柯里尔杂志》,1卷2期(1989年春季),页58。
但这里我将重点谈种族与杀人效率间的关系,主要是两大种群:爱尔兰人和美国黑人士兵。在军界他们都声名远扬:爱尔兰人“全民尚武”,而美国黑人则总被视作蹩脚士兵。如此分类,背后有什么“科学依据”?又将产生怎样的效果?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8
爱尔兰人天生好斗,曾是许多人的共识。见詹姆斯·费舍尔,《爱尔兰兵团在佛兰德和达达尼尔海峡的不朽事迹》,1辑(都柏林,1916);丹尼斯·格温,《雷蒙德的最后岁月》(伦敦,1919),页201;约瑟夫·基廷,“泰恩河畔的爱尔兰部队”,收费利克斯·拉维里(编),《伟大的爱尔兰将士和政治人物》(伦敦,1920),页128—129;G。肯尼迪教士,《一位随军牧师的峻语》(伦敦,1918),页35—36;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3及158;迈克尔·麦克多,《爱尔兰人在索姆河》(伦敦,1917),页26—27及114;N。马洛,“爱尔兰的精神”,《英伦评论》,6卷1期(1915年7月),页4及9;兰德尔·帕里什,《一个爱尔兰士兵的故事》(伦敦,1914),卷首插图及页343。他们生来非兵即僧,是句俗话。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111。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是其士兵特别勇猛的共识:事实上,正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比英国兵更勇猛,所以军事指挥官才特别愿意把他们选入“导弹部队”。陆军史蒂芬·格温上尉,“爱尔兰兵团”,收费利克斯·拉维里(编),《伟大的爱尔兰将士和政治人物》(伦敦,1920),页149及哈罗德·斯彭德,“爱尔兰人与战争”,《当代评论》,110卷(1916年11月),页567。其胆量、“闯劲”和积极主动无人能及。阿尔弗雷德·奥拉希利教授,《耶稣会威廉·多伊尔神父:宗教研究》(伦敦,1925),页439;丹尼斯·格温,《约翰·雷蒙德的一生》(伦敦,1932),页404;亨利·汉纳,《苏乌拉湾的战友:皇家第七都柏林燧发枪团》(伦敦,1932),页7;约瑟夫·基廷,“泰恩河畔的爱尔兰部队”,收费利克斯·拉维里(编),《伟大的爱尔兰将士和政治人物》(伦敦,1920),页145;S。克尔,《爱尔兰兵团的作为》(伦敦,1916),页135;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124;J。麦肯齐,《欲望之箭:国民性格及前景论文集》(伦敦,1920),页182及196—197;哈罗德·斯彭德,“爱尔兰人与战争”,《当代评论》,110卷(1916年11月),页566—567。正如诗人艾丽斯·库克所说:爱尔兰士兵“战壕里最优秀,拼杀时不落后”。艾丽斯·库克,《爱尔兰英雄在红色战争中》(都柏林,1915),页16。另见页19—20。这种近乎本能的好战欲也被用来解释在爱尔兰超军事组织遍地生根的原因。自由党作家哈罗德·斯彭德曾于1916年在《当代评论》上撰文说:
当前游离在英国陆军和民族义勇军之外的爱尔兰青年不会乐于置身一场世界性混乱以外。在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超级唐尼布鲁克集市[始于1204年,每年在都柏林郊区举办,以喧闹混乱闻名,1855年被取缔——译注]时,别指望爱尔兰人会坐在炉边悠闲地烤火。战时的爱国心虽然摇摆不定,但对战争的喜好却没有丝毫泯灭。一度超然的人们……开始转向可能的暴力形式。哈罗德·斯彭德,“爱尔兰人与战争”,《当代评论》,110卷(1916年11月),页570。
换言之,爱尔兰人满腔的进攻欲亟待释放——要是不能老老实实地服役,就只有投身其他形式的武装冲突。征兵率偏低虽会引来对爱尔兰人缺乏活力的指摘,但其“灵魂”处仍深藏着尚武精神。如有人竟敢否认,会被喝“滚开”,甚至成为谩骂的对象。“爱尔兰征兵情况令人满意吗?”,《联军杂志》,新辑,51卷(1915年4—9月),页567及571。
爱尔兰人天生善战的神话在上世纪初不可思议地成为人们的信条,整个20世纪没有人对它产生过怀疑。二战时,在突击队中他们极为抢手,就是因为嗜杀成性(分列二、三的据说是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戈登·霍曼,《突击进攻》(伦敦,1942),页53。该观点甚至得到历史学家的赞同。在其无所不包的《现代战争研究:战士、战具与战术》(1973)中,谢尔弗德·比德韦尔欣然评论说,有的种群,如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廓尔科人,可谓“尚武之族”。谢尔弗德·比德韦尔,《现代战争研究:战士、战具与战术》(伦敦,1973),页146。在《好战的爱尔兰人》中,肖恩·麦坎把他们描画为“性情急噪……在任何历史阶段,不论对错,从不甘于寂寞,有机会总要施展一下”。肖恩·麦坎,《好战的爱尔兰人》(伦敦,1972),页9。另见陆军上将约翰·哈基特爵士序,陆军A。布雷丁准将,《爱尔兰士兵史》(贝尔法斯特,1987),页Ⅹ。连彼得·卡斯坦也在其学术著作中认可了“爱尔兰人好斗”的说法:没办法,他们就是天生爱干架。彼得·卡斯坦,“英军中的爱尔兰士兵,1792—1922:被收买还是被控制?”,《社会史学刊》,17期(1983),页40及59。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9
跟所有真正的英雄一样,爱尔兰士兵也特别善使刺刀。列兵罗伯特·麦格雷格1915年致父书,引自艾米·格兰特,《善恶对决:一战书信集》(波士顿,1930),页91—92及S。克尔,《爱尔兰兵团的作为》(伦敦,1916),页47—48及103。用都柏林第八军团威廉·多伊尔神父的话来说:“我们本可以生擒更多的人,都怪这鲁莽的爱尔兰人,这个危险的家伙只要摸着刀就要在每人身上戳好几个窟窿才完事。”阿尔弗雷德·奥拉希利教授,《耶稣会威廉·多伊尔神父:宗教研究》(伦敦,1925),页473。爱尔兰的宣传机器也拿这点大做文章。S。巴涅尔·克尔在《爱尔兰兵团的作为》(1916)中称,“爱尔兰士兵尤好近身作战。这种打法早已融入其血液,是与生俱来的。躺在战壕里等着‘中枪子’是他们最无法忍受的,这倒和法国人相似;爱尔兰人要的就是‘起来干他们’”。S。克尔,《爱尔兰兵团的作为》(伦敦,1916),页47—48。
如果说爱尔兰人是天生的斗士,勇武世人皆称道的话,那美国黑人就正好相反,被认为是厌战、怯懦的典型。从历史来看,这并不符实。事实是,黑人士兵在美军服役的历史很是久远,且有着骄人业绩,直到一战爆发前都是这样。其勇武一以贯之,从独立战争、美英战争到南北战争、美西战争。摘要见霍勒斯·邦德,“一战前美军中的黑人”,《黑人教育杂志》,7卷(1943),页268—287。但一战中,他们却被安排在勤务而非战斗部队,使得四分之三的黑人士兵整个战争期间不得不在非战斗部队服役。查尔斯·威廉斯,《黑人士兵趣闻》(波士顿,1923),页27。二战时,军方故意以黑人在美国人口中比例为限来招募黑人士兵,也就是说,每十名美兵中只有一个是黑人。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494。而这为数不多的黑人士兵又有四分之三是军需兵、工兵或运输兵。黑人士兵在整个陆军中占10%,但在勤务部队中就有20%,在“一般性”士兵中占了15%,在战斗部队只有5%。尤利西兹·李,《招募黑人士兵》(华盛顿特区,1966),页453—454。一战中,有首军谣这样唱道:
黑人兄弟只能用铲子和锄头打仗——
老天爷,您睁眼可怜可怜我们吧。约翰·奈尔斯,《唱歌的士兵》(纽约,1927),页48。奈尔斯认为黑人士兵唱歌不错,可打仗不行(页Ⅸ)。
虽然军方赞赏黑人对勤务部队的贡献,但不让他们上阵冲锋,还是被认为是对其勇武的直接否认。
这一政策背后有明显的种族歧视。美国空军最初就有这样的论断,说黑人(和日本人一样)不会驾驶飞机;等被事实驳倒了,又说他们打仗不勇猛,即使敌军防空火力“微弱、不准”也怕得要死。尤利西兹·李,《招募黑人士兵》(华盛顿特区,1966),页453—454。约翰·理查兹在一战时指挥一支黑人部队。他认为黑人士兵“身体素质好”,适于阅兵表演,忍耐力强,而且忠诚,“能无畏于枪林弹雨,勇往直前”,理查兹写道。但因为他们怕黑,进取心弱,易陷于恐慌,所以总的来说在战争中用处很有限。黑人不像英美人那么好斗,且易受他人影响,常开小差。理查兹继续写道:
你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可做起事来总是稀里糊涂。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骨子里缺乏白人那种自由、独立的精神;弹如雨下时,正是这种精神显现、我们受到激励之时,“德国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胜利终将属于我”。
在黑人士兵、军官中这种信念很少见。理查兹写道:“他们还都是孩子。永远无法长大,即使在炮火下也一样。”1926年,俄克拉何马大学某社会学教授也附和其观点,认为黑人士兵与生俱来的孩子气和对长官的完全信赖,使得“卓越的领导”成为保证其战斗力的最重要因素。他坚持认为,最好的黑人部队都是“德才兼备”的白人军官带出来的。约翰·理查兹,“与黑人士兵共处”,《大西洋月刊》,1919年8月,引自杰罗姆·道得,《黑人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纽约,1926),页233—236及239—240。巴勒德上将关于一战期间黑人士兵表现的报告也作如是观。他在日记中称,这些黑人士兵简直就是
窝囊废。且不说上阵杀敌,他们就连自己也照看不了。指望他们冲锋陷阵根本就是痴人说梦。我随军已三周,却无法让他们哪怕向敌人发起一次进攻。他们不是当兵的料。巴勒德上将的报告,引自杰罗姆·道得,《黑人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纽约,1926),页226。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10
这种看法会产生误解甚至“敌我不分”。1941到1945年间在美国南部白人女大学生中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她们甚至认为黑人不如德国佬,到1944年时便连日本人都不如了。黑人迷信、慵懒、无知、笃信宗教、不能倚赖、不尽人事、肮脏、邋遢、不修边幅。尽管愈发融入军队,但对黑人的种族成见却没有改观。多萝西·希戈,“成见:珍珠港事件前后”,《心理学刊》,23期(1947),页55—63。另见林恩·拉尔亚,“医学预科心理学专业学生关于人性的奇怪想法”,《英国教育心理学杂志》,15卷2期(1945年6月),页72及141。
也有论者认为,黑人士兵表现欠佳是白人官兵看低他们造成的。自尊心不强,缺乏信心和受教育程度低导致他们作战欲望不高。美国陆军首席历史学家曾指出,缺乏攻击性是黑人刻意保持低调的结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外界的攻击。他的结论是,指望把二等、三等甚至四等公民培育成第一流的士兵是不现实的。小沃尔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