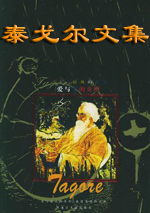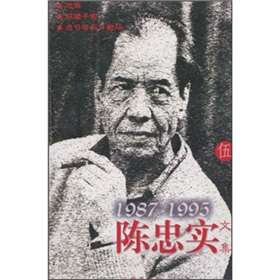张洁文集-第16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行啊,你带个头儿。”于是女劳模就起了个头,“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在这种场合下唱这种歌?不过胡秉宸还是跟着大家唱了起来。吴为不唱,抬着头眯着眼睛看天,看云。
好端端的阳光灿烂,突然就密布阴云。重又开始割稻时,吴为对胡秉宸说:“您的每个音符都不准,不是升了半个音,就是降了半个音。”
“这么说,还是对了一半儿,该给六十分广一旦与吴为对话,胡秉宸就情不自禁地诙谐起来。
“不,只能是零分。您大概不知道您是音盲吧?”回去的路上,胡秉宸清醒了,有意不与吴为同行。他犯不上为了那股中药味、那点政治上的宜泄以及那个“您”,招致群众的“看法”。
割稻之后,吴为发现老与胡秉宸照面。如果说她在室外阅读《毛选》时,隔壁的胡秉宸过来搭个茬儿还不为奇的话,那么他像影子似的,无时无刻、无声无息地跟在身后的情况,就着实让她有些恐惧。
最吓人的一次是晚上她独自徜徉在通往小镇的大路上,天光下,路面上一条好端端的木棍突然立了起来,原来是条蛇!吓得她往后一跳。
虽然吓了一跳,还不至于惊叫起来。可这一跳正好跳在后面一个软软的物件上,这比那条蛇还可怕地让吴为惊叫起来。
回头一看是胡秉宸,原来她这一跳之后,撞到了胡秉宸身上。
胡秉宸说:“对不起。”
怎么会这么近!
他一直在跟踪她,还是偶然?
连胡秉宸也发觉他们碰面的机会是不是太多了。休息日,胡秉宸常常在山野里走来走去,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休息。上个休息日到一条很远的河去,远远听到有人哭得好不凄怆。会不会是干校的人?此人会不会寻短见?便循声而去,等到走近才发现是歌声,真是长歌当哭了。
于是在离河滩不远的梨树下站住,不知怎么就知道,躺在梨树下的那个歌者,定是吴为。
他不禁心头一悸,她有什么苦处吗?这样的女人居然会有痛苦?
河边,梨树,歌声,孤男,寡女……真不是个好场景,赶快反身回走。晚秋的太阳晒得他的背好暖好暖,吴为的歌声却又阴又冷,那是什么歌呢?当然不是语录歌,也不像中国歌曲。
那一天,胡秉宸的耳边不断响起那凄怆如泣的歌声。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平时见她走路,脸子都快仰到天上去了。难怪人们要整治她,若不整治还不知会怎样,可她却躲到那么远的河边去唱。胡秉宸盼上了早上或下午的政治学习;盼上了那个坐在室外,拿着一本《毛选》对着远山发愣的吴为。有时更拿了几行传抄的诗句去搭茬儿:“你觉得这是陈毅写的诗吗?”
胡秉宸真是用了心,字体是他难得一现的工整。吴为反复琢磨胡秉宸抄在纸上的诗句——
二十年来是与非,一身系得几安危?
浩歌归去天连海,鸦噪夕阳任鼓吹。南国风云二十年,一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胡秉宸却打量着低头读诗的吴为。她的头发很浓,中间那条发缝白得让他心跳。
吴为随即在“一头须向国门悬”上画了一笔,显然是欣赏的意思;又在“一身系得几安危”的“一”字上画了一个圈,认真说道:“用字重复……倒是像他的性格。可他会写诗吗?
胡秉宸没有继续求证是不是陈毅写的诗,却缓缓地说:“有人问曹禺为什么不写东西了,曹禺说:‘写什么呢?’……《王昭君》是失败的,奉命嘛,命题作文总是不好写的……他应该有勇气写点儿什么。抗战期间他写过一个很好的剧本,说的是国民党一个伤兵医院,自院长而下腐败透顶,有位女大夫是个正面人物,来了个马专员,大力整顿,把院长撤了职,医院才面目一新,在暴露国民党腐败这个问题上很受观众欢迎。这个戏解放战争期间还在上演,后来却被说成是‘为国民党涂脂抹粉’,从曹禺的作品中消失了。如果不谈这些时代背景,只是就戏论戏,真是个好剧本,当时演出的剧团也是进步剧团,女主角由舒绣文扮演……我实在为曹禺可惜,他的才华没能全部发挥出来。他应该有勇气,为什么没有呢?只要不离谱儿就行’了嘛!我老认为老舍《茶馆》里三个老入扔纸钱的结尾,是‘曹禺式’的结尾,也许是曹禺给老舍出的主意,或者至少是受了曹禺的影响。真希望合禺再给中国留下几个经典剧本。
吴为说:“什么叫‘不离谱儿’?不离谱儿还能写出您所谓的经典剧本吗?”
一副与胡秉宸没的可说的姿态。
一看话不投机,胡秉宸及时调整了话题:“小时候读冰心的文章,可能是《寄小读者》吧,老记着那个在海边骑着一匹白马的小姑娘,这个形象好像凝固在脑子里了。十几岁又读了意大利人写的《爱的教育》,一个孩子为从马车底下救出一个更小的孩子轧断了腿,他的同学又如何帮助他去学校……当时老想,什么时候我也能牺牲自己,去救一个更小的孩子……”
吴为这才不说怪话,开始认真听他说。
日后,随着他们关系的深入,胡秉宸将不断发现,矣为与他的一些趣味竟那样相似,——不过相似而已。
胡秉宸不能停顿,一停顿就很难继续这个谈话,也很难保存这种谈话的质地。他不能一再重复这种走近她的机会,吴为不觉得奇怪才叫见鬼。而且这是一个多争合适的场合。大庭广众之下,吴为的膝头还摊放着一本《毛选》,绝对不会有人另作他想,便不慌不忙侃侃而谈:“就说林黛玉,怎么不可以有个林黛玉?而且没有林黛五就没有《红楼梦》,为什么要用大抹子把一切都抹平?连主席都肯定了《红楼梦》嘛!不要把每个作品都样板化,否则就不能丰富多彩。京剧还得有各个流派,大名旦四个,小名旦还有四个……
“Dickens的陈腐的阶级观点和大团圆结尾让人厌烦,但文字是美的,我大学一年级读的英文课本就是原文版的《大卫·科波菲尔》。”刚才还打算认真听个仔细的吴为,说话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又开始一脸狐疑地看着胡秉宸。他说的都是什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像个杂货铺,不知专营什么买卖。是不是有点急于表现自己?又为什么要表现自己?
“您是不是觉得,狄更斯应该先学习学习马克思的阶级观点?”她拍拍摊在膝上的《毛选》说道。
吴为的刁钻此时已见端倪,如果胡秉宸早有所悟,将来也就不会悔清了肠子喝道:“你这个刁钻的女人!”此时千不该万不该把吴为的刁钻当有趣,大人不见小人怪地接着说:“……我想起牛津,古老风味儿十足,还有莎士比亚住过的那条小街也是如此。”然后转身回到隔壁的屋子里去,留下吴为继续对着远山发愣,百思不得其解:胡秉宸今天怎么一反平日的矜持,话多得出奇?
回到屋里,胡秉宸对自己大发其火。
吴为不是不明白胡秉宸这些姿态传递的是什么信息。像她这样一个自小就读《白雪公主》以及各类西方文学的人,怎么不懂得男女间的那些密码?
她只是怕了男人,既怕与哪个男人坠人爱河,更怕和哪个男人谈婚论嫁。
不是没有男人对吴为感兴趣,但无法让她相信那是真爱。其实验证起来并不复杂,只要不让他们切入主题,马上拿她的前科说话。
那些男人不过耍她而已!
像她这样有过前科的女人,还奢望什么男人的真情实意!
可惜正大光明的“随便玩玩”一说,一九四九年后不但转入地下,而且至少七十年代之前,只能潜伏在某些老奸巨猾男人的内里,女人就更不可能搭乘这趟车。
如果条件像二十世纪末那样宽松,吴为何不可陪着他们玩上一把?
但她从来不是随便玩玩的人,那些随便玩玩的人,哪个会玩出一个私生子来!
别忘了吴为毕竟是顾秋水的女儿,别忘了顾秋水当年怎样轻易就将自己的一生交待给了包天剑!
恰恰相反,吴为不投入则已,一投入就是不知进退,有去无回。那真是将身家性命都押上去的豪赌,直到赔光输净才会回头,而不像有些女人,一旦发现没有赚头拨马便走。她那输光当尽的下场,实在怨不得他人。
而且爱好文学的吴为,早就显出创作的倾向,不但喜欢创作故事,也喜欢创作男人。
她总是把男人的职业与他们本人混为一谈,把会唱两句歌,叫做歌唱家的那种人,当做音乐;把写了那么几笔,甚至出版了几本书,叫做作家的那种人,当做文学。见到与文字沾点边的人,也就以为遭遇了文学,便热情澎湃地扑将上去,还以为自己是委身文学,“文学”也就何乐而不为地接受了她。过后再读契诃夫的《宝贝》,只好会心一笑。
因此她也把干过革命、到过革命根据地的那种人,当做革命……她后来对胡秉宸的迷恋,和胡秉宸的革命经历有很大关系。岂不知大部分情况下,会唱两句歌和音乐根本不是一回事。同样,会写两笔甚至出版了很多书的人,和文学也不是一回事。就像那个会写两笔又出版了几本书的吴为,谁又能肯定说她与文学有关?吴为既热爱革命,又热爱音乐,又热爱文学,综观她这一生所选择的男人,差不多都和这种爱屋及乌的情节有关。《尚书大传》大战篇有“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于她则是“爱乌者,兼其屋下之人”,或双相通用。她的热爱要是再多,怎么是好?那么她这一生更是非常、非常地热闹而麻烦了。
所幸她热爱绘画的时候,已近日暮途穷。
不过这种无可救药的女人,哪个时代都有。
直到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文学生了一个私生子,并遭天谴人怒之后才知道,“相似号”不是;“等号”,才知道不能轻许,才开始自我放逐。
而多年的羞辱也为吴为的敏感优柔穿上了坚而冷的盔甲,她能不如此脆弱又如此坚硬吗?
再说,这个博大精深、十足贯通宋明理学“无言笑”的男人,怎么可能对她有非分之想!
4
“文化大革命”如斗形龙卷风,裹挟许多生命,陀螺般地旋转而去。如果只留意它锥形的长尾,为人间留下的不过是个下流无耻的回味。
风过处,却是哀鸿遍野,万树凋零,这才是龙卷风的用意所在。
一盘残棋下到这里,就是不断有人调回北京,也陆续有人被分配出去。
吴为自然是被遗忘的角落。她早巳习惯遗忘,觉得这个地位不错。干校里的人越来越少,也不赶着人们下地干活了。
于是吴为身背一把砍刀,型号如那个所谓反革命分子用于自杀的一般,独自爬上渺无人迹的深山,时而陷身青云暗雾,时而倾听奇禽啼鸣于幽林深处。当地老乡说山中常有豺狼出没,她却从来没有遇到过,连蛇也没有看到过,也许蛇们只是绕在树上将她窥视,并不游下树来与她为难。她难免猜想,那夜在小镇路上遇到的蛇,是否有意帮胡秉宸一把?
漫山都是毛竹,吴为却非要爬到山顶,砍一根七八十斤重的巨竹背下山来。这样一来,不是可以消磨一个整天?
下得山来,将毛竹截锯为一米多的长段,用砍刀劈成细条,再用瓦片刮润,做了门帘送人。
或在成堆废弃不用的木头中,拣些硬木块到车间加工小玩意儿,台灯座或是小水桶,然后用水彩在上面随意乱画,再涂一层清漆。
哪一桩是女人玩的活儿!可是,车床、砍刀、锯子、锉子,她样样玩得得心应手。
除了机油味、破车床、东一堆西一堆成形不成形的加工件,车间里什么也没有,真让人不能相信这里曾是心术角斗的沸腾场地。
吴为游走在这些破东烂西中,不是开怀坏笑就是嗷嗷怪叫,偏偏不作哈姆雷特式的严肃思考,不知这是否为她日后成为作家的一个缘由?
那天,又是如此这般在车间里翻江倒海,然后又上车床车一个螺钉,一手摇着进刀的手柄,一手拿着油壶往加工件上喷射冷却油降温,冷不丁听见背后有人说:“带水枪的女工。”
就像那个晚上在路上看到那一条蛇;猛然往后一跳,踩上一个软软的物件那样,又是一个惊恐。
回头一看,又是胡秉宸。
调过头来继续干活,心里一慌,进刀猛了,眼看螺纹车坏了,可她还是装模作样继续车下去。等。胡秉宸转身走开才停下床子,把那个废螺钉从夹具上取下,拿着那个废螺钉好一阵发呆。方才还能翻江倒海的吴为,转眼就变成一只瘪了的轮胎。
似乎有一只蚊子在很远处飞,越飞越近,到了近处才知道那不是蚊子振翅,而是一种不祥的声音。她伸出双手,妄图挡住那不祥之兆,可是它们比她的手臂有力,不容抗拒地向她渐渐逼近。
天色已暗,她拿起抹布擦了擦满是机油的手,出了车间。
有星星冷锋在她脸上交错相击,抬头一看,雪片如席。冬天已经过去,春天就要来临,可是这场春雪比冬雪还大,地上积雪足有一尺多厚。
树枝被积雪压得咔咔轻响,有些细枝还断裂下来。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何止细枝的断裂声,连自己的呼吸也听得清清楚楚,心情也就好了起来。
积雪没过了吴为的脚踝,她一面数着自己的脚印一面前行,雪片边落边融,将她的头发湿贴在额上,凉丝丝地爽,毕竟是春雪了。可是,绝非一人独处的感觉向她袭来,转身缓缓四顾,天色苍暗,漠漠飞雪,如烟如梦,是焉非焉的一个胡秉宸,靠着一棵树站在雪地里。
难道在等她吗?帽子和身上的积雪,说明他已在雪地站了不少时间。
吴为脸上那点本就不多的笑意变成了严酷。
胡秉宸的确在等吴为。刚才到车间巡视,还没进门之前就想,要是能看见吴为就好了,一旦看到她,胡秉宸兴奋得简直有点莫名其妙,否则怎么会说出“带水枪的女工”那样明目张胆的调笑之词。
胡秉宸对吴为的调笑绝对始于性,哪个男人听了有关一个女人的那样传言,不往性上靠?可不知什么时候起,渐渐变成对她气质、素养、清雅外形的倾慕。多少次胡秉宸在车间外面窥视吴为,越来越发现她不像一个淫荡的女人,就连对“带水枪的女工”也挥然不觉。换了另一个女人,比如那位女劳模,就完全可以体味个中滋味。
这女人真是个谜,她到底聪明还是糊涂?单纯还是放荡?……
胡秉宸毕竟是胡秉宸,男人也毕竟是男人,将来他对吴为的兴趣还会回归为性,不过现在正缓慢地进入认识的第二阶段。
胡秉宸那个站立的姿态,让吴为的心隐隐一动,就像接上了阴阳两个电极。那不祥的声音又靠近了。
胡秉宸让她渐渐放松了对男人的戒备……原来她是怕自己对他好感有加。
望着吴为在雪中渐渐模糊的身影,胡秉宸相当失望。难道她没有看出他等在这里,只是为了再看她一眼,很有节制的一眼?只是为了再打个照面,说几句“多好的雪”之类不热不冷的话?
似乎并不因为她是女人。仅仅想和她说几句不热不冷的话吗?
实在又因为她是女人。
这个与已然中止咖日日生活似乎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女人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