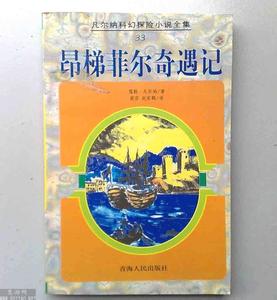昂梯菲尔奇遇记-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朱埃勒能否金榜题名,对年轻的姑娘极为重要,因为她和表兄早有约定。只有他拿到远洋船长证书时才是洞房花烛夜之日。他俩真诚相爱,纯洁的爱会带给他们幸福。全家早就盼着两个青年人尽快结合,喜日越接近,纳侬心中越是喜欢。还有什么障碍,那集叔父与监护人为一身的家长不是同意了吗?……或者,这位主宰一切的人提出的条件是当船长,方能结婚。这对朱埃勒并不算什么。他对本行业已全面学习过。从实习生、见习水手、服役水兵、商船大副等他都当过,他既有理论,又有实践,那位监护人其实也从心底里为侄子自豪。自然也不排除,他曾想过为他侄子攀一富豪联姻,小伙子确实人才难得;或许他也希望他的外甥女能嫁给一个有钱的贵族,因为全城也找不到这么可爱的姑娘。
“就是在伊尔一维兰,也找不到第二个!”他双眉紧锁,重复念道,他甚至想把此结论推广到全布列塔尼。
现有5千法郎的年金,已兴高彩烈,一旦成为百万富翁,他又会怎样呢?……他常这样沉溺于这些胡思乱想之中。
纳侬母女俩,正在收拾那位让人恐惧的人住的房间。或许应该把他的大脑也清理一下。这里,真有该清理的油腻、灰尘,还有飞蛾、蜘蛛……。
昂梯菲尔踱来踱去,眼珠轴辘、轱辘直转,这表明怒气尚未消除,电闪雷鸣随时有可能发生。当他看到墙上的晴雨表时,似乎又要发火,因为那仪器指针一动不动,无任何变化。
“朱埃勒还没回来!”他问外甥女。
“没有,舅舅。”
“已经12点了。”
“舅舅,还没有到。”
“他准是误了火车。”
“不会的,舅舅。”
尽管纳侬一再示意,姑娘还是竭力为表兄鸣不平。不同意这位出言不逊的舅舅对表兄的无理指责。
电闪雷鸣已不远了,难道没有一根避雷针,去排掉积在壮汉身上的电吗?可能有。“给我去找特雷哥曼”母女俩便急忙听命,一路小跑直奔着去找驳船长。
“上帝保佑,但愿他在家!”他们互相说着。谢天谢地,他在家。5分钟之后,他便来到壮汉昂梯菲尔的面前。
吉尔达·特雷哥曼,51岁,与他的邻居有不少相似点:都是单身汉,都当过海员、船长;现在又都不干了,都靠退休金渡日,也是圣马洛人。但截然不同的是在思想、气质方面:吉尔达,沉静、内向;昂梯菲尔活泼开朗。一个是富于哲理,平易近人;一个则暴跳如雷,难以相处。体质上两位老兄也差异不小。但他们两人是挚友。昂梯菲尔尤为在意他俩的友谊,而吉尔达·特雷哥曼则显差些。谁都知道作壮汉的朋友,并非是件美事。
虽然,吉尔达也曾当过水手,但比起昂梯菲尔航空阅历差远了,他因为是寡妇的儿子,免于服兵役,没有当过水兵,所以他从未见过大海。他从埃卡勒高地,从弗雷埃勒角,也望到过英吉利海峡,可从未去那儿航行过。他出生在驳船的小舱室里,在驳船上渡过了逝去的岁月。开始他当内河经港员,以后当了“可爱的阿美丽”号的船老板,在朗斯河上,游来游去。从迪纳尔到迪南,再到普隆莫卡,然后顺流而下返回,运载些木板、酒、煤炭等物。他对北滨海省和伊尔——维兰地区的河流,略有了解。这位是温和的内河水手而那位则是大海上最泼辣的水手——一个航海船老大。特雷哥曼自然十分敬重自己的邻居,而这位邻居竟然受之无愧。
吉尔达住一所漂亮而别致的小房,离昂梯菲尔家约百步远。在图声兹大街的尽头。靠城墙。房子一面临朗斯河的入海口,另一面则是外海。他虎背熊腰,肩宽近一米,身高5尺6寸,上半身厚壮得象一堵墙,总是穿一件双排扣的大坎肩,和一件背后及袖子均打摺的粗绒短衫,十分整洁。两只粗壮结实的胳膊,有一般人的大腿粗,一双大手掌简直象古卫士的脚那么大。可见,四肢和肌肉如此发达的特雷哥曼,一定力大如神。但这位和善的大力神,他从不滥用神力。就连与别人握手,也只用食指和拇指,生怕把人家的手指玉碎。他从不炫耀,从不打人。
把他与机器比,他更象是冷压钢板的水压机。这种力是来自他伟大而慷慨,缓慢而不外露的气质。
他两肩托着一大圆脑袋,戴顶宽边礼帽,头发扁平,两颊薄须,翘翘鼻子很有性格。嘴总带微笑,上唇偏里,下唇偏外,雪白的牙齿,肥厚的双下颏。只是右上门牙脱落了,不能叼烟嘴,也才能使牙齿不被烟污染。他眉毛红棕、浓密,眼睛明亮而和善。他面色红润这要归功于朗斯河的清风吹拂的结果。
这就是吉尔达·特雷哥曼,一位助人为乐的人。无论你中午来找他,还是两点来打他,他随时都准备帮助你。因此,他是壮汉的怒浪冲不垮的岩石。当他们邻居发怒派人找他时,他仍去承受那位凶神所掀起的波涛袭击。
这位“可爱的阿美丽”号前任船主,在昂梯菲尔家极受爱戴的人物。纳侬把他当靠山,朱埃勒对他象对父亲,爱诺卡特竟无拘束地亲吻他的双颊和前额——相面人说过,从他的长相就可看出他秉性温存,为人随和。
将近4点30分钟,这位驳船长登上通往二楼的扶梯。在那沉重的脚步下,楼梯嘎嘎作响。接着,推开门,来到他的老朋友面前。
昂梯菲尔奇遇记 第五章 吉尔达·特雷哥曼并非总是顺从昂梯菲尔 “你总算来了,船老板?”
“招之即来嘛,我的朋友……”
“未必没拖时间!”
“就是跑路的时间。”
“真的!我还以为你是乘‘可爱的阿美丽’号来的呢!”
与快速的海船相比,“阿美丽”号驳船当然慢得多了。这种带刺的话,吉尔达并不介意,也不觉惊奇。他知道他这位邻居的秉性,他早已习已为常,还有什么不能容忍呢!
昂梯菲尔伸给他一个手指头,他用自己的大手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捏了捏。
“唉,别这么使劲,见鬼!你总捏得那么利害!”
“请原谅……我可不是故意的……”
“好吧!算我倒楣!”
昂梯菲尔做了个手势,请他的朋友坐在屋子中间的桌子前。
驳船船长听命坐到他指的那张椅子上,两腿弯曲,两脚向外撇,宽大的手帕铺在膝盖上,是一块棉织手帕,上边有蓝、红色的小花,每个角上绣着一个锚。
一看见锚,昂梯菲尔猛的耸了一下肩……一个驳船长的锚!为什么不绣一个驳船的桅杆!
“喝酒不,船老板?”说着他拿出两只酒杯和一瓶白兰地。
“我是从不喝酒的,朋友。”
昂梯菲尔还是斟满了两小高脚杯。按照老习惯,他喝完自己的这杯,又去喝好朋友的那杯。
“现在咱们谈谈。”
“谈什么?”驳船主答道,他很清楚为什么找自己来。
“谈什么,船主?你说呢?还不是……”
“对!又是纬度。你找到那个方位了?”
“找到了?开玩笑,你要我怎么找到?……你听那两个妇人嚼舌根就能找到……刚才……”
“是纳侬和我的可爱的爱诺卡特!”
“噢!我知道……你总是反对我袒护他俩,但问题不在这儿……我的父亲托马已去世8年了,8年了,这个问题还没有进展一步……总该有个收场吧!”
“我……”船长挤着眼说,“我认为收场就是不再过问此事……”
“真的,船老板!我父亲的临终嘱咐,怎么办?……那遗嘱可是神圣的!”
“糟糕的是你的好父亲没能多说一些!”
“他没多说是因为他本来知道的就不多!见鬼!是否我也会到临终时仍无进展?”
吉尔达·特雷哥曼正要回答说那很可能,甚至想说他希望如此。但他没有说出口,为的是不致使他那爱抬杠的朋友火上浇油。
那是在托马·昂梯菲尔临终前几天,突然发生的事。
1854年,老水手重病在身,觉得是时候了,是该把他那神秘莫测的故事讲给儿子听了。
55年前,1799年,拿破仑枪杀雅法战争战俘的那天,托马·昂梯菲尔在近东商船上,正沿巴勒斯坦海岸航行。一个奄奄一息的受难者躲在一块岩石边,死亡在威胁着他。夜里,法国水手发现了他,把他带上船,给他治伤,经过两个月的精心治疗,终于恢复了健康。
得救的战俘向他的救命恩人自我介绍说,他叫卡米尔克,埃及人。告辞时,他向好心的圣马洛人担保,他不会忘恩,到时一定会报答。
分手后,托马·昂梯菲尔继续他的航行,或多或少地也想过许诺给他的诺言。后来干脆不去想了。因为,在他看来那个诺言永远也实现不了。
随着岁月的流失,老水手退休了,回到圣马洛,一心教儿子皮埃尔学航海。1842年6月他突然收到一封信。那时,他已67岁了。
这封用法文写的信是从哪儿来的呢?……从邮戳上看是从埃及寄来的。里面写些什么?……原来只有几句话:
“敬请托马·昂梯菲尔船长牢牢记下这个纬度:北纬24°59′。经度暂缺,随后告知。切记勿忘、勿漏,这是一笔巨额财宝,纬度和经度,总有一天将是价值连城的黄金、钻石及珠宝,雅法战俘谨以此报答船长救命之恩。”
这封信的署名是连写的双K。
这信勾起好心人托马的遐想。事隔43年,卡米尔克还记得哪?他花了多少时间啊!毫无疑义,各种障碍使他未能如期报答。因为叙利亚的政局,只是在1840年7月15日签订了“伦敦协定”【1840年英、俄、奥、普四国在伦敦缔结的声称共同保障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与独立”,联合向副国王提出的最后通牒,促使其投降苏丹】之后,才终于稳定下来。
现在托马·昂梯菲尔是一个纬度的拥有者,它是通过地球上的某一个点,而卡米尔克总督的财富就藏在那里。……或许也只不过是几百万块钱罢了。但信中说要绝对保密。所以他对谁也不说,包括对自己的儿子。他期待着送信人总有一天会给他带来那个经度。
他等啊等啊,等了20年。
如果他直到临终时,还不见总督的信使,那么,他就会把这个秘密带往坟墓?……不!他想也不至于吧。他要把此秘密告诉一个能代替他的人——那此人便是他的儿子:皮埃尔·塞尔旺·马洛。所以当1854年81岁高龄的老水手,深感自己活不了几天时,便毫不迟疑地把总督的意图告诉了皮埃尔。并让他发誓——就象别人叮嘱过他的那样,永不忘却那个纬度,珍藏签有双K的信,信心十足地等待信使的到来。
不久,老水手与世长辞了。亲人们哭悼他,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怀念他,他被葬进了自家墓地。
人们了解昂梯菲尔师傅,这样的秘密透露给他,对他的精神,对他那一点就着的妄想,将会是什么影响,他全身心都燃起了强烈的欲望。在他看来,那财宝价值会比他父亲估计的几百万要扩大10倍。他想象着,卡米尔克总督好比“一千零一夜”里的大富豪。那财宝就象埋在阿里巴巴山洞里的黄金和宝石。然而,他生性浮躁,神经质,根本做不到象他父亲那样守口如瓶,那样12年只字不漏,也不想了解双K签名人到底怎样了?这一切,儿子根本做不到。1858年,在一次地中海的航行中,停在亚历山大港,他想方设法四处打听总督的下落。
是否真有其人?……这,既然父亲有他亲笔信,那还用疑义吗?
他现在还活着吗?……这是儿子最为关心的,得到的结果,令其失望,卡米尔克已离家近20年,目前下落不明。
这对昂梯菲尔是个可怕的打击,但他并不灰心。即使如此,也可断言,1842年他还活着。那封信便是证明。或许出于难以言明的理由,他离开祖国,但只要时机到来,他的信使一定会带来那令人焦盼的经度。既然父亲已故去,儿子出面迎接也是理所当然的。于是,昂梯菲尔回到圣马洛,尽管这次他付出了代价,而他和谁也没说。
但是,这整天无所事事,总为一个念头所缠绕,又是多么无聊呢?24度59分就像只可恶的苍蝇在绕头乱飞!他终于熬不住了,把秘密告诉了姐姐、外甥女、侄子以及吉尔达·特雷哥曼。因此,这个秘密——至少是一部分,不久便传遍全城,甚至传到了圣塞尔旺和迪纳尔以外。众所周知,一笔巨大的,不可思议的财富,总有一天会落到昂梯菲尔的手中,这本应是十拿九稳的事。然而,总是没有人来告诉他:“这就是你所等待的经度。”
几年过去了,总督和信使均未露面。根本就没有一个外国人跨过他家的门槛。昂梯菲尔常常大发雷霆,其根源就在于此。家里人已不再相信此事了,那封信只不过是一颗定心丸。吉尔达早就有看法,他只觉得自己的朋友过于天真幼稚罢了。为此,在内河航行的同伴中竟招致难堪。但皮埃尔·塞尔旺·马洛却坚信不疑,谁也动摇不了他的信念。这巨额财宝,好象他已在握,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谁只要稍有异议,便会引起轩然大波。
因此,这天晚上,驳船长坐在斟满白兰地的酒杯前,决计不想惹怒这位邻居,免得引起火药库的爆炸。
“嗳,”昂梯菲尔瞧着他说:“你好象不明白?请直截了当回答我!总之,‘阿美丽’号船老板是从未测过方位……在朗斯河两岸之间,没必要测定高度,观察日月星辰……”
通过例述航海学的种种基本实践,皮埃尔显然想表明,内河航行的驳船长阅历比起他——近海航行的船老大相差十万八千里。
和善的特雷哥曼只是微笑着,并不争辩,眼瞧着那块铺放在双膝上的花手帕。
“哎!你听见没有?驳船长?”
“听着呢,朋友。”
“好!干脆说吧,你准确知道什么是纬度?”
“知道点儿。”
“纬度是和赤道平行的圆周,分为360度,即21660分,相当于100万零280秒,你知道吗?”
“我怎能不知道呢?”吉尔达·特雷哥曼笑呵呵地答道。
“15度的弧线相当于一小时,15分的弧度相当于一分钟,15秒的弧度相当于1秒钟……”
“是不是要我再给你背一遍?”
“不,那不必。哎!我知道24度59分这个纬度。可在这平行圆周上,有360度——你听见吗?360度!有359度我可以不去理睬!但,有一点我至今还不了解,只有当有人送来与之交叉的经度时,我才真正了解它,就是在那个地方,有……多少多少法郎……你别笑我……”
“我没笑,朋友!”
“对,几百万属于我的财宝。知道它的藏处时,我就有权把它们挖出来……”
“好啊,”驳船长温和地回答道,“必须耐心地等待才是。”
“耐心,耐心!……你的静脉是什么?”
“我想是糖分,别无其它。”吉尔达·特雷哥曼答道。
“我呢!是流动的水银,它活泼,溶在我的血液里是硝酸盐……我无法冷静……我心烦意乱,如坐针毡。”
“你要镇静些!”
“镇静?……你忘了,1854年我父亲去世,而现在是1862年,他在1842年就得到这个秘密,快20年啦!我们至今还未解开这个谜。”
“20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