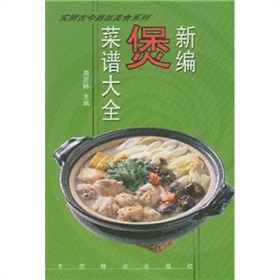红旗谱-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店掌柜绷起脸,摇晃着手,气呼呼地说:“咳!把那个外交官割了舌头,剜了眼了!”
忠大伯说:“八成,这仗得打起来!”
店掌柜囚了一下脖子,笑咧咧地说:“不,他们不行,他们软。这北伐军绕了个弯儿转过去了!”
朱老忠有点不相信,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江涛,江涛也说:“革命军打到武汉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还和共产党合作哩,共产党发动工农群众,向帝国主义游行示威,强硬收回外国租界。后来,他们骇怕了,镇压了工农群众,屠杀了共产党。这样以来,北伐军里就缺乏了革命性,打到济南城的时候,他们的外交官就被日本鬼子割舌头剜眼睛了!”
说到这里,店掌柜拍了拍江涛的肩膀说:“好小伙子!你是个明白人,将来一定能行。”说着,缩起脖子,嗤嗤地笑着走出去了。
朱老忠这时觉得心慌意乱,亲子情分,还是不忍回去。他又坐下来打火抽烟,想:“运涛这孩子……他要长期过着监狱生活了……”想着,目不转睛看着江涛。长圆的脸,大眼睛,和哥哥一样浓厚的眉毛,又黑又长的睫毛打着忽闪。叹口气说:“咳!多好的孩子,偏生在咱这人家。”
朱老忠自从接到运涛的信,总是替严志和父子着急,心上架着一团火。到这里,看运涛没有死的危险,心里才踏实下来。现在,全身的骨架再也撑持不住了,躺在炕上晕晕地睡着,做起梦来……梦里,他正躺在打麦场上睡觉。运涛笑模悠悠地,远远地跑来看他了。说:“忠大伯!院里下雨哩,屋里睡去。”说着,黑疙瘩云头上掉下铜钱大的雨点子,打得杨树的叶子啪啦乱响。
江涛看太阳下去,天空开始漫散着夜色,城郊有汽笛在吼鸣。他想到祖父和父亲的一生,想到朱老巩和忠大伯的一生,想到旧社会的冷酷无情。心里说:“阶级斗争,是要流血的!你要是没有斗争的决心和魄力,你就不会得到最后的胜利!”想到这里,头顶上象亮出一个天窗,另见一层天地。
忠大伯睡醒了一看,哪里有什么场院,哪里有什么杨树,还是在炕上睡着。他点着一袋烟,向江涛叙述了他的梦境,说:
“运涛一定能回去,能回到咱的锁井镇上!”
江涛说:“哪里有这么巧的事,是你想运涛想的。”
江涛在济南买了几张大明湖的碑帖,又买了二斤乐陵小枣,包了个小包袱,挂在腰带上。在山东地面买了一匹小驴,叫忠大伯骑上,江涛折了根柳枝,在后头轰着走回来。路上,忠大伯还说:“按我这个梦境说,运涛这孩子一定要回来,共产党不算完!”
江涛说:“当然不算完!反革命在武汉大屠杀以后的日子,毛泽东同志带领革命的士兵、工人和农民举行了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朱德同志带领南昌起义的部队转战湖南。他们在井冈山上会师了,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工农红军,建设了革命的根据地。今后要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叫无地少地的农民们都有田种!”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第25节
江涛从济南回来,秋天过了,父亲还在病着。他把运涛的事情一五一十对父亲说了。母亲割完谷,砍完玉蜀黍,正在场上碾场扬场。他又帮着砍了豆子,摘了棉花。做着活,母亲问他:“江涛!你哥哥可是怎么着哩?”他只说:“还在监狱里。”母亲天天想念着在狱里受苦的儿子。
收完了秋,江涛去找朱老忠,说:“忠大伯!家里出了这么大的变故,上不起学校了,我想退学。”朱老忠说:“莫呀,孩子!上济南剩下来的钱,你先拿去。家里,我再想法子借钱,叫你爹吃药治病。咳!赶上这个年头儿,不管怎么,也得托着掖着闯过去。”江涛说:“那只够今年的,明年又怎么办呢?”朱老忠说:“不要紧,孩子!有大伯我呢,只要有口饭吃,脱了裤子扒了袄,也得供给你在师范学堂毕了业。”
江涛回到保定,第二天洗了澡理了发,换上身浆洗过的衣裳,去看严萍。一进严知孝的小院,北屋里上了灯,老伴俩正在灯下说闲话。严知孝见江涛进来,问他:“运涛怎么样?”
江涛把小包袱放在桌子上,说:“他判了无期徒刑!”
一听得江涛的声音,严萍在她的小东屋里发了话:“江涛回来了!”东房门一响,踏看焦脆的脚步声走过来。她弯下腰,两手拄着膝头,对着江涛的脸说:“你瘦了,黑了!”又伸出指头,指着江涛的鼻子说:“是在灯影儿里的过?”
妈妈看严萍这么亲近江涛,满心眼里不高兴,撅起嘴来说:“长天野地里去跑嘛,可不黑了!”妈妈是个高身材的乡村妇人,脸上显出苍老了,高鼻准,下巴长一点。说着,走到桌旁,解开包袱看了看说:“看江涛带来什么好东西,嘿!
通红的枣儿!”
严萍拈起一枚小枣,掏出手绢擦了擦,放在嘴里,咂着嘴儿说:“可甜哩,没有核儿。”她抓起几个枣,放在父亲手心里。又用手绢包起一些,藏下自己吃。
严知孝取出眼镜盒,戴上眼镜看碑帖,说:“小枣,别有风趣。大明湖的碑帖嘛,看来没有什么可贵之处。”江涛说:“枣儿是全国有名的。碑帖,也许是没买着好的。”
严知孝摘下眼镜,捏起一枚小枣放进嘴里。说:“你没见过张秘书长?不能维持一下?”
江涛说:“他说案子属省党部直接处理,探望一下可以,别的,他们无权过问。已经定了‘无期徒刑’。”
严知孝说:“咳!活跳跳的个人儿,一辈子完了!”
严萍斜起眼睛看着父亲,说:“哦,那将来还有出来的一天。”
严知孝冷淡地说:“什么时候出来?”说到这里,他又停了一下。
严萍说:“将来红军势力大了,统一全国的时候。”
江涛对着严萍摇了摇头,不再说什么。严知孝抬起手拢了一下长头发,说:“这话,也难说了。”他背叉起手,在地上走来走去,拈着浓黑的短胡髭,又说:“昨天,还是被人捉住砍头的,他们就需要与别人合作。今天,他们把权柄抓在手里,就不需要合作了,要砍别人的头了。过了河就拆桥,看来‘权’‘势’两字,是毁人不过的!”
江涛说:“如今他们有权有势,刀柄在他们手里攥着嘛!”
严知孝说:“他们也要防备刀柄攥在别人手里的时候。一个不久以前还是被人欢迎过的,昨天就在天华市场出现了‘打倒刮民党’的传单!”
严萍说:“他们成了反动派嘛!”
江涛说:“他背叛了群众……”
严知孝说:“咳!如今的世界呀!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你征我伐,到什么时候是个完?过来过去总是糟践老百姓!”
严萍说:“我看谁想当权,就把最大的官儿给他们坐,不就完了?”
严知孝绷起脸说:“没有那么简单,他们都想坐最大的官,有没有那么多的大官给他们坐?”一句话说得一家人都笑了。
严萍坐在父亲的帆布躺椅上,转着眼珠想:“可就是,我就没有想到。”
“我看龙多不治水,鸡多不下蛋……国家民族还是强不了!”妈妈不凉不酸地说着,走了出去。不过是插科打诨,取个笑儿罢了。
严知孝说:“不管怎么的吧,咱是落伍了。政治舞台上的事情,咱算是门外汉。干脆,闭门不问天下事,心里倒也干净。”
严知孝又问了家乡的年景呀,庄稼呀,一些老家的事情,又问老家的人们。他不常回家,每次从老家来了人,他总是关心地问长问短,而且问得很详细。妈妈又煮了枣儿来,说是搁了糖的。吃了糖枣,严萍叫江涛到她的小屋子里去。江涛一进门,转着身子看了看,见屋里没有什么新的变动,心上才安下来。坐在椅子上,转着黑眼瞳呆着。
严萍看他老是不说话,问:“怎么,又在想什么心事?净好一个人静默,也不闷的慌?”
江涛说:“静默就是休息。”
严萍说:“你还不如说,静默就是思想。”
江涛说:“能够静默下来,当然是好。一个人坦坦然然地想个什么事情,有多么好?不过有时,有一种逆流冲动着你,不让你静默下来。”
严萍说:“我就不行,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多么愁闷。什么力量不让你静默?”
江涛说:“革命!”
严萍说:“又想起革命来。想到什么问题?”
江涛说:“祖辈几代:祖父的,父亲的,哥哥的,我的……没有一个暴风雨般的革命运动,不能改变这受压迫的道路。”
严萍说:“你说得不错!”
江涛再也不说什么,定住黑眼珠静默起来。
严萍拿眼睛呼唤他几次,拿下巴点了他几次,他都没有知觉。她把两个巴掌伸到他的耳朵上一拍,说:“嗨!你发什么呆?”
江涛笑模悠悠地说:“想起运涛,一个人坐狱,几家子人担心!”
严萍说:“几家人?你家、我家……”
江涛说:“还有忠大伯家、春兰姑娘家……”
严萍不等江涛说完,问:“春兰是谁?”
江涛说:“春兰是运涛相好的人儿,她聪明活泼又进步。打算等运涛回来跟她结婚呢,这样一来……”说着话,他又沉默下来。
严萍听说运涛要长期住狱,那个钟情的姑娘还在等着他,对春兰发生了很大的同情心,屏住气凝住神,睁着眼睛听着。可是江涛睁着大圆圆的眼睛,不再说下去。严萍等急了,说:
“你可说呀!”
江涛把运涛和春兰的交情叙述一遍,又说:“春兰帮着运涛织布,两个人对着脸儿掏缯,睁着大眼睛,他看着她,她看着他,掏着缯着,就发生了感情……”
严萍听着,笑出来说:“两个人耳鬓厮磨嘛,当然要发生感情。”说着,腾地一片红潮升到耳根上。
江涛继续说:“有一天晚上,我睡着睡着,听得大门一响,走进两个人来。我猛地从炕上爬起来,隔着窗上的小玻璃一看;月亮上来了,把树影筛在地上。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是运涛,女的是春兰……”
严萍问:“妈妈也不说他们?”
江涛又说:“看见他们走到小棚子里去,我翻身跳下炕来,要跑出去捉他们。母亲伸手一把将我抓回来,问:‘你去干什么?’我说:‘去看看他们。’母亲说:‘两个人好好儿的,你甭去讨人嫌!’这时,父亲也抬起头来,望着窗外看了看,伸起耳朵听了听,说:‘你去吧!将来春兰不给你做鞋做袜。’”
严萍听到这里,喷地笑了,说:“怪不得!你们有这么知心的老人。看起来运涛和春兰挺好了,运涛一入狱,说不定春兰心里有多难受哩!”说着,直想掉出泪来。
两个人正在屋里说着话,听得母亲在窗前走来走去。江涛转个话题问:“我去了这些日子,你看什么书来?”严萍坐在小床上,悠搭着腿儿,说:“我嘛,读了很多书。真的,《创造月刊》上那些革命小说,我看了还想看。数学什么的,再也听不到耳朵里。”
江涛说:“按一个学生来说,把功课弄好,书也多看,才算政治上进步哪!要多看一些社会科学的书,不能光看文艺小说。”每次,他都对严萍这样谈,希望她多读一些政治书籍。他觉得从他跟严萍的关系上来说,他有责任推动他们的思想走向革命。
听得妈妈老是在窗前蹓来蹓去,江涛才从屋里走出来。严萍也在后头跟着。出了大门,江涛悄悄地问:“登龙常来玩吗?”
严萍直爽地说:“差不多,他每个礼拜日都来玩,来了就咕咕叨叨,蘑菇一天才走。妈妈还给他做好东西吃。”
江萍说:“这人不喜欢读书。”
严萍说:“他正在学武术,可着迷哪!练什么铁沙掌呀,太极拳呀,他说将来要学军事。他说将来绝对不向文科发展,要做些对国家民族有益的事……”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着,走到西城门,她又楞住,笑了说:“怎么办?你送我回去吧,叫我一个人回去?这么黑的天。”
江涛又把严萍送回门口,在黑影里,严萍拍拍江涛的胸脯,看了看他的脸,说:“好好儿的,把运涛的事情放开吧,不要过分悲伤。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革命工作要紧。”江涛说:“是的,革命可以改变被压迫人们的命运!”严萍听了,也点点头。江涛站在门口,听她走进去把门插上,才走出胡同。街上行人稀少,路灯半明半暗,呆呆地照着。路面不平,他独自一个人,一步一蹶地穿过冷清的街道走回来。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第26节
白色恐怖的年月过去,江涛眼睁睁看着哥哥被关进牢狱里,心上象钉上苦难的荆棘。他寒假暑假回家帮助父亲料理家事,参与劳动,一开学就又回到保定。每天下午完了课,就到校外去工作。夜晚钻进储藏室,把小油灯点在破柜橱里看书。他读完了组织上发来的《社会科学讲义》,心上好象开了两扇门,照进太阳的光亮。
他们从学校到工厂,从工厂到乡村,偷偷地把革命的种籽撒在工农大众的心上,单等时机一到,在平原上掀起风暴。
那年秋天,上级派人到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视察工作,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决定发动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进攻。到了冬天,组织上派江涛回到锁井镇上,去发动农民,组织反割头税、反百货税运动。
他动身的那天早晨,天上垂下白腾腾的云雾。马路上、屋顶上、树枝上,都披着霜雪树挂。江涛走到严萍的门前,伸出手去,想拍打门环,又迟疑住,想:“还是不告诉她吧!”停了一刻,才抽回手走出城来。
走不多远,天上卷起绞脖子风,推着他一股劲往前跑,想停一下脚步也难停住。又飘起雪来,急风绞起雪霰,望人脸上扑,浑身冷飕飕的。江涛脸上冻僵了,鼻子也冻红了。
一大团一大团的雪花从天上旋卷下来,纷纷扬扬,象抖着棉花穰子。雪片洒在地上,唰哩哩地响着。
一直跑到天黑,跑得满身大汗,两腿也酸软了,他想找个地方休憩休憩。稍停一会,就觉得身上冰凉。看那边象是几棵树的影子,他走了一节地,还是看不见村庄树林,又啃啃哧哧地走回来。想蹲在道沟的雪坡下避避风,可是两条腿硬挺挺回不过弯了。棉袍子冻上一层冰,象穿上冰凌铠甲,一弯腰身上就咯吱乱响。他搓着手,抬起头看了看天上,灰色的云雾没有边际。浑身楞怔了一下,想:“唉呀!这是走到什么地方?什么方向?”歇了一会,并没减轻疲乏,觉得身上潮湿得厉害,索性咬起牙关,一股劲地往前跑。一直跑到深夜,通过飞扬的雪花看得见贾老师的村庄了。去年春天他才来过,还记得小梢门前头那棵老香椿树,树下那口井,井台上那根石头井桩。门朝村外开着,对着一片田野。如今野外一片白,柳树上驮着满枝白雪。
他在小梢门底下停住脚步,拍打拍打门板,听不见动静。又拍了两下,还是听不见动静。一天走了两天的路,直觉得浑身酸痛,想坐在门坎上歇一下。抖动了一下肩膀,身上的雪象穰花一样纷纷落在地上。忽然间村西南传来了马蹄声,嚓嚓嚓地越来越近,骑着马的黑衣裳警察,冒着风雪跑过去了。他身上一机灵,想:“为什么在冬天的深夜,刮着风下着大雪,会有骑马疾驰的警察呢?”按一般习惯,他该马上走开。可是今天,他已经跑了一天路,身上太乏累了。一天水米不落肚,很想喝点汤水润润肚肠。他不加思索地连连拍打着门板,仄起耳朵一听,屋顶上有踏雪的声音。他想抬起头望望,有什么人在屋顶上走动。才说移动脚步伸出头去,猛地克嚓一声,一把明亮的粪叉从屋檐上飞了下来。他机警地闪进角落里。紧接着,又嗡地一把禾叉飞到他的脚下,掘起地上的泥土,迸了满脸。他一下子楞住,皮肤紧缩了一下,

![[网王+樱兰+十二国记]既宅又腐,开始有谱封面](http://www.38xs.net/cover/1/129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