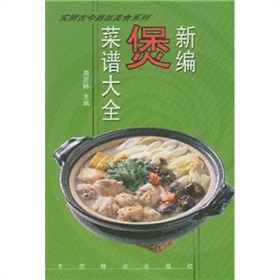红旗谱-第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又从滹沱河跑到唐河。不久,瘦得凹着两只大眼睛了。
这时夜快深了,屋里没有灯,人们都睡着,操场上静静的,全城没有一点声音。贾老师睁开晶亮的眼睛,看着耸立在夜暗里的古圣殿的轮廊,看着重楼上飞檐斗拱的影子,拍着嘉庆的肩膀说:“嘉庆!不要哭,你还年轻,应当更好地锻炼……”他慢慢走过来,把手搭在张嘉庆的肩头上,喃喃地说:“要锻炼得能够独立思考问题、决定问题,能够独立工作,那才是一个坚强的干部。目前,我们党就是缺少这样的干部。”他又歪起头看着嘉庆的脸,说:“要知道,你应该勇敢地向前看,不应该是个用眼泪来洗脸的人。”
张嘉庆忙用袖子擦去眼泪,说:“是。”
贾老师说:“我把你介绍给江涛,他和你一样,也是在党的教养下长大的。这人在工作上英勇、机智,性格也挺浑厚。你通过他接上关系,我要在介绍信上注明,等你年岁一到,立刻转为党员。江涛在去年已经转党了。他一定好好照顾你……
哎!他有个女朋友,你见过吗?”
嘉庆立刻破涕为笑,说:“我见过,她参加过反割头税运动。长得细身腰,长身条,黑眼珠儿特别的黑,白眼珠儿特别的白……”
贾老师又说:“是呀!我给你写个信,叫他们想办法帮助你考上第二师范。你的生活问题、读书问题,就都解决了。”张嘉庆说:“我知道江涛是个能干的人,和他们一块工作,一定是很愉快的。”
贾老师说:“第二师范供给膳宿费,不够的话,可请求组织上帮助,这也在信上注明。你再好好读几年书,文化水平低的人,就很难在政治上很快提高。”张嘉庆问:“你呢?”贾老师说:“我是不能动的,我还要在这里坚持。我要采取合法存在非法活动的方式工作下去!”
贾老师说着,站在张嘉庆的背后,用手指抚摸着张嘉庆的下颏,嘴巴上的胡子,已经硬起来了。他说:“记住,同志!光凭热情不行呀!一个好的革命干部,他需要文化知识——
各方面的知识。需要通达事理,了解社会人情……”
张嘉庆听到这里,从椅子上站起来,背靠着窗台说:“我不同意江涛早早有了爱人。”
贾老师直着眼睛问他:“嗯,为什么?”
张嘉庆说:“我觉得,这样对女同志并不好。再说,做为一个女人,多痛苦呀!她要管家,要生孩子,要……不,应该让她们独立,象男人一样的革命,在社会上做些事业。”
贾老师说:“可是她们早晚要结婚的。当然,一个好的女同志,她不一定漂亮。内心的美丽,比长得漂亮更为可贵。”说着,又纳起闷来:“他为什么这样同情女人?显然是受了一种什么刺激。”
张嘉庆是张家的独生儿子。母亲生下他的时候,唱了两台大戏,喜幛贺联摆满了半条街。酒席摆了一院子,送礼的人们,喝酒猜拳的声音,传到二三里路以外。他长大了,只许跟大娘叫娘,跟母亲叫“小娘”。生他的时候,母亲只有十七岁,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母亲晚上和父亲在一块睡觉,白天和长工们下地做活,摘花割谷,在磨房里碾米、磨面,给大娘洗衣服。
大娘不让母亲奶嘉庆,雇了个奶母。说也奇怪,嘉庆渐渐地不象母亲了。母亲哭着说:“大娘使了魔法,把我的孩子脱形了!”人们抱起嘉庆来端相端相,说:“可就是,真也奇怪!”
张嘉庆长大了,大娘不叫他和母亲见面。有时母亲背着筐下园子拔菜,在路上碰上他,就流下两行泪,抚摸着孩子的头顶说:“儿呀,儿呀,你快长大!长慢一点,娘就等不得你了!”说着,用破袖子擦着眼泪。
奶母对嘉庆说:“穷娘嫁到财主家里,一下轿大娘横着皮鞭站在天地神牌底下。装腔作势,在娘脊梁上抽了一百鞭子,立过家法。”还说:“别看大娘吃得强穿得强,生身的母亲是穿破衣裳的。”
张嘉庆长大了,母亲青春的年岁也过去了,父亲又娶了个小娘来。小娘长得更漂亮,把母亲忘在脖子后头。母亲再也见不到父亲的面,从此用泪洗脸,就泪吃饭。母亲的脸,渐渐地瘦了黄了,长上横纹。她不愿这样地活下去,在张嘉庆逃跑以后,也就离开张家,上北京去,帮人做活,当起佣人来。
张嘉庆的家庭历史情况,贾老师在他入团之前就知道。看他阶级出身不平常,对他加强阶级教育,培养成一个赤色的战士。也曾对他说过:“象你母亲这样的人,何止千千万万!
你是受压迫的人生的儿子,你要为他们战斗一生!”
夜深了,嘉庆骑了一天车子,身上累了。激动的感情,又慢慢平静下来。用眼泪洗净了心情,倒在床上睡着了。贾老师对着深夜,对着静寂的院落出神。他在这个地区工作了将近七年,走过不少村庄,接触了不少革命的农民,培养了干部,教育了青年一代。如今,敌人要追捕他。他对家乡有很深的留恋,嘴里不住地念着:“家乡啊,亲爱的家乡!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凶狠,我要和家乡的人们并肩作战,度过这白色的恐怖!”
为了送张嘉庆走,贾老师第二天早起了床。点上灯,给江涛写了信。贾老师把张嘉庆的衣服包好,叫他起来说:“棉衣和被褥,我告诉这里同志们,给你捎去。”
张嘉庆说:“我要是考不上呢?”
贾老师说:“考不上也不要紧,我经过保定的时候,告诉组织上,安排你的工作。”
张嘉庆点了一下头,“唔”了一声,带上自己的东西,走出了学校。出了门,他又回过头去看了看,心上依依不舍的,不忍离开他的母校。天刚薄明,他们趁着夜暗,沿城根走到西北角上,爬过城去。贾老师说:“路上渴了喝壶茶,别可惜那么一点钱。出了门一闹起病来,花钱更多。”张嘉庆说:
“是!我记住了,你回去吧!”
张嘉庆跳下城墙,走了一段路,回头看了看他住过几年的城堡。贾老师还独自一个人站在土岗上,呆呆地望着他走远。他要亲眼看着年轻的同志脱离险境。张嘉庆回过头来,看着他严峻的形象,一步一步地走远。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第41节
保定市在小清河和京汉线交叉的地方,离北京三百七十里。河水缓缓地流着,流过丘岗,流过平原,流过古老城堡的脚下。流过白洋淀,和大清河汇流,流向天津,流入渤海。
这座小城市,在河北平原上,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当时有十五万人口。民国初年,在这里建下军官大学,为军阀混战种下了冤孽。狭窄的街道上,满铺着石块,街坊上大部分是上世纪留下的木板搭。有大车和帆船把粮食、兽皮、水果,运往京津。再把洋货——工业品运到乡村里去。
这里有十三所学校,一所大学。省立第二师范就在西城的角下,这是一个中级学校,当时全校有三百多同学。一条小清河的支流,从旁边流过。江涛在这里受过四年师范教育,在保定市有了四年工作历史,是保属革命救济会的负责人,二师学生会的主任委员。暑假期间,江涛被选在学生公寓委员会里工作——沿着旧习,每年暑期招生,学生会筹办临时公寓,招待乡村里来投考的学生们。
江涛得到支部负责人夏应图同志的同意,把嘉庆安排在养病室里。每天演算术、写小字,准备投考的功课。江涛分派厨工里的“同志”,按时把病号饭送去。在这个期间,第二师范经常住着不花栈费的客人。
江涛为了解决嘉庆的生活问题,带他去找严萍,她是救济会的会员。一进门,严萍刚下课回来,看见嘉庆就问:“张先生来了?少见!”张嘉庆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称呼,睁开大眼睛看着她。严萍回过头来笑着说:“我还不知道你是个神枪手哪!”开了门,在自己小屋子里招待他们。她洗了手沏上茶,从父亲屋里拿了一盒香烟来。
张嘉庆一见到严萍,就悄悄地把眼光避开。他住在小城市里惯了,没接触过女人,今天遇到严萍,不敢正眼去看。视线一碰到严萍的眼睛,觉得她眼睛里射出来的光芒,象锥子一样尖锐,好象隔着胸膛,能看透别人心血的吞吐。张嘉庆象一只被苍鹰拿败了的百灵,把脑袋钻在翅膀底下,再也不敢鸣啭。象有千丈长绳缠在他身上。其实是严萍一见到江涛,就心上高兴,脸上泛出明媚逼人的光辉。
张嘉庆抬起下颏看这间精致的小屋:屋子很小,只放开一个书架,一张书桌,一只小床。小床上铺着大花被单,小窗上挂着花布窗幔。墙上挂着一个银色的镜架,是严萍的放大像。她学着电影明星的姿态,仄起脸儿在笑。嘉庆一看,心上很是讨厌,他不喜欢这样姿态的女同志。
江涛把贾老师的意见告诉她,她斯文礼貌地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江涛面前,一杯放在嘉庆面前。撕开烟盒,递给江涛一支香烟,嘉庆摇了摇头,严萍就不再给他。顺手划根火柴,给江涛把烟点着。嘉庆心里暗想:这是什么女人的作风?
严萍说:“我知道张先生好枪法。可是,我也听得说过,你的家庭……”她看嘉庆不象个穷学生,知道他的家庭是个大地主。
嘉庆楞楞青青地说:“有家就不遭这个难了!”他觉得被一个女人看过来看过去,浑身挺不自在,尽把眼睛看着屋角里。
江涛把嘉庆的经历告诉严萍,严萍轻轻笑着说:“这就是了,近来常在报纸上看到,有的青年人为了革命离开家庭。也有的家庭怕吃革命连累,抛弃自己的儿子。”看嘉庆有不耐烦的神色,紧跟上说:“革命就是家,让我们想想办法看,可以在内部进行募捐。”
江涛笑了说:“好!就请严小姐解决这个问题吧。”
他们商量完了事情,又谈到文学上,严萍侃侃地谈个不停。嘉庆也谈了些革命文学上的意见,他说:“我一念起革命的诗歌,心上就热烘烘的。”严萍说:“我很喜欢浪漫主义的作品,看了那些热情的小说,好象驾上云儿,飘飘呼呼地走向革命。”
张嘉庆问:“你正在读什么书?”
严萍说:“《毁灭》。”
张嘉庆问:“你还读了些什么苏联小说?”
严萍说:“还读了《十月》,我很喜欢革命的热情。十月革命成功了,被压迫的人们站起来了,得到政权和土地。我也很喜欢诗歌。”说着,她扬起手朗诵了一首诗:
太阳没了,
在那西北的天郊。
满天的霾云,
正在暗地里狞笑。
…………
…………
严萍挥起两只手,用音乐般的音调唱着,又孩子般地笑了。张嘉庆看她天真的举动,很是喜欢。文学把他们的感情联系起来,张嘉庆再也不感到拘束。江涛拉开抽屉,拿出严萍的画报来看着。等他们谈完了,才说:“文学嘛,咱是门外汉。”
严萍说:“你是社会科学家嘛,就不再喜欢文学了!”
他们又说了一会子革命工作上的话,江涛和嘉庆才走出来。一离开严萍的眼睛,就象割断了嘉庆身上缠的绳索,觉得轻松起来。大拇指朝江涛一弹,打了个响梆儿,挤巴挤巴眼睛说:“不错!”
江涛郑重其事地说:“那是一个好同志,可不要开玩笑。”
张嘉庆说:“是呀,那是首要条件,不过……不过……做为一个‘同志’,我给你提个意见:象你,应该有一个身体雄壮的爱人,她好象一个勇士,时刻不离地保卫着你,你就不至于被捕了。老实讲,老实讲……”他咽下一口唾沫说:“美丽……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
江涛拍了嘉庆一掌,说:“净瞎说白道,我情愿!”
张嘉庆睁开大眼睛,把右手在左掌上一拍,说:“唉!算了!你们两好碰一好儿,咱算白说!”
今年有二千四百人下场,学校只考取一班,形势是相当艰险的。张嘉庆鼓着劲考上了头一榜,算是过了第一关。可是二百五十个人,离四十个人还差得远。江涛觉得张嘉庆为了工作,把功课耽误了,实在难保证他闯过第二关。为了完成党的任务,应该克服的困难,尽力克服,江涛又去请教夏应图。
经过老夏同志的指导,总结了历年共青团员在考学斗争上的经验。江涛又把嘉庆带到严萍家里,叫她拿出一身衣裳,把嘉庆的衣服换下来。江涛和严萍提着桶抬了水来,给他洗净。严萍扯起褂子看了看,脊梁上破了个三角口子,小口袋扯破了,搭拉下来。放在盆里洗着,说:“你这方面就得好好儿学习江涛。你看他,一天早晚身上衣服整整齐齐。一年到头儿,头上脚下不落灰尘。”
江涛也说:“你穿着这么脏的衣服,能考得上学校?”
张嘉庆嘻嘻笑着,拎起贾老师给他的那件布衫一看,和擦桌子布一样,发散着汗臭。他捏着鼻子放下,觉得叫严萍给他洗这么脏的衣裳,很觉过意不去。心里说:“真是,丢人现眼!”
严萍说:“在锁井见你的时候,还穿得漂漂亮亮的。这早晚,你学得邋邋遢遢。”
张嘉庆说:“那是什么时候?那时候还是少爷,这早晚变成无产阶级了!”
江涛说:“你得改变这个习惯。”
严萍把一盆洗浑了的水倒出去,说:“这有一车泥!”她在喘着气,洗衣板把她细长的手指磨得通红。打肥皂啊,搓呀,涮呀,一件衣服洗了几盆水。她说:“别看我身子骨儿单薄,并不怕劳动。我就是胆小,爱害怕。那年秋天,有个同学把一条毛毛虫放在我的书桌上,吓得我一天不敢去上课。一想起来,毛毛虫就象在心里鼓弄。我还怕炮声,一听到炮声,就赶紧捂上耳朵。”
江涛说:“那我可不信,那年大年夜里,你一个人摸着挺远的黑路去找我。”
严萍斜起眼睛,瞟着江涛说:“那天晚上,可不是平常的晚上。”
张嘉庆跟上说:“从那天晚上,你们就开始……”
严萍不等他说完,故意岔开话头说:“从那天晚上,我就开始走上革命……你看你,头发那么长了,也不梳洗。多好的衣裳,穿在你的身上,就曲皱得象牛口里嚼的,穿鞋露着脚指头,这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口试的时候,当面一谈就蹭了!”
一阵话搔着张嘉庆的痒处,他不耐烦地说:“得啦,同志!咱俩算是没有缘法,我在你嘴里,算是逃不出去,我那里比得过江涛?”他又指着江涛说:“你看他,两个肩膀一般高,两条胳膊一般粗,两条大腿一般长,两只眼睛一般大,两条眉毛……两只耳朵……”他说话一快,就有些口吃。一股劲地说下去,象放机关枪一样:“象我吧,成天价不干不净,马马虎虎。不过读书不读书吧,为了找个吃饭的地方,才考这‘第二客栈’,好住着店开辟工作呀!”
一下子把严萍说了个大红脸,她怕张嘉庆批评她小资产阶级意识,再也不敢吱声。严萍把衣服洗好晾上。掏出两块钱,放在小床上,说:“去,洗个澡理个发,买双鞋来。口试的时候,好去出头露面呀!”江涛和嘉庆带上钱,走出门来,张嘉庆拍着江涛的肩膀说:“同志!你算憋住宝了!”江涛摇摇头说:“少说废话,你不是主张中国革命成功了,再找爱人吗?”张嘉庆说:“当然哪,中国革命不成功,我连想也不想。”两个人洗了澡理了发,到鞋店里试着买了双鞋子。把新鞋子穿在脚上,那双旧鞋子,又破又有气味,放在鞋店里玻璃门前的花砖地上,抬起腿就走了。
严萍把张嘉庆的衣裳折叠整齐,坐在椅子上压得平平正正。张嘉庆穿在身上,浑身上下干净利落。严萍拍拍他的肩膀,捵捵衣襟说:“看,怎么样?小伙子漂亮了吧!明天口试的时候,一过眼就取上了!”
江涛、严萍、嘉庆,在院里洗衣服的时候,严知孝和老伴在北屋里有一场小小的争论。妈妈说:“闺女大了,也该有个安排。”又指着窗户

![[网王+樱兰+十二国记]既宅又腐,开始有谱封面](http://www.38xs.net/cover/1/129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