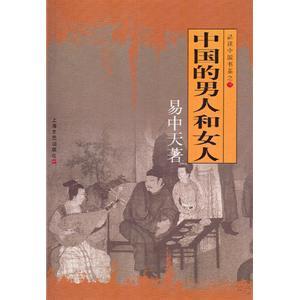爱恋中的女人-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向前伸着。她轻巧地出了院门,穿过草地,到了水边,站在那儿就像一尊用象牙和青铜雕铸的小雕像。她拿下『毛』巾看着那些吃惊的天鹅,它们刚从水中钻出来。跟着跑出来的是布雷德利小姐,她的泳衣是深蓝『色』的,像一朵轻柔的大梅花。接着是吉拉尔德,一条红『色』丝绸围巾围在他的腰间,胳膊上搭着一条『毛』巾。看起来他想在阳光下显示一下自己,悠然地走来走去,还时不时地大笑。他『裸』『露』的身子白而强壮。再下一个是乔舒亚爵士,他披着外套,最后一个是赫米奥恩,她身着紫『色』丝绸披风,迈着大步,挺着身子,用一种很优雅的姿势走过来,她头上的丝带白紫相间。她的身材挺拔修长,大腿雪白而漂亮。当她迈着矫健的步伐向前走时,披风抖了起来,人们从她那儿体会出一种静穆之美。她悠然严肃的穿过草坪到了水边。整个动作的感觉好似在回忆起什么似的。
在通向山谷的梯田上有三个池塘,在太阳底下显得宽阔、美丽、清澈。池水冲出一堵很小的石墙,没过一些小石砾,水珠落在下一个池塘的表面。天鹅已经游过去,到了对岸。一股股清香从芦苇那边散发过来,微风吹拂着皮肤。
吉拉尔德和乔舒亚跳入水中,游到池塘的尽头。然后他爬上去,坐在石墙上。小个子的伯爵夫人也跳下水,好像一只老鼠似的游过去,到了吉拉尔德那儿。两个人都双手抱在胸前,在太阳下说笑着,笑个不停。乔舒亚也向他们游过去,站在他们眼前,头和肩膀『露』出了水面。接着赫米奥恩和布雷德利小姐也游来了,他们在岸上坐成一排。
“他们难道不可怕吗?他们真不可怕吗?”古德兰说,“他们看上去像不像一种动物——蜥蜴?他们就象是大蜥蜴。你以前有没有见过像乔舒亚那样的人?真的,欧秀拉,他属于原始世界,在那个世界爬来爬去的大蜥蜴。”
古德兰很失望地看着乔舒亚爵士。他站在水里,上身『露』在水面上,他的眼睛被他灰白的长头发遮住了,他的脖子缩在宽厚的肩膀里。他正在跟布雷德利小姐说话。她圆鼓鼓、胖乎乎、湿漉漉的坐在岸上,看起来像动物园里正在摆动的海狮,马上就准备到水中大展手脚似的。
欧秀拉默默地注视着。吉拉尔德正在赫米奥恩和意大利女人之间哈哈大笑。他让她想起了酒神狄奥尼索斯。因为他有金黄的头发、结实的身材,笑起来也前摇后晃。赫米奥恩身子靠向他,一动不动,形态优雅,却原形毕『露』,令人吃惊、害怕,好象她对自己做的事情一点都不负责任一样。他知道她身上蕴藏着一种危机、一种疯癫,好像痉挛。但他却更加开怀大笑,而且还时不时地把身子扭向娇小的伯爵夫人。她则仰着头,红着脸地看着他。他们又跳下水,像一群海豹一样游泳。赫米奥恩游得非常带劲儿而且忘我,她的动作舒缓而有力。帕勒斯特双手挥动,拍击着水面、只有白『色』的身影依稀可辨。接着他们一个个地上岸,从原路回到屋里。
但吉拉尔德还磨蹭了一会儿,想找话与古德兰说。“你不喜欢到水里去吗?”他说。
她用一种难以捉『摸』的眼视缓缓地注视着他,他毫不掩饰地站在她面前,全身湿漉漉的。
“我很喜欢。”她回答说。
他停了一会儿。她做出解释。
“你会游泳吗?”
“是的,我会。”
他还是没问她为什么没去游泳,他觉得她的脸上挂着嘲讽。他第一次很生气地走开了。
后来,等他穿戴整齐,重新显出一个英国年轻绅土的风度时他又问她:“那你为什么不愿下去游泳呢?”
她犹豫了一下,不喜欢他这么问她,接着她回答说:“因为我不喜欢集体活动。”
他笑了。他的脑中一直回响着她的话。
她的话正对他的口味。不管他是否承认,她就是他真正的世界。他想达到她的水平高度,去实现她的愿望。他知道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她的标准。在天『性』上,他和别人都不一样,不管其地位高低。吉拉尔德情不自禁地想达到她的标准。他一定要付出最大的努力以实现她对一个男人、一个人所提出的要求和标准。吃完午饭,别人都离席了,只有赫米奥恩、吉拉尔德和伯基想把话说完而没有走。他们正在就人类的新形态和新的世界问题而展开讨论。总的来讲,这些问题特别抽象和空洞。试想这个旧的社会形态在破坏和摧毁,那么什么会在这混『乱』中出现呢?这个伟大的社会思想用乔舒亚的话来说就是人类的平等。“不,”吉拉尔德说,“思想是要每个人都承担各自的职责——让他做他该做的,以及他自己高兴的相结合的原则,就是手中的工作,只有工作、出产品的工作才能让人们联合起来。那是机械化的,不过社会也是机械的。没有工作,他们就可以独自自由地做他们想做的。”
“噢,”古德兰叫道,“那么我们就不用要名字了——我们应该像德国人一样——只有总管和副总管。我们可以想象——我是煤矿经理克瑞奇大人——我是议员罗迪斯夫人。我是美术教师布兰哥温小姐。那还真不错。”
“事情会好办得多,美术老师布兰哥温小姐。”吉拉尔德说。“什么事情,煤矿经理克瑞奇先生?比如说你和我之间的关系。”
“是的,比方说。”意大利人大叫道,“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那是非社会『性』的。”伯基讽刺说。
“正是,”吉拉尔德说,“在我和一个女人之间与社会问题没有关系,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只是十镑钱的事”。伯基说。
“你不承认『妇』女的社会存在吗?”欧秀拉问吉拉尔德。“她是双重的。”吉拉尔德说,“从研究社会问题着手,她是一个社会存在。但对于她个人,她是一个自由的人,她要做什么是她自己的事。”
“那么要调节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困难吗?”欧秀拉问。“哦,不。”吉拉尔德说,“她很自然地调节自己——这种事情到处可见。”
“你现在是不是笑得太早了?”伯基说。
吉拉尔德有点生气地皱了皱眉。
“我在笑吗?”他说。
“如果,”赫米奥恩最后说,“我们能意识到我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都是兄弟。——剩下的就无关紧要了。那时就不会有挑『毛』病,不会有嫉妒,也不会争权夺利,那只是在毁坏,毁坏一切。”
这些话被默默地接受了。大家几乎同时从桌旁站起来。但当别人都走后,伯基转过身,非常庄严地声明:
“完全相反,恰恰相反,赫米奥恩,我们在精神上是不同的,不平等的——只有社会地位的差别才是建立在偶然的物质基础上。我们可以是抽象的数学上的平等。如果按你所讲,每个人都有饥渴、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两条腿、在数量上我们都是一样的,但在精神上,是完全不同的,既不能说平等,又不能说不平等。你必须按照这个去认定一个状态。如果你把平等用在一个抽象的数学范围之外,那你所说民主完全是谎言——你的人们之间的手足关系也完全是骗局。我们都是先喝牛『奶』,然后吃面包和肉,我们都坐在小汽车里驾驶——这就是‘手足之情’的开始和结束,但不是平等。”
“但是我,我自己,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和别的男人、女人讲平等?在精神上,我就像一颗星星,和别的星星相距甚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状态,一个人不会比另一个人好多少,并不是因为他们平等而是因为他们内在的本质不同,所以也没必要比较他们。在你开始比较的那一阵子,你会发现一个人要比另一个人好得多,你所能想象出的所有不平等都是自然存在的,我希望每个人都分享世界上的商品,这样我就能摆脱他的哀求,我就能告诉他,现在你已有了你那一份,好,你这个一张嘴巴的傻瓜,自己照顾自己,别来打扰我。”
赫米奥恩翻着白眼斜睨他。他可以感到他所讲的引起了她的恼怒和厌恶,这是从她无意识中涌出的强烈的气愤和极度厌恶的黑『潮』,她的无意识的自我听到了他的话,而在意识上她好象已经聋了,根本没有注意他的话。
“听起来太狂妄自大了,鲁伯特。”吉拉尔德很和蔼地说。赫米奥恩奇怪地嘟囔了几句,伯基站后了几步。
“是的,就算这样。”他突然说,声调变了音,但十分固执、盛气凌人,说完转身就走了。
但后来他感到良心有些不安,他对可怜的赫米奥恩太不近情意了,他想弥补自己的错误。他伤害了她,对她报复太重,他想与她重修旧好。
他去了她的房间。这个房间僻静而舒服。她正在桌前写信。他进来的时候,她呆呆地抬起头,看到他走到沙发前面坐下,她又继续低头写她的信。
他拿起一本以前他一直在读的书,开始很详细地看作者简介,他背对着赫米奥恩。她不能继续她的信,她的整个儿思绪『乱』了,黑暗在扑向她,她努力挣扎,想尽力控制自己的想法,就像一个游泳的人在漩涡里拼挣一样。不管她怎样尽力,她还是垮了,黑暗漫漫地吞没她,她觉得心都要裂了。这种可怕的紧张气氛越来越强,这是最可怕的痛苦,好像被关在高墙里。
然后,她便意识到他的存在就像一堵高墙,正在毁掉她,除非她冲破它,不然会悲惨可怕地受堵而死。他正是那堵墙,她必须推倒它——她必须推倒眼前的他,他这个可怕的障碍将阻碍她前进,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分钟,这堵墙,必须摧毁,不然她会悲惨地死去。
可怕的震动传遍了她的全身,好象触电一样,她好象被高压电流击中,她很清楚地意识到了他静静地坐在那儿形成了一种不可想象的可恨的阻碍,就是他无声而弯曲的后背和他的后脑勺毁掉了她的思想,抑制了她的呼吸。
一阵强烈的快感传遍了她的手臂——她想有一种肉欲的满足。她的手臂颤抖着充满了强力,一种无法估计、不可遏止的强力。多快活啊,有力量是多么让人快活、多么痛快啊!她终于想要满足自己肉欲的冲动了,这种冲动已经上来了,在激烈的痛苦和可怕中她知道情欲所带来的兴奋抓住了她,使她感到极大的快感。她用手握住了桌上的一个石球,那是用来压书用的,很漂亮的蓝『色』。她的手一边滚着石球,一边悄悄地站起来,她的心她像火一样在燃烧。她现在完全处于一种无意识的失魂落魄之中。她慢慢走向他,在他的身后狂喜地站了一会儿。他她似被符咒『迷』住了一样,坐着一动不动、没有知觉。
很快地心中的火焰像电一样传遍了她的全身,给她一种完美的无法描述的快感,一种无法说清的满足。她用尽力量把宝石球砸在他的头上,但因为球被她的手指挡着,所以并不很重。尽管这样,他的头还是碰到了桌子上,石球滑到一边,从他耳边掉了下去。她高兴地浑身发抖,手指的疼痛让她满脸通红。但这一次还不够痛快,她又一次高高地举起手,想再对桌上那已经昏沉的脑袋再来一击,她必须打碎他,她必须在她那痛快的感觉结束以前砸碎它,在没有满足之中把它砸碎。现在一条生命的死与活都不再重要,只要能达到这种完美的快感就行。
她的动作并不很快,而是舒缓的。一个很强烈的意识让他清醒过来,抬起脸,转过去看她。她的胳膊举了起来,手里拿着蓝石球。她用的是左手,他突然害怕的意识到她是个左撇子。他的头一缩,赶紧用那本厚厚的修西得底斯的著作盖在头上挡住。她突然砸下来,差点打断他的脖子,砸碎他的心。
他的心被砸碎了。但他不害怕,他转过脸对着她,推开桌子从她身边跑开。他好象一只被砸的瓶子,觉得自己已被砸成碎片、砸成碎沫。不过他的动作还不算慌『乱』,头脑还冷静、灵魂还完整,没有被击垮。
“不,赫米奥恩,你别砸”他低声说,“我不允许你这样。”他看她高高地站在那儿,脸『色』发青,一副专注的神情,那块石头不紧紧攥在手里。
“走开些,让我过去。”他说着向她走近。
她好象被一只手推了一把,靠在了边上,一直盯着他,没什么变化,就像一个保持中立的天使面对着他。
“没什么好处,”走过她身边时他说,“死不了的,你听见了吗?”在他出去的时候,他一直脸朝着她,害怕她再砸过来。在他有防备的时候,她是不敢随意行动的。因为他有防备,她就失去了力量。于是他走了,就留她一个人在那儿。
她完全僵在了那里,一直保持着那种姿势站立了很久,然后她晃晃悠悠地走向睡椅,躺下来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等她醒过来的,她记起了她所干的事。她只是打了他,像每个女人都会做的那样,因为他折磨了她。她完全正确,她知道,精神上她是正确的。她只是凭着自己绝对清白的良心做了她应做的事,是对的。她是纯洁的,一种莫名的几乎是凶狠的虔诚教徒似的表情停留在她的脸上。
伯基不知不觉但方向明确地走出了房子,径直穿过公园,到了开阔的田野上,上了小山。晴朗的天气现在却变得乌云密布,下起了小雨。他在荒凉的山谷边转悠。在那儿有很多榛树,满地都是鲜花,一丛丛的石楠和枞树正在发出嫩绿的芽儿,到处都湿湿的,山谷底下一条小溪在流。到处已经很昏暗。他意识到他不可能再得到清醒的知觉。他是在黑暗中移动。
但他想要某种东西。他很高兴,在山腰上,那儿被灌木和花丛遮掩着。他想触『摸』这一切,把自己消融在触『摸』中。他脱掉衣服,赤『裸』着,坐在樱草中间,双脚在草丛中慢慢移动。他的腿,他的膝,他的胳膊到腋窝都躺在草丛中。让樱草触『摸』着他的肚子、胸脯是多么惬意!凉爽而神秘。在这触『摸』中他好像已融入它们之中。
但它们太柔软了。他穿过细长的樱草到了灌木丛前,这些不及人高的树丛软而尖的枝条划在他身上。他穿过它们,皮肤扎得生痛,树稍上冷冷的水珠滴到肚子上,柔软尖细的树枝扎在腰上。有一根大树枝狠狠地戳了他一下,但并不太疼,因为他步子迈得小心、慢悠。他躺下来,在密密的清凉的洋水仙中打滚,他平卧在那儿,柔软湿漉的青草覆盖身上,像微风般地柔软,比女人的抚『摸』更加温柔、舒服和美妙。然后他把大腿放在黑黑的枞树枝的刺『毛』上,接着他又感受了榛树枝在肩膀上的抽打和扎刺。他紧紧抓住白『色』的杨树枝,把它贴在胸口,它们光滑、坚硬,长满了结实和疙瘩——这一切都特别美妙,让人心旷神怡,这是任何别的东西都不能代替的。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人如此满足。只有这凉爽,这植物在人的血『液』中的奇特的渗透,才能使他满足。他多么幸运,因为有这些可爱的神秘的解人心扉的草木在等待着他,正如他等待着它们一样,多么满足,多么幸福!
当他用手绢把自己擦干时,他想到了赫米奥恩和她那一击,他还能感到头的一侧在发痛。但毕竟这又算什么?赫米奥恩算什么呢?所有这些人又算什么呢?这儿是那么完美、清凉、干净、新鲜而没人打扰。的确,他是犯了个错误,认为需要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