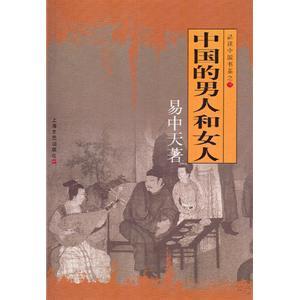爱恋中的女人-第3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总是认为,我会被别人爱的——但我一次次地失望。你不爱我,你自己清楚,你不想为我服务,你只要你自己。”他血『液』里一阵愤怒的颤栗,只是重复道,“你不想为我服务。”所有的幻想倾刻消失。
“不,”他气愤地说,“我不想为你服务,因为没有什么好服务的,你想让我为你服务什么呢?没有,什么也没有,它甚至不是你想要的,那只是女人的本『性』,我不会给你这女『性』的虚荣心以一丝一毫的帮助——那是个破洋娃娃。”
“哈!”她嘲弄地大笑起来,“那就是你对我的看法,对吗?那你还居然鲁莽地说你爱我。”
她愤怒地站起来,要回家。
“你要的是极乐的白痴。”她说着又转向他面前,而他依旧坐在树影里,隐约可见。“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谢谢你,你想我属于你,永不批评你,永不为我自己辩解,你只想我成为你的一种什么东西,不,谢谢你!如果你需要,那儿有成批的『妇』女可以给你这些,有很多『妇』女愿意躺下,让你从她们身上走过——去找她们吧,如果那就是你需要的——去找她们吧。”
“不,”他充满怒气地蹦出一句,“我希望你放弃你那骄傲的意志,你那可恶的自我坚持,那才是我所希望的,我希望你能绝对地相信你自己,能够完全放松你自己。”
“放松我自己。”她嘲讽地重复了一句,“我可以很容易地放松我自己,而正是你不能放松你自己,正是你把自己当作宝贝似的不肯松手,你——你是,旧学校的老师,你——你这个牧师”这一番话中的道理使他一下怔住了,不得不对她另眼相看。“我不要你像酒神狂欢节那样地放任自己,”他说,“我知道你可以做到那一点,但我讨厌狂欢,不论是酒神节或其它场合,那看起来像是在一个松鼠笼子里打转儿。我希望你别只关心自己,不要在那儿只想着你自己,别太顽固——高兴起来,要自信,对什么都不要太在意。”
“谁固执呢?”她讥笑说,“是谁在那儿固执己见?不是我!”她口气里带着明显的嘲笑和气愤。他不由得沉默了一阵儿。“我明白,”他说,“不管是我们中谁固执,我们都错了,但我们之间没有达成一致,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他们俩静静地坐在湖畔的树荫下,坐在黑暗中,被月光笼罩着,渐渐陶醉了。
慢慢地,平静安宁来到他们之间。她轻轻地把手放在他的手上,他们的手在宁静中轻柔地默默地握在一起。
“你真的爱我吗?”她问。
他笑起来。
“我管它叫你的战争叫嚣。”他滑稽地回答说。
“为什么?”她叫起来,感到很可笑,很有趣。
“你的固执,你的战争叫嚣,‘布莱哥温,布莱哥温’一种古老的战争叫嚣,你的是‘你爱我吗?’——要么投降,要么死路一条!”
“不,”她恳求地说,“不是那样的,但我必须清楚你爱我,不是吗?”
“那么,好吧,现在知道了,不要再问了。”“但,你真的爱我?”
“是的,我爱你,我知道,这就是最后的结论,这是结论,为什么还要再罗嗦呢?”
她一阵不语,又惊又喜。
“你确定吗?”她说着慢慢向他靠近。
“很确定——别问了——接受这个事实,就什么都结束了。”她紧紧地幸福地依偎着他。
“什么东西结束了?”她快乐地喃喃道。
“烦恼。”他说。
她又贴近了他些。他紧紧地搂住她,轻轻地温柔地吻着她。一切是那么宁静,那么安详。没有思想,没有欲望和需求,就这样轻轻地搂着她,吻着她,只和她在一起,这么安静地呆在一起,不是一种催眠式宁静,而是充满幸福快乐的宁静,没有任何欲望和固执,如同天堂,只有两个人静静地厮守一起。
她就这样长时间地幸福地依偎着他。他不停地吻着她的头发,她的脸庞,她的耳朵,轻轻地,温柔地,像甘『露』落下。但是他在她的耳边炽热的呼吸又再次使她心烦意『乱』,又点燃了她心中原始的毁灭的火焰。她紧紧地贴着他,而他觉得他的血『液』如水银般在上升。
“但我们需要保持平静,对吗?”他说。
“是的。”她说道。仿佛很依从。
她继续向他越贴越紧。
但一会儿,她又离开他,抬起头来看着他。
“我要回家了。”她说。
“一定要走?——多令人难过。”他回答。
她倚向他,把嘴伸过去等待亲吻。
“你真的难过吗?”她微笑着呢喃。
“是的。”他说,“我多希望我们能永远像刚才那样呆在一起!”“永远,是吗?”他亲吻着她时,她低声说。然后又激动地粗着嗓子低叫,“吻我!吻我!”说着又紧紧贴住他。他不断地吻她。但他也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愿,但只想要温柔的感情交流,不要别的,不要激情,因此,她很快地站起来,带上帽子,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却感到格外的思慕、渴望。他想,也许他错了,或许他不应该带着他想要什么的愿望去接近她,那究竟只是一种想法呢,还是对那种深切渴望的解释呢?如果是后者,为什么他又总在谈论感觉上的圆满呢?这两者不太一致呀。
突然,他感觉到自己正面临一种局面,那么简单,再简单不过了。一方面,他知道他不再想要感觉方面的体验——一种比日常生活可以给予的更深刻、更黑暗的东西。他记起他常在度假日见到的那些非洲神物,他又回想起一个大约两英尺高的小塑像,刻的是西非的一个细高优美的人物像,用黑木雕成,光亮、雅致,那是个女人,头发像顶西瓜皮似高高挽起。他对她印象深刻,她是他思想的亲密伙伴。她的身子很长很美,脸象甲虫般小巧,脖子上戴着一圈圈铁环似的项圈。他记得,她那被刻画出的惊人的美丽,她那甲虫般玲珑的脸庞,长而优美的身子,但她的腿粗短丑陋,『臀』部格外突出,那么沉重,与她那异长细细的腰身很不相称。她知道很多他不知道的事情,她有几千年的纯粹的感觉,她背后隐藏了无数种族的知识,她的种族很可能灭绝几千年了。多么神奇。那种感觉和可表达出来的思想的联系被打破,只剩下一种体验,一种奇特的感觉。几千年以前,他的这种感情一定也曾存在于那些非洲人中间,那些美好、圣贤、创造的欲望和那种生产的幸福感一定已经消亡了,只剩下一种追求知识的强烈愿望,没有灵气的不断发展的知识,被思想捕捉、又结束了思想的知识,无法解释无法理解的知识,就像甲虫所拥有的那种只存在于腐烂世界和冷漠无望中的知识,这就是为什么她的脸看起来像甲虫,这就是为什么埃及人要崇拜球状甲虫形的宝石,就是因为这些存在于消亡和腐烂中的伦理。
在死亡之后,自从灵魂像落叶一般摆脱了无尽的折磨之后,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与生命和希望摆脱了联系,我们从纯粹的躯体中走出来,从创造和自由坠落到长长的非洲式的纯感『性』理解和体认的过程,仿佛进入了神秘的消亡之中。
他现在意识到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它需要成千上万的时间,在创造精神消亡之后,他意识到有许多神秘事物有待揭开,那感觉的、无思维的、可怕的秘密,远超过对『性』蕾的崇拜。这些西非人,在他们倒逆的文化中,在『性』知识上到底已经超越了多远了?很远很远,伯基又再次回想起那尊女人像,那被加长了的太长的躯体、那个令人惊叹、好奇的沉甸甸的『臀』部,那长长的不自由的脖子,那有甲虫特征的面部,这远远超过任何一种对『性』的理解,感觉上的、精细的现实,远远超过任何一种对『性』的研究。这条路,这种非洲式的过程仍需完成。要白种人做这种事太困难了。这些白种人有冰雪聚合成的北极给他们垫底,会去解开冰冷的、摧毁『性』的知识之谜,画一样抽象的毁灭之谜,然而西非人被撒哈拉死一般抽象的灼热所控制,便解开了太阳毁灭和太阳光腐败之谜。
这就是所有剩下的吗?难道现在除了脱离幸福、创造『性』的有机体之外再没有什么了吗?时间已经完结了吗?难道留给我们的只有那些奇怪的,可恶的知识消亡后的剩余了吗?那些跟我们这些来自北边的金发碧眼的人不同的非洲式的知识!
伯基想起了吉拉尔德,他就是这些来自北方的奇怪的、神奇的白『色』魔鬼中的一个,是在毁灭『性』的霜冻的神秘中诞生的。难道他注定要从这种知识中消亡吗?在这种冰冻的知识世界里冻结于严寒中吗?他是否是一个使者,一个世界将在冰天雪地里消亡的征兆呢?
伯基觉得有些恐惧,当他一设想到这种猜测时,他觉得累极了。突然间,他那奇异的绷紧的注意力消失了,他无法再集中去想这些神秘之事了。有另外一条路,一条自由之路,一条凌架于爱情和欲望之上的极乐之路,可以进入纯粹单独的自我,它比任何感情上的痛楚更为强烈,一种可以接受的与其他人产生永久关系的义务的自由、骄傲、独立、可爱的境界,可以为爱情的束缚和控制所屈服,却不需要为之丧失自我的骄傲和独立,即使就处于相爱和屈服的时候。
还有另一条路,一条剩下的路,他必须跑着才能赶上。他想到了欧秀拉,她是多么敏感,多么精巧,她有多么好的皮肤,细嫩得仿佛还需再加一层,她相当温柔敏感。他刚才怎么忘了这一点?他必须马上去找她,他要让她嫁给他,他们必须立刻结婚,以便有一个确定的关系,进入一种明确的思想交流。他要立即出去问她,就在现在,没有时间再等了。
他快速地向贝欧多弗跑去,几乎对自己的行为已失去了意识,他看见了位于山坡上的小镇,小镇并不零散仿佛被两边满是工人住宅的直直的、一通到底的街道给围了起来,成为一个巨大的方形,很像他想象中的耶路撒冷,这个小世界对他来说,陌生而透明。
罗莎琳德给他开了门。正像一般年轻女孩那样,她有些吃惊地说,
“噢,我要去告诉爸爸。”
说完她就不见了,只剩下伯基一个人在大厅里看一些复制的毕加索的作品,这些画是最近古德兰拿回来的。正当他欣赏一幅对地球有绝妙领悟的画时,威尔·布兰哥温一边翻下他衬衣的袖子,一边走出来。
“噢,”布兰哥温说,“我去穿件外衣。”于是,他也消失了。一会儿之后,他回来了,并打开画室的门说。
“请原谅,我正在棚子里做一点工作。你请进。”
伯基走进去坐下,注视着这个男人,他脸庞红润发亮,眉『毛』细长,双目明亮,黑黑的剪过的胡子下面,一张宽阔的富于情感的嘴巴。这就是一个人,多奇怪!不管布兰哥温先生以为他自己是什么,在现实的他面前都显得毫无意义。伯基可以看到的只是一个奇怪的不可解释、不成型的组合体,情感、欲望、压抑、传统和机械思想的简单组合,那么无条理、不和谐地堆积成这个优柔寡断、面『色』红润、快五十岁的男人,和二十岁时一样,他不成熟,没造就,他不是个父亲,他有了有血肉之躯的儿女,却没有把思想传给他们,这种思想不是从任何祖先那里得来,而是从无知世界中得来,一个孩子要么是个神奇的孩子,要么就是没有造就成型。
“天气不像前几天那么差了。”布兰哥温等了一会儿说。两个人之间没有丝毫的联系。”
“是的,”伯基说,“两天前是满月。”
“噢,那么你是相信月亮能影响天气了。”
“不,我不这样认为,我对此知道的不多。”
“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月亮和天气可能一起变化,但月亮的变化却不会导致天气的变化。”
“是这样吗?”伯基问,“我没听说过。”
一阵停顿后,伯基说,
“我妨碍您了吗?我其实是来看欧秀拉的。她在家吗?”“我想她不在,我相信她去了图书馆,我去看看。”
伯基可以听到他在餐厅里询问。
“是的,”他回来说,“但不会太久的,你有话对她说?”伯基用冷静、清澈的目光看着对面的男人。
“事实上,”他说,“我是想让她嫁给我的。”
这位老人棕黄『色』的眼睛里有一道光闪了一下。
“噢——?”他看着伯基问,在伯基那冷静、执著的注视下,又垂下眼去,“那么,她在等您吗?”
“不。”伯基说。
“没有?——我从来不知道会有这种事发生。”布兰哥温先生尴尬地笑了。
伯基回视他,自言自语道,“我不明白为什么称之为‘发生’“于是他大声说。
“不,它是来得很突然”这时,他想起了他和欧秀拉的关系,又补充道,“但,我不知道——”
“很突然,不是吗?——嗯!”布兰哥温说着有些困『惑』和气愤。“从一方面说是,”伯基回答道,“但从另一方面讲又不是。”一阵沉默之后,布兰哥温开口道,
“那么,她自己也高兴?”
“噢,是的。”伯基平静地说。
布兰哥温雄壮的声音中有了一丝颤抖,他回答说,“尽管我不想让她如此的匆匆忙忙,但我也不想等到太迟的时候后悔。”
“噢,不会太迟的。”伯基说,“就这事而言。”
“你这话什么意思?”她父亲问。
“如果一个人后悔结了婚,那么这婚姻就算完了。”伯基说。“你这样认为?”
“是的!”
“哎,也许,那只是你的看法。”
伯基沉默着,自己想到:“也许是这样,布兰哥温,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才需要一番解释。”
“我猜想,”布兰哥温说,“你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吗?她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
“她吗?”伯基暗自思量,想起了他少年时代的行为“是只母猫。”
“我知道她在怎样的环境中长大吗?”他重复问了一句。他似乎在故意激怒布兰哥温先生。
“那么,”他说,“她拥有一个女孩子应有的一切——只要是我们可能的和能够给她的。”
“我相信是这样。”伯基说完停了好一会儿,布兰哥温变得越来越怒不可遏,仅仅是伯基的存在就会使他不由得感到生气。“我想看到她后悔。”他用一种有力的声音说。
“为什么?”伯基说。
这个简单的字眼顿时像一颗子弹在布兰哥温先生的脑袋里炸开了。
“为什么?我不信任你的那些新思想、新做法——像个青蛙似地在海松树脂中跳进跳出,我根本不会喜欢这些做法。”伯基用凝视的无表情的眼睛看着他。这两个男人之间的矛盾正在升级。
“是吗?但我的做法和思维都是新型的吗?”伯基问。“难道不是?”布兰哥温先生站起来,“我并不是单单指你一个人。”他说,我的孩子们是在言行都要以宗教为准的教育中长大的,像我所受的教育一样,我不希望看到他们脱离这些。”接着是一阵危险的沉默。
“还有超越哪些?”伯基问。
那位父亲犹豫了,他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哦?你是什么意思?我想说的只是,我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