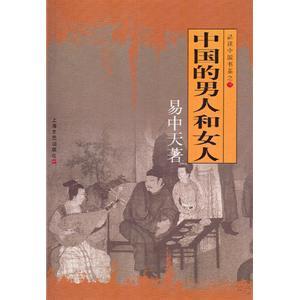爱恋中的女人-第3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威妮弗雷德默默地走向她,神『色』奇怪而庄严。
“我们真高兴您能回来,”她说,“这是给您的鲜花。”她向古德兰献上花束。
“给我的?”古德兰说。她有那么一会儿给呆住了。然后一道红晕泛上她的脸颊,好像在那一刻被喜悦的火花照花了眼。之后,她抬起那双有些奇怪而又燃烧着的眼睛了看了看这位父亲,然后又看了看吉拉尔德。吉拉尔德的心又缩了一下,好像不能忍受她辛辣的没有掩饰的目光。他难以忍受她所流『露』出来的神情,他扭过脸去,但却觉得无法躲避她。他的身体在她的注视下扭曲着。古德兰把脸埋在了花簇里。
“多美啊!”她低沉的声音从花束中传来。但她突然迸发出感情,弯下腰,吻了一下威妮弗雷德。
克瑞奇先生走向前,伸出一只手来。
“我还担心你想离开我们呢。”他开玩笑地说。
古德兰仰望着他,那容光焕发的脸上『露』出了淘气的难以形容的表情。
“是吗?”她回答,“不,我不想呆在伦敦。”
她的话暗指她很高兴回到肖特兰兹来。她的语调热情,还有点安慰的意味。
“那好哇。”父亲微笑着说,“你看,在我们这儿,你有多受欢迎哩。”
古德兰只是动着她那热情、羞涩的黑『色』大眼睛。她不自觉地陶醉于自己的力量。
“看起来你好像带着胜利的果实回来了。”克瑞奇拉着她的手继续说道。
“不,”她变得奇怪地说,“我来这儿之前可真没干什么事。”“噢,好了,好了,我们可不想听这些谦虚的话了。吉拉尔德,我们在报纸上读到过关于她的文章,是不是?”
“你干得确实不错。”吉拉尔德握了握她的手说,“画卖掉了吗?”
“没卖完。”她说,“卖得不多。”
“那也够可以。”他说。
她不太明白他话的意思。但这种接待方式让她心情很好。她被这种为她专门举行的略带点恭维意思的欢迎仪式而陶醉。“威妮弗雷德,”父亲说,“拿双鞋给布兰哥温小姐换上。你最好快点换一下。”
古德兰出去,手里还拿那束花。
“真是了不得的姑娘。”她出去了以后,父亲对吉拉尔德说。“是的。”吉拉尔德简明地回答说,就好像他不想听这个评论。克瑞奇先生想让古德兰陪他坐半个小时。他经常脸『色』很糟糕。很没有精神,元气都耗尽了。他一旦有了精神,他希望让别人知道他还是以前的那个他、身心十分健康,正若北斗,虽然并不属于外面的世界,但在他健旺的生活中仍处于最佳状态。古德兰在他的身边,让他有理由有这种想法。他如果跟她在一起,就会觉得十分精神,精力也十分充沛。自由自在地度过宝贵的半小时,好像比以前过得还快。
她去他那儿时,他正支撑在书房里,脸『色』十分黄、目光暗淡,像是没有了视力。他下巴上的胡子显得灰白。仿佛是从一个尸体的腊黄的肉体中长出来的一样。但他周围的气氛却生机勃勃,十分活泼、欢快。古德兰也让自己置身其中。在她看来,他只是个平常人,只是他那可怕的长相不知不觉地在她心灵中留下了可怕的印象。她明白,虽然他看起来很愉快。但他的眼中却『露』出掩盖不住的空洞,那只是死人的眼睛。
“啊,这是布兰哥温小姐吧,”男仆通报她进来的时候,他突然精神好起来,对男仆说,“托马斯,替布兰哥温小姐摆把椅子在这儿——对,就这儿。”他高兴地看着她那柔嫩清新的脸。它让他想到了生命,“啊,来杯雪梨酒吧,再来一小片蛋糕,托马斯……”
“不了,不了,谢谢。”古德兰说。就在她说的同时,她的心忽然沉了下去。这个病人看起来会被她的拒绝推到死亡的边上。她应该顺从地而不违背他的意思。顿时,她的脸上『露』出了有点淘气的笑容。
“我不太喜欢雪梨酒,”她说,“但是对其它的什么酒我都差不多喜欢。”
病人立刻抓住了这根救命的稻草。
“不喜欢雪梨酒!不喜欢,来点别的!别的什么?托马斯,还有什么酒?”
“葡萄牙红葡萄酒——库拉索酒——”
“我要库拉索酒——”古德兰很信赖地看着病人说。“当然,那么,托马斯,就来杯库拉索酒——再要点蛋糕还是饼干?”
“饼干。”古德兰说。她什么都不想要,但她很明智。“好的。”他一直等到小酒杯和饼干在她面前摆好,他才心满意足。“你已经听说这个计划了吗?”他说,有点激动。”把马厩改成威妮弗雷德的画室?”
“还没呢!”古德兰故作惊讶地叫道。
“哦……我还以为威妮在信中跟你说了呢。”
“哦,是说过——当然,但我想那可能只是她自己的一个小想法。”古德兰宽容地让人不可捉『摸』地笑了笑。病人也笑了,情绪很不错。
“噢,那不是她自己的主意,是一个真正的计划,在马厩的屋顶下有一个很好的房间——有斜坡式的椽木,我们准备把它改成画室。”
“太好了。”古德兰叫了起来,特别激动。她一想到椽木,就为之心动。
“你觉得那还可以吗?好,就这样做吧。”
“那可就让威妮弗雷德高兴坏了。当然啦,她需要认认真真地干,那就是她所要的。一个人总需要一个自己的工作室,要不然永远成不了专职人员!”
“是吗?是的,当然,我希望你和威妮弗雷德共同享用那个画室。”
“真谢谢您了。”
古德兰已经早知道了这些,但必须显出惊喜、感激、羞怯的样子。
“当然了,我最希望的是,你能放弃你在中学的工作,充分地利用起这个画室,在那儿工作——时间多少,都按你自己喜欢的来。”
他用黑暗空洞的眼睛看着古德兰,她好像充满感激地回视他。即将死去的人用语居然这样完整流畅,就好像回声一样从他快死的口中传来。
“对于你的报酬——教育委员会给你多少,我就给你多少,千万不要不好意思,我可不想让你有所损失。”
“噢,”古德兰说,“只要能在画室中工作,我就能有足够的钱,真的。”
“好。”他说,特别高兴自己在做施恩者。“一切都会很好地安排的。你不介意在这儿打发日子吧。”
“如果能在画室中工作,”古德兰说,“我没有什么别的要求。”
“真的吗?”
他感到十分高兴。但他已经很累了。她看得出他已隐约感到了死亡的痛苦。他那暗淡空虚的眼光中会『露』出这种痛苦的折磨,死亡的过程还没有结束。她轻轻地站起身说:
“可能您要睡了,我得去找找威妮弗雷德。”
她走了出去,告诉护士她把他一个人留在那儿。一天过一天,病人的细胞在不断减少,死亡的过程越来越接近尾声,接近连结人成为一个整体的最后一个结合点。但是这一点还比较牢固,不太容易解散,垂死者的意志还不愿屈服。也许他已死了大部分,但所剩的那一点依然如前一样在最后的崩溃到来之前,凭着意志把自己聚集成一个整体,不让它溃散。但是,能由他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小,最终会缩成一点而消失。
要坚持着活下去,他就需要和人们保持联系,每一根救命的稻草都不可以放过。威妮弗雷德、管家、护士、古德兰,这些人都是他生命的最后源泉。父亲在场时,吉拉尔德总是神情十分紧张,除了威妮弗雷德,家里别的孩子都一样,但是没有那么严重,他们看着父亲,所看见的只有死亡。仿佛某种潜意识的憎恶抓住了他们的心,他们看不见父亲那张熟悉的脸,听不见父亲那熟悉的声音,看见、听见的只是死亡,对死亡的憎恶给他们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在父亲面前,吉拉尔德简直不可呼吸,他必须马上出去。所以,在儿子在场时,父亲也无法忍受。那会使将死的人的灵魂感到厌烦。
画室基本已准备好,古德兰和威妮弗雷德搬了进去。她们俩对房间的布局和齐全的设备十分满意,现在她们几乎不用进大房子了。她们俩在画室里用餐,在那儿平安地住着。大房子已经变得越发可怕。两个穿白衣的护士悄没声地四处走动,好像是死神的使者。父亲还是抱病卧床。在屋子里,兄弟姐妹、孩子们都压底声音来来去去。
威妮弗雷是经常去看望父亲的一个。每天早晨,吃过早餐,她都要去父亲的房间,那个时候,他在靠着床梳洗。她总是要和他呆上半个小时。
“爸爸,你好点了吗?”她总是这么问。
而他总是回答:
“是的,我想我好一点了,宝贝。”她十分疼爱他,保护似地用两只手握住他的手。他感到是那么温暖亲切。
午饭时,像是一个规矩,她又跑了进来,告诉他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而到了晚上,拉上窗帘以后,他的房间十分温暖舒服。她就很长时间地陪他。古德兰回家了,威妮弗雷在房子里很孤单,她就最喜欢跟父亲呆在一起。他们有时认真谈话,有时闲聊。他总显得很有精力,像是他来回走那样。于是以孩子的一种十分敏感的本能,威妮弗雷德尽量不说那些让他痛苦的事,装着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样子。她下意识地不去注意父亲的病,而显得快乐高兴。但是在内心,她和一般成人一样明白而且可能会更加明白。
父亲和她在一起时也装出没有什么问题的样子。但她走了以后,他就又恢复了旧态,痛苦地忍受肉体的折磨。但也有高兴的时候,虽然随着气力的衰竭,他的注意力也越来越弱。护士不得已会赶威妮弗雷德走,以免他太疲倦。
他从不承认自己即将要死去。他知道是那样,他明白末日快来了。不过,他甚至对自己都不承认。他憎恨这个事实,恨得厉害,他不能忍受死亡把自己征服了。他有着坚强的意志,对他来说,死亡是不存在的。不过,有时,他很想大声喊叫、哀号、哭诉。他本想对吉拉尔德诉说,好吓一吓儿子。吉拉尔德本能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就躺入了自己的小天地里,这种活不了死不成的样子是他最厌烦的。人死,就死得干脆些,像罗马人一样。人死时应该跟活着时一样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父亲的这种死,好像有一条大蟒蛇紧紧地缠住,使他颤抖。大蟒蛇缠着父亲,而儿子似乎已被卷入进去。他一直在抵挡着,从某种奇特的意义上说,他是父亲的中心力量。即将死去的人最后一次要求见古德兰时,脸『色』是死白的,但是他必须要见什么人,在他神志还算清醒时,他必须和活人的世界保持一点联系,不然就不得不接受现实。幸运的是,约绝大多数时候,他都是神志不清,眼睛昏花。他花了很多时间去模糊地回忆往事,可算是对以前生活的再次的经历。但在很多时候,直到最后的时刻,他心里都很明白现在发生的是件什么事,他很清楚死神已降临在他身上,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会求救于外来的帮助,不管是谁的帮助,因为他很明白他正在经受的死亡是超出一般死亡的,是不能忍受,他不会去承认它。
古德兰被他的容貌给惊住了,还有他那暗淡无光而又不屈不挠的眼睛。
“嗯,”他用十分微弱的声音说,“你和威妮弗雷德过得挺好吧?”
“噢,很好。”古德兰回答说。
在谈话中出现了一阵短暂却如死一般的沉寂,仿佛在病人的脑中呈现的想法是些垂死的混『乱』中飘浮不定、不可捉『摸』的稻草。“画室合适吗?”他说。
“好极了,再没有比那更漂亮更完美的了。”古德兰说。她等待着他的另一个问题。
“你认为威妮弗雷德有没有雕塑的天赋?”
真是奇怪,他的话是那么空洞,没有任何意义。
“我肯定她有天赋。有那么一天,她会有所成就的。”“啊,那她的生命就不会完全地虚渡过去了。你觉得呢?”古德兰觉得十分惊讶。
“当然不会。”她轻柔地嚷道。
“好,好。”
古德兰又在等他开腔。
“你发现了生活愉快、很值得活下去吧?”他问。脸上『露』出一股很可怜的微笑。古德兰却有些不忍看。
“是的,”她微笑着——她会见机撒谎的——“我相信我会过得很愉快。”“好的,快乐的『性』格是很难得的。”
古德兰笑了一下,尽管她的内心已感到烦腻,人非要这样死?一面让生命被迫而逝,一面还要谈笑自如。至到最后的时刻?难道就没有别的方式?人非要经历种种的恐怖,表现出了十分坚韧的意志,一直到意志战胜了恐怖吗?人必须得这样,这是唯一的方式。她极为赞许要死的人的自制能力和镇静。但她对死亡深恶痛绝。让她高兴的是,日常世界是完美的,没有必要不着边际地去想别的事。
“你在这儿很好吧?——有什么还需要我们做的?——在你那方面没有什么不满意吗?”
“只有一点:您对我太好了!”古德兰说。
“啊,问题还是在你这儿,”他说。他感到了一点得意,因为这话表明,他依然是那样强壮、那样有力量。但是物极必反,他的胸口开始有一种恶心的感觉。
古德兰走开了,到了威妮弗雷德身边。法国女教师已经辞职而去了。古德兰在肖特兰兹呆了很长时间。另外又有一位家庭教师,接着给威妮弗雷德上课。但是她不住在这儿,她还要回学校去上课。
一天,古德兰准备和威妮弗雷德、吉拉尔德还有伯基开车进城。天特别黑,还下着大雨。威妮弗雷德和古德兰已经收拾好,在门口等着。威妮弗雷德十分沉静,但古德兰没有察觉到。突然,威妮弗雷德很冷漠地说:
“布兰哥温小姐,你认为我父亲会死吗?”
古德兰吃了一惊。
“不知道。”她回答。
“你真的不知道?”
“没有人敢肯定。当然,他有可能会死的。”
孩子慢慢地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她问:
“但你觉得他会死吗?”
这好像课堂上的提问,一个劲地追问着,要『逼』迫成年人来回答似的。孩子眼睛瞪得大大的,那神情很有些胜利的感觉,就好像是个魔鬼。
“我认为他会死吗?”古德兰重复,“是的,我这样认为。”但是威妮弗雷德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她。
“他病得很厉害。”古德兰说。
威妮弗雷德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疑虑重重的样子。“我可不相信他会死。”孩子坚持说,有些讥讽的味道,然后她走到了街上。古德兰看着她孤独的背影,她的心猛缩了一下。威妮弗雷德正在很认真地玩着水。完全跟什么都没说过一样。“我已造了一个堤坝。”她的话穿过『潮』湿的空气传来。吉拉尔德从后面的门厅来到门口。
“她不愿相信也好。”他说。
古德兰看了他一眼,两人的目光相遇一起,互相交换了理解而又讥讽的眼神。
“也好。”古德兰说。
他又看了看她,在她的眼中似乎有一股燃烧的火焰。“既然罗马肯定要被烧掉,为什么不在烈火前跳舞呢?你说?”他说。
她吃了一惊。但是她振作起来回答说,“啊,当然了,跳舞要比衰号好。”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