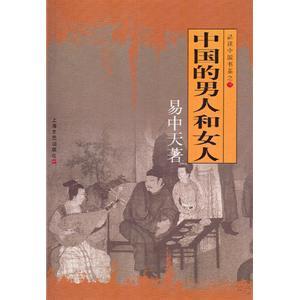爱恋中的女人-第5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她没有听见,她躺在那儿,像对一个什么她永远无法理解的东西似的看着他,像一个孩子看着一个大人,永远无法明白,只有服从。
他吻着她,吻着她的眼睑,使她无法继续看下去,他现在想得到些什么,一些理解,一个信号,或是她的承认。但她只是安详地躺着,孩童般的,很遥远,仿佛一个被征服却无法理解的孩童,只感到『迷』失。他又吻了吻她,便放弃了。
“或许我们该去楼下喝点咖啡、吃点点心?”他问。窗外,落日的余晖已变成灰蓝『色』。她闭了闭眼睛,驱走了脑中那单调的死亡的幻想,然后又睁开来,重新面对这日常世界。“好的。”她简短的回答,集中了一下她的意识,然后,再次走向窗户。蓝『色』的夜晚已经降临在窗外雪的摇篮和那巨大的斜坡。但是那耸入天际的峰巅却是玫瑰『色』的,象花蕊似的闪烁、炫目,盛开在天堂的顶端,超乎一切,『迷』人而又遥不可及。
古德兰看着所有这些可爱之处。她知道它们的美丽是不朽的。在夕阳蓝『色』的斜晖中,玫瑰『色』的花蕊,积雪发出的火花,她可以看得见,感觉得到,却无法溶于其中,她被拒绝,被排斥,她的灵魂也被阻挡在外。
她伤感地又望了一眼窗外,才转过身来,梳理头发。他已打开了行李,看着她,等她。她知道他在看她,这使她有些局促,潜意识中有点不安和躁动。
他们一起走下楼。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奇怪的表情,而且眼睛放光。他们看见伯基和欧秀拉在一个角落的长桌旁坐着等他们。
“他们在一起看起来如此的简单而又协调。”古德兰嫉妒地想着。她羡慕他们之间那种出于自然童稚的满足,这是她无法得到的。在她看来,他们就象小孩子。
“嘿,这么好的点心。”欧秀拉贪婪地叫道,“太棒了!”“不错。”古德兰说,“我们也来点咖啡和点心吧!”她对侍者加了一句。
然后她便挨着吉拉尔德坐在长椅上。伯基望着他们,感到一种温柔的心痛。
“我认为这地方真不错,吉拉尔德。”他说,“棒极了,太妙了,简直没治,还有其它所有的德文形容词都用得上。”
吉拉尔德『露』出一丝微笑。
“我喜欢这儿。”他说道。
用刨光白木制成的桌子,布满了餐厅的三面,就象在小酒馆那样。伯基和欧秀拉背靠着墙面,吉拉尔德和古德兰则挨着他们坐在角落里靠着火炉。这里的地方还算大,有一个小酒巴,就象个乡村小酒店,但却更简单,设备更少,且都是用漆过的松木制成的,房顶、四壁、地板,仅有的家具就是桌子和椅子,环绕着餐厅的三面,还有一个大大的绿『色』的炉子,一个小柜台,入口在第四边墙上,窗户是双层的,没有任何窗帘。现在已是傍晚了。咖啡端来了——滚热且味浓——还有一块蛋糕。
“哗,一整块点心!”欧秀拉大喊,“他们给你的比我的多,我要吃你的。”
周围还有其他人,大约共有十个。伯基很快便知道了,他们是两个艺术家,三个学生,一对夫『妇』,一个教授带着两个女儿——都是德国人。而他们这新来的英国人,坐得高高的,可以俯视一切。那些德国人站在门口向里探头望了望,对那侍者说了几句话,便又离开了。还没到吃饭的时间,所以他们没有进餐厅,只是来这儿换双鞋去参加联谊会。
这些英国人可以听到不时传来的齐特拉琴的演奏声,钢琴的弹奏声,还伴随着阵阵的笑声,吵闹和歌声。四周有些轻微的声音的震动。由于整个房子是木制的,因此,它象是一个容纳了各种声音在里面的大鼓。但是不但没有使噪音更大而是使其减弱了一些,因而那些齐特拉琴声听起来如此微弱,象是一把小提琴不知藏在什么地方轻轻地演奏,而且钢琴听起来也是小型的,好似一架古式小钢琴。
当他们喝完咖啡时,老板走进来。他是个泰罗人,身材魁梧,颧骨扁平,有一张苍白的麻子脸和浓密的胡子。
“你们愿意不愿意参加联谊会,去结识结识其他的女士和先生?”他弯下腰来,笑容可掬地问道,『露』出一口大白牙。他那蓝『色』的眼睛把这几个人扫视了一圈——他不太有把握与这几个英国人打招呼。由于不会说英语,他感到不太自在,而且他也不知道可否用他的法语一试。
“我们要不要去联谊会,认识其他的客人呢?”吉拉尔德大笑着重复道。
一阵小小的犹豫。
“我想,我们最好——最好打破这僵局吧!”伯基说。两们女士站了起来,脸红红的。于是那身材魁梧,长着象甲虫一般黑黑皮肤的旅店老板在前面带路,把他们带向那喧闹的地方,他打开门,把四位客人让进游艺厅。房间里一下静了下来,大家都感到有些尴尬。他们四个觉得所有的面孔都在朝他们这边看。这时老板对着一个矮小的看起来精力充沛的长着络腮胡子的人欠腰低声说了几句:
“教授,请允许我介绍——”
教授的反应很快,马上便神采奕奕地微笑着向四位客人一弯腰,仿佛立即与他们成了朋友。
“各位女士、先生可否参加我们的联谊?”他的语气充满活力,却又温和可亲地问了一句。
四个英国人笑了,他们有些不安地在房间中央转了一圈。吉拉尔德作为他们的发言人,表示他们将十分乐意参加这里的聚会。古德兰和欧秀拉兴奋地笑着,觉得所有男人的目光都投向她俩,而她们则高傲地抬着头谁也不看。
教授一一介绍了在场的人,当他们弯腰致意时,却不时地搞错对象。除了那一队『妇』夫外,所有德国人都在场。教授的两个女儿,皮肤白净,身材高挑、健壮,身着朴素的深蓝『色』衬衣和裙子,脖子长而结实,眼睛清澈湛蓝,头发精心地梳起来束在脑后。她们弯了腰,便红了脸退了回去。那三个学生都深深鞠了一躬,很谦逊,大约要表现他们良好的修养,给客人留下好印象;然后是一个瘦瘦的,皮肤黝黑,眼睛鼓鼓的男人,看起来象个小孩,他微微欠欠身;他的同伴,一个头很大、很年轻的男人,衣着入时,把腰弯得很低,脸一下红到耳根。
“刚才,勒尔克先生正在用科隆方言给我们朗读。”教授说。“他一定原谅我们打断了他,”吉拉尔德说,“我们愿意继续聆听。”
立刻就有一阵鞠躬让座的喧哗。古德兰和欧秀拉,还有吉拉尔德和伯基靠墙坐于沙发中。这间房也和其它一样,用刷过的柚木镶嵌而成。有一架钢琴,几把椅子、沙发和一些放了书和杂志的桌子。除了那个蓝『色』的火炉之外,这间房子里再无其它装饰品。但却很典雅、舒适。
勒尔克是个小个儿,长着一副小孩子身材。他那圆圆的脑袋,看上去对事物很敏感。一双突出、锐利的眼睛象耗子。他迅速地把客人们瞟了一眼,便又显出那副自负的样子。
“请继续您的朗读。”教授笑着说,但口气却很有权威『性』。勒尔克弓身坐在钢琴凳上,眨着眼睛没有答话。
“我们很荣幸,”欧秀拉想了几分钟,才准备好用德语说了这句话。
这时,刚才没有答话的那个小个子男人突然走向一边,面对着他刚才的听众,冲口便开始朗读起来,接上他刚才停止的地方,用一种控制得极好的声音,模仿一个科隆『妇』女和铁路工的吵骂。他身材单薄、且没成形,象个男孩子,但他的声音却很成熟,带着讥讽的音调,声音的波动很轻柔,力度恰到好处,显示了他深厚的理解力。
古德兰对他的科隆方言一句也听不懂,但她却着了魔般地看着他。他一定是位艺术家,任何其他人都不会有如此的适应力和个『性』。那些德国人听着他那滑稽的科隆方言的词语和词组,不禁一个个都笑弯了腰,在兴奋之中时而也很尊敬地瞟一眼这四位“选民”——英国客人。古德兰和欧秀拉也禁不住笑了起来。整个房间都『荡』漾着大笑声。教授的两个女儿的蓝蓝的大眼睛笑出了眼泪,双颊兴奋得发红。他们的父亲也呲牙咧嘴地大笑着。三个学生则把头埋在膝间,笑得直不起腰来。欧秀拉惊诧地看着四周,她的笑声不停愿地从嘴里冒出来。她看着古德兰,古德兰看着她,两姐妹不由地同时爆发出一阵大笑,完全不理会周围。勒尔克用他那凸凸的眼睛很快地瞟了她俩一眼。伯基也在不情愿地呵呵笑着,而吉拉尔德则笔直地坐在那儿,脸上因兴奋而发光。又是一阵狂野的大笑,教授的女儿们笑得全身直抖,而教授则笑得发不出声来,脸涨得通红,脖子上青筋毕『露』,三个学生喊着一些『乱』七八糟的句了,但不时被笑声打断。突然之间,艺术的朗读戛然而止,笑声小了很多。欧秀拉和古德兰在擦眼泪,教授还在大叫着:“没治了,太棒了——”
“绝妙极了!”笑得筋疲力尽的两个女儿无力地回应着。“我们听不懂!”欧秀拉嚷了一句。
“噢,遗憾!遗憾!”教授说。“你们听不懂?”学生冲口对她们喊道,“噢,这太遗憾了,亲爱的夫人,你瞧——”
这些新来的客人象新掺入的成分,和这帮德国人搅和到了一起,整个房间活跃了起来。吉拉尔德身处得心应手的环境之中,兴奋地畅所欲言,他的脸上有种奇特的兴致勃勃的表情。还有伯基,最后也开口讲话,他很羞怯,拘谨,虽然精神很集中。欧秀拉被大家劝动去唱“安妮·劳拉”,教授这样称它。大家怀着极度的尊敬安静了下来,她一生中还从来没这么被人捧过。古德兰凭着记忆,用钢琴给她伴奏。
欧秀拉有一副清脆的好嗓子,但她常常由于缺乏自信而把事情弄得很糟,而这天晚上,她感到很自信,无拘无束。伯基安稳地坐在阴影里,而她则相反,在前面大放异彩,那些德国人使她的感受好极了,仿佛自己一无缺点,她太自信了,以至于有些放肆,她觉得她的声音冲出喉咙时,她就象一只空中飞舞的小鸟,飞翔在歌曲中,完全陶醉了。小鸟的翅膀在风中滑翔、玩耍,她的歌声中加入了些伤感,令观众听得如痴如醉。她太高兴了,充满了对自己情感和能力的自信,自顾自地唱着,撩动着每个人包括自己的心弦。她在极力的自我表现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同时,也使德国人心满意足。
最后,德国人都满怀崇敬,被她那委婉动听的歌声打动了,他们交口称赞她柔美感人的嗓音,几乎无法用语言表达。“太棒了!绝了!她唱的苏格兰民歌好听极了,曲调高雅,噢,伟大的夫人,她太了不起了,简直是个艺术家。”
她兴致飞扬,光彩焕发,象朝阳中的一朵鲜花。她感觉到伯基在看她,仿佛妒忌她似的。她胸膛起伏,血『液』奔涌,她如同太阳在云端上『露』出笑脸般快活。看起来每个人都很崇拜她,情绪激昂,太棒了!
吃过饭后,她想出外走走,看看周围的世界,她的伙伴们都极力地劝阻她——因为外面太冷了。但她说,只是出去看看。于是他们四个裹得严严实实的走出来,四周雪『色』暗淡,看不出它的广阔,仿佛是个妖魔之地。星光下的影子很奇怪。外面的确很冷,冷气似乎是恶作剧般有意地钻入她的鼻孔,简直让她不敢相信。
但这一切都是神奇的。一派虚幻的、静寂的、若明若暗的、不真实的雪景。她与有形世界之间无形的交谈,她和星星之间的交流,她可以看见有颗流星正在滑落,那样奇妙,奇妙得令她想大喊。
四周都是雪的摇篮,脚下都是坚实的雪。雪的冷气透过鞋帮直穿进来。这宁静的夜晚!她想象着她可以听到星星的耳语。她清晰地想象着行星流动的声音,仿佛近在耳边,而她自己则象个小鸟般遨游在星体之间。
她紧紧地贴着伯基。她突然意识到她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她不知道他的思想发展到哪儿了。
“亲爱的!”她停下来望着他。
他脸『色』苍白,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在星光下闪烁。他看见她柔美的脸庞,那么近地抬向他,禁不住地吻住了她。“什么?”他问。
“你爱我吗?”她问。
“非常爱。”他静静地回答。
她又贴近了些。
“不是非常。”她抱怨说。
“比非常还爱。”他几乎难过地说。
“如果我是你的全部,会不会使你难过?”她急切地问。他搂紧了她,亲吻着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不,但我却觉得象个乞讨者——象个穷光蛋。”她沉默不语,开始抬头看星星,然后又吻了他。
“不要作乞丐。”她急切地恳求说:“爱并不使你耻辱。”“感觉象个穷光蛋很耻辱,不是吗?”他回答。
“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她问。而他只是站在冷冷的寒气中紧紧地把她搂紧在怀里。那看不见的寒气正涌上山顶。“如果没有你,我就无法忍受这个寒气永远不散的地方,我无法忍受,这里会使我的生命冻结。”她又突然吻了他一下。
“你讨厌这里吗?”她疑『惑』地猜想着问。
“如果我无法与你靠近,如果你不在这里,我会憎恨这里,我会无法忍受这里。”他回答。
“但这儿的人很好。”她说。
“我的意思是我不能忍受这雪,这静,这里的寒冷,一切都被冻结了,永恒不变。”他说。
她猜想着,然后她便明白了他的意思,情不自禁地依偎在他怀里。
“是的,我们能这么温暖地在一起真太好了。”她说。然后他们开始动身返回。他们看见在寂静的雪夜里那旅馆的灯光格外引人注目,但在这山谷中部却显得十分渺小,象是一颗黄『色』的草莓、又象是一缕阳光,细小、橙黄,闪烁在一片雪的黑暗中,身后是高山的阴影,鬼怪般遮住了星星。
他们走近了他们的家。他们看见一个男人从漆黑的门里走出来,手里提着灯笼,摇摇晃晃发出黄『色』的光,照着他一双黑『色』的鞋,正走进雪地里,那矮小阴暗的身影走在雪中。他打开了一扇小屋的门,冰冷的空气中传来一般牛呀、猪呀热乎乎的酸臭气。他们瞥见那漆黑的牛棚里有两头牛犊。小屋的门又被关上了,一丝光也不漏。这再次使欧秀拉想起家乡马什农场,她的童年以及布鲁塞尔之行,而且很奇怪,她还想起了安东·斯克里奔斯基。噢,天啊,谁能忍受总是回忆旧时光?她能忍受,回忆逝去的一切。她看了看周围,寂静的冰冷的星光下这雪的世界,这是一个天国,象一盏魔灯照出的景致。马什、考思塞、伊尔克斯,一一出现在这普照的魔灯之下,还有一个不真实的欧秀拉的影子,整个一出超现实的皮影戏。一切是那么虚幻,象魔灯之影,但又不是漫无边际。她希望不曾有过去,她想只和伯基在一起,从天堂沿着滑坡,一下滑到这个地方,不要再在童年艰涩的回忆中跋涉,回忆她的成长,让所有的一切都过去吧,她觉得记忆象是给她开了个恶作剧式的玩笑。为什么她要有“记忆”,这是什么伦理吗?为什么不可以来个洗礼,开始新的生活,让往事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在,和伯基在一起,她才在这高山雪原的星光下重新回到了尘世。她和她的父母、她的祖先到底有何相干呢?她知道她现在已脱胎换骨,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