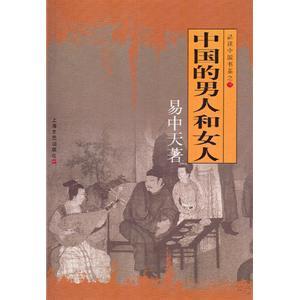爱恋中的女人-第5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还用说。”古德兰戏弄他。
欧秀拉站起来走开了,留下他们三个人在一起。
古德兰从吉拉尔德手里接过画,又仔细地看了起来。“当然,”她又开始嘲弄,“你是理解你那学艺术的学生的。”他扬了扬眉头,自豪地耸了一下肩。
“这个小女孩吗?”吉拉尔德指着画片问。
古德兰端坐着,图画摊在膝盖上。她抬起头来直视吉拉尔德,那目光仿佛要刺瞎他的眼睛。
“他难道不理解这个女孩吗!”她嘲弄地开玩笑说,“你只看着那双脚,它们多么可爱啊,多么美丽,多么纤细——噢,它们的确很棒,很吸引人,真的。”
她慢慢抬起眼,目带炽火,直视勒尔克,那份热烈的赞赏注满了他的心胸。他似乎陡然长高了许多,对她更多了些尊重。吉拉尔德还在审视塑像的那双脚,它们彼此半搭着,羞羞答答地,还有些害怕。他看了很久,完全被『迷』住了,然后几乎是忍痛割爱般把画拿开,一种失落感涌上来。
“她名叫什么?”古德兰问勒尔克。
“马奈特·马·威克。”勒尔克回忆着说,“是的,她漂亮,很清秀——但有时也很烦人,她是个调皮鬼——没有一刻能安静——除非我使劲掴她一巴掌,打得她哭起来,然后她才能老实地坐几分钟。”他在考虑他的作品,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只是他的工作。
“你真的打她了吗?”古德兰冷冷地问。
他瞥了她一眼,读懂了她眼神中的挑战。
“是的,我是那么做的。”他若无其事地说,“我这辈子从未那么重地揍过其他人。我必须,必须那样做——那是我唯一可以做我的雕塑的方法。”
古德兰那双大大的带着阴郁的眼睛瞪了他一会儿,她几乎在琢磨他的内心,然后沉默地抵下头去。
“你为什么要把戈迪瓦夫人雕刻得如此年轻?”吉拉尔德问,“她那么小,而且还坐在马上——那么大一匹马——这么一个孩子。”
勒尔克的脸抽搐了一下。
“是的,”他说,“我不希望她能再大些或再老些,她十六、七、八时最美丽的时候,再往后,她对我来说,就没有用处了。”一阵沉默。
“为什么没有了?”吉拉尔德问。
勒尔克耸了耸肩。
“我发现她不再有趣——不再美丽——对我和我的工作没有什么好处。”
“你的意思是女人过了二十岁就不再美丽了吗?”吉拉尔德问。“对我来说是这样,二十岁之前,她们年龄娇小、纤细、柔嫩,那之后,不论她是什么样的,对我都不再有了吸引力,米洛的维纳斯是个布尔乔亚,她们都是布尔乔亚。”
“你一点都不喜欢过了二十岁的女人?”吉拉尔德问。“她们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对我的艺术也没有用。”勒尔克不耐烦地重复着,“我觉得她们不美丽。”
“你是个享乐主义者。”吉拉尔德说着,讽刺地大笑起来。“那么男人又如何呢?”古德兰突然开口问。
“噢,是的。他们在任何年纪都是好的。”勒尔克回答说,“男人应该强壮,有力——他老或年轻都不要紧,只要他们有那副体格,一种粗野、笨重的体形。”
欧秀拉独自走入外面纯净新鲜的雪地中。但那耀眼的白雪似乎刺伤了她。她感觉到那冰冷几乎使她窒息。她大脑麻木发呆。突然,她想走开,一个奇迹般的念头——她即将走入另一个世界——冒了出来。在这永恒的冰雪中,她感到那么绝望,永不可摆脱。
突然,仿佛奇迹一般,她记起在远方乌黑的沃土在她脚下延伸,一直向南伸展到一片黑『色』的土地,那里长满了黑『色』的桔树、柏树和灰『色』的橄榄树。栎树的簇簇针叶,指向蓝天,撒下满地浓荫,奇迹中的奇迹——这死一般的沉寂,冰冻的雪顶世界并不是世界的全部!一个人可以离开它,与它脱离联系,你可以走开。她想立刻实现她的梦想,她几乎想立刻与这个冰雪世界脱离关系。这个可怕的静止、冰雪筑成的山脊。她想去看黑『色』的沃土,去闻闻大地的芳香,去看看那坚韧的冬菜,感受那阳光,触『摸』那待吐的花蕾。
她愉快地走回旅馆,充满了希望。伯基正躺在床上看书。“鲁伯特,”她脱口而出,“我想离开这儿。”
他慢慢地抬起头来。
“是吗?”他温和地反问。
她坐在他身边。双臂环着他的脖子。他如此不慌不忙,使她很吃惊。
“你不想吗?”她困『惑』地问。
“我没想过。”他说,“但我想我也会的。”
她猛地坐直了身体。
“我恨这儿。”她说,“我恨这雪,那么不自然,它反『射』在每个人身上的光线都那么不自然,可怕地耀眼,使每个人都有一种不自然的感觉。”
他平静地躺着,大笑着,思索着。
“那么,”他说,“我可以离开这——我们可以明天就走。我们明天去维罗纳,去作罗密欧与朱利叶,坐在圆形剧场里看戏——好吗?”
突然,她困『惑』、害羞地把脸埋在他肩上。伯基还跟没事人似地躺着。
“好的,”她温柔地如释重负般地说,她觉得她的灵魂仿佛长出新的翅膀,现在他如此洒脱。“我会喜欢罗密欧与朱利叶,”他说,“我亲爱的。”
“在维罗纳那可怕的寒风中,”他说,“穿过阿尔卑斯山,我们可以闻到雪的气息。”
她坐起来望着他。
“你喜欢去吗?”她困『惑』地问。
他的眼睛眯起来,笑出了声,她的脸靠着他的脖子,紧贴着哀求道:
“别笑我,别笑我嘛!”
“为什么,怎么了?”他笑着双臂搂住了她。
“因为我不喜欢被别人嘲笑。”她低声细语。
他吻着她那头光滑、散发着芳香的秀发,还在不停地笑着。“你爱我吗?”她一本正经地细声道。
“爱。”他笑着回答。
突然她抬起头,把嘴唇送过去让他吻。她的嘴唇紧绷着,颤栗着,热烈如火,而他则柔软、深切,细敏,他们久久地互吻着,然后一阵悲哀爬上心头。
“你的嘴唇如此坚硬。”他微微不满地说。
“而你的很柔软很舒服。”她愉快地说。
“你为什么老是咬着嘴唇?”他不无遗憾地问。
“别在意。”她快速地说,“这是我的习惯。”
她知道他喜欢她,她确信这点,但她却无法放松自己,不能忍受让他如此怀疑她,然而她因被爱而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想法。她知道,当她委身于他时,她虽快乐却总也不免有几分伤感。她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去跟随他,但她无法控制自己,不敢赤『裸』『裸』地走向他,把心毫无保留地交给他。她或栖身于他,或抓住他,从他身上寻找欢乐。她很喜欢他,但他们从来未在同一时刻达到完善的结合,总有一个人步子跟不上。虽然如此,她还是很高兴地处于幻想之中,光彩闪烁,自由、充满生机和活力。而在此刻,他则安静、温柔而有耐心。
他们开始为第二天的出行作准备。他们先去古德兰的房间,而她和吉拉尔德已经穿上晚上室内便服。
“古德兰,”欧秀拉说,“我想我们明天会离开这儿,我无法再忍受这里的雪了,这使我的皮肤和心灵受到了伤害。”“这真的使你的心灵到了伤害吗?”古德兰惊讶地问,“我可以想象这雪会伤害你的皮肤,——太可怕了,但我想对心灵却有净化作用。”
“不,对我不是这样,它只是伤害了我。”欧秀拉说。“真的呀!”古德兰叫。
房间里一阵沉默。欧秀拉和伯基可以觉察到古德兰和吉拉尔德为他们的离开而松了口气。
“你们要去南方?”吉拉尔德的口气中带着一丝不安。“是的。”伯基沉着地转过身去。近来这两个男人之间有些奇怪而无法说清的敌意。伯基总的来说,处于恍惚、冷漠的状态。自从到了异国以来,他一直漂流在昏暗、流畅的水面上,不闻不问,很有耐心。而另一方面,吉拉尔德则紧张、感情炽热、『性』子急躁:两个男人彼此抑制。
古德兰和吉拉尔德对于两个人的离去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为他们准备一切,就像对待两个小孩一般。古德兰拿着三双『色』长筒袜走到欧秀拉的卧室,随手扔在床上,她对袜子的讲究是出了名的。这几双是厚真丝袜,一双粉红,一双菊蓝、一双灰的。它们是在巴黎买的。灰『色』的那双是手织的,看不出针脚、很重。欧秀拉高兴极了,她知道古德兰能给她这样一些好东西,心里一定是很爱她的。
“我不能拿走你的这些东西,古德兰。”她惊讶,“我不能把它们从你身边夺走,这是你的宝贝。”
“是我的宝贝!”古德兰依依不舍地看着自己的宝贝,“它们是不是招人喜爱?”
“是啊,你应该留着它们。”欧秀拉说。
“我不需要了。我另外还有三双。我把它们送给你——我希望你拥有它们,这是你的,放这儿——”
她的双手激动地颤抖着,把三双袜子塞到欧秀拉的枕头下。“谁得到这些可爱的长筒袜都会感到莫大的荣幸与快乐。”“是的。”古德兰回答,“最大的快乐!”
她坐进椅子中,显然她是来和欧秀拉道别的。欧秀拉因为不知她想得到什么,便静静地等待着。
“你觉得吗,欧秀拉,”古德兰疑『惑』地问,“你有要永远地离开,不再回来的那种感觉?”
“噢,我们会回来。”欧秀拉说,“火车旅行不是个问题。”“是,我知道。可从感觉上,可以这样说,你们都要远离我们了。”
欧秀拉颤了一下。
“我一点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些什么,”她说,“我只知道我们要去某个地方。”
古德兰等着她往下说。
“你们高兴这样做吗?”她问。
“我相信我会很高兴的。”欧秀拉回答。
但是,古德兰更加注意到了她姐姐脸『色』无意识流『露』出的兴奋,而不是她口气中的不确定。
“但你难道不认为你仍然想要保持和这个旧世界的联系吗?——爸爸,还有我们其他人,也就是说,英国和整个这个意识空间——你难道不认为要创建一个新世界,你会需要这些吗?”欧秀拉沉默不语,极力地什么都不想。
又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天空蓝蓝的。微风绕于群峰之间,风中飘扬着雪花,象把宝剑般锋利。吉拉尔德带着男人的成熟走出来。今天早上,古德兰与他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但他们俩自己却不知不觉都带了副平底雪橇出了门,留下欧秀拉和伯基在后面。古德兰身着猩红和品蓝——一件猩红滑雪衫和帽子,品蓝『色』裙子和长袜,由吉拉尔德陪伴着兴奋地在雪中滑行。吉拉尔德身着白『色』和灰『色』,在前面拉着雪橇。他们跑得远远地去爬陡峭的雪坡,身影越来越小。
古德兰自己仿佛已完全融进白『色』的雪野中,她成了一个纯净的,没有思维的水晶石。当她顶着风爬上坡顶向四下望去时,她看见一山一山的岩石和白雪,耸立在碧蓝的天宇下。在她看来,她正处身在长满丛丛鲜花的园中,而她正以她的心灵来采摘它们,她几乎无法分心去注意吉拉尔德。
当他们从陡峭的山坡疾滑下时,她紧紧抓住吉拉尔德。她觉得刀的意志正在经受磨刀石的磨砺,如火焰般锋利的磨刀石,两边的雪飞溅,像是磨刀石四『射』的火星。四面的白雪越来越快地飞奔,白『色』的山地如火焰般迎面扑来。她如一个小球冲进火海一般冲入了这白花花的世界中,似乎要被溶解了。坡底有个大转弯。他们仿佛旋转着落到地面,结束了他们的运动。
他们停下来休息一阵。但当她站起来时,她却没能站住,她发一声奇怪的叫声,便转过来倒向吉拉尔德。她的头耷拉在他的胸前,晕在他怀中,她整个瘫倒在他身上,一时失去了知觉。“怎么了?”他问,“是不是玩得太累了?”
但她什么也听不见。
当她苏醒过来时,她站起来向四周看了一下,很奇怪,她面无血『色』,眼睛却异常光彩照人地圆睁着。
“怎么回事?”他又问,“你很难受吗?”
她那双明亮的眼睛望着他,仿佛经历了一种彻底的改变,接着便兴奋地大笑起来。
“不”她大叫着,带着胜利的喜悦,“这是我生命中最完美的一刻。”
她望着他,发出那种着了魔般的笑声,肆无忌惮又令人『迷』『惑』,像一把利刃刺入他心脏。然而,她却不在乎,甚至根本没有注意。然后他们又一次爬上斜坡,又再次迎着白『色』的火焰冲下来,相当精彩。古德兰大笑着向下冲,身上挂满了雪水晶。吉拉尔德玩得棒极了。他觉得自己可以如此娴熟地驾着这平底橇,穿上云霄,直入天宫。驾雪橇对他来说,仿佛是一种力量的发泄,他只需动动胳膊。这一切都像是本身固有的天『性』。他们继续探索了其它斜坡,以寻找一个更佳的雪场。他觉得一定还有比现在更好的地方。终于,他如愿以偿,找到了一个很长很陡的滑坡,经过一块巨石的根部,一直冲入山脚的那片树林。他知道,这里很危险,但同时他知道,路,他强烈希望用他的手指。“我想,”终于他不情愿地说,“鲁伯特是对的——一个人需要一个新环境,从旧的世界中摆脱出来。”
古德兰望着她姐姐,目不转眼,不为所动。
“一个人需要一个新环境这个我没意见。”她说,“但我认为新的世界应是旧世界的发展,若是只和另一个躲起来,把自己与世隔绝,则根本不是找到了一个新世界,而是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幻想中,保护自己。”
欧秀拉望着窗外,她的思想中开始进行搏斗。她很害怕,很害怕语言的力量,因为她知道,常常是三言两语就能使她相信她本来根本不相信的东西。
“也许,”她说,带着对任何人,包括对她自己的不信任说,“但是,”她又加了一句,“我也相信,如果一个人那么在意旧的世界,那他就不会得到任何新的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甚至,与旧环境搏击,你也是属于它的。我知道,人常常会一时兴起要终止旧世界,就去反抗它,但那是没有用的。”古德兰沉思着。
“是的,”她说,“在某种意义上讲,如果一个人是在旧环境中,他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你要脱离它,难道不是个幻想吗?毕竟,无论是阿布鲁兹的一间农舍或者其它的叫什么的地方都不是个新世界,不是!对付这世界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彻底看透它。”欧秀拉目光转向一边。她实在很怕这种争论。
“但那儿总有一些别的什么,不是吗?”她说,“从你心灵深处看透世界,到你行动上的看破红尘,还有很长的间隔,而且当人的心里看破红尘时,他已经是另一个人了。”
“一个人能从心里看破红尘吗?”古德兰说,“如果你的意思是你可以看到将来会发生的什么事情的话,我不同意,我真的不敢苟同,无论如何,你不可能立刻飞向另一个星球,只因为你可以看透这个星球。”
欧秀拉忽然挺直起身体。
“是的,”她说,“是的——大家都明的!人与这个世界没有联系了,一个人有另外一种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