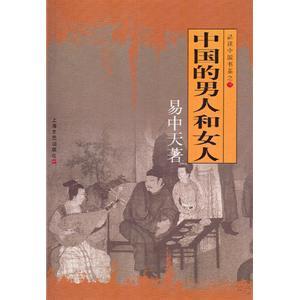爱恋中的女人-第6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睁着她那大大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勒尔克,他低下头去,躲开她的目光。
“不,别去巴黎。”他说,“在那里不是推崇爱情,就是信仰什么新主义或者寻找什么新的救世主。一个人每天总是这样。还不如去骑旋转的木马,到德累斯顿吧。那儿有我的一个雕塑室——我可以给你工作——嗯,那是十分容易的,我还没有看过你的任何作品,但是我很相信你,来德累斯顿吧——那是个生活起来比较舒服的城市,在那儿生活,你会很满意的,那儿什么东西都有,只是没有巴黎的愚昧和慕尼黑的渺小。”
他坐着,冷漠地看着她。最让她喜欢的就是,他像对自己一样纯真而坦诚地和她说话。他是一个艺术方面的同行,首先是她的同伴。”
“不要去巴黎,”他继续说道,“那个地方让人恶心。呸——爱情,我憎恶它。爱情,爱情——无论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我都憎恨它,女人和爱情,那是最无聊的。”他大嚷道。
她有些生气。但这也是她自己的感觉。男人和爱情——也是最没有意思的。
“我的想法也一样。”她说。
“一种乏味的事。”他又说了一遍,“我戴这顶帽子和那顶帽子都无所谓,爱情也是一样的。我戴某一顶帽子,只是为了方便,同样也是为了方便而需要爱情,我告诉你,夫人——”然后他的身体靠近她,接着很奇怪地挥了挥手,好像把什么扔在了一边,“小姐,别在意——我告诉你,我愿意放弃一切,所有一切,包括你的所有的爱,来结成一种精神上的小小的伴侣关系——”他的眼睛眨了眨,向她发出一种隐秘而阴险的目光,“你理解吗?”他问道,『露』出一点笑容,“只要那个女人能够理解,不管她是一百岁还是一千岁我都不在乎——对我来讲都是一样。”他双眼很快地一眨。
古德兰又很恼火了,那么,他不觉得她长得很漂亮吗?她忍俊不禁地笑了。
“我还需要等八十年才能达到你的要求。”她说,“我长得很难看,是不是。”
他用一个艺术家的敏锐的拥有鉴赏力和判断力的眼光打量着她。
“你长得很漂亮。”他说,“我为此而感到高兴。不过,这可不是原因——不是这个。”他大声说。他那种强调的语气让她心中很高兴,“而是因为你有一种智慧,一种理解力——而我呢?我又小又弱,很不足道,哦,可别要求变得英俊、强壮,那就是我,”——他很奇怪地把手指放在嘴上——“就是这么个我在寻觅我的情人,就是这个我在期待着你做我的情人,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特别的智慧成双成对——你能理解吗?”
“是的。”她说,“我理解。”
“至于另外一个,那个爱情——”他把手一甩,好像要把很讨厌的东西扔掉一样——“不太重要,那不重要,我今天晚上喝不喝白葡萄酒,有什么关系吗?这无关紧要,所以这种爱情,这种接吻也是这样,有或没有,今天,明天或永远没有,都是一样,无所谓的——和喝不喝葡萄酒一样。”他说完以后,头很奇怪地低下去;表示强烈的否定。古德兰在很认真地盯着他,她脸『色』很苍白。
忽然,她伸出手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的确是这样。”她热烈地大声叫道,“我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理解才是最为重要的。”
他抬起头来看着她,几乎是带着惊慌躲闪的神情,接着,他有些不太高兴地点点头,她放开了他的手,但是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他们很沉默地坐着。
他忽然抬起头,用他那自大的预言家的眼光看着她,说,“你知道吗?你的命运将会和我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一直到——”他猛地又停住了,做了个鬼脸。
“一直到什么时候?”她问道,脸上没有血『色』,嘴唇也发白,她对这种不祥的预言极为敏感。可他只是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
吉拉尔德直到夜『色』降临的时候才回来。他没有在四点钟赶回来和她一起喝午茶。雪正好厚得可以滑雪。他自己一个人,套着滑雪板在白雪覆盖的山坡上滑了很长的路。他爬到了山上,爬得特别高,能看见五英里之外的山顶的关口,可以看见“圣母小屋”——一家座落在关口顶峰的小旅馆,半埋在积雪之中。还能看见远处深谷的对面是一片昏暗的松林,可以从那条路回家。可是一想到家他就直恶心,甚至发抖。他可以从那儿滑下去,至关口下面那一条古老的帝国大路上,不过,为什么要到大路上去呢?一想到要回到这个现实世界中,他就浑身不舒服。他需要永远在这雪中呆着。他独自一个人是多么开心,独自一个人在高高的山上如飞一般地滑雪,掠过覆盖着的发着光彩的雪层下的黑『色』岩石,飞向远方。
但是他感到心中有一种象冰一样的东西在冻结,身上那坚持了很多天的奇特的忍耐力和单纯的气质正在慢慢地消失。他又要成为那可怕的激情的痛苦的牺牲品了。
所以,他十分不情愿地下了山,向在两座山峰交界处的山谷中的房子滑过去。他看到了房子里灯光昏暗,便停下不前,希望自己进去不要看到那些人,听到那些吵闹的声音,感觉人群当中那种混杂味。他的心灵是紧闭的,好像心脏是在真空管当中,或者纯净的冰壳之中。
就在那时他看到了古德兰,心中猛地愣了一下。她显得气质不凡,雍容华贵。此刻她正冲着那个德国人在笑。他心中突然有种欲望,想杀掉她。他心里想,杀了她该是一种多么大的肉欲上的满足啊。整个晚上,他一直心不在焉,总在想着积雪和激情。他的脑中一直在想着要能掐死她该是一种多么大的肉欲上的满足啊,把她生命的火花一颗颗地掐灭,掐得她永远动弹不得,软软的,松松地在他的双手中软肉一般地躺着,完全死了。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永远而且最终占有她,那将是多么大的肉欲的满足啊!
古德兰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像平时一样平静而温和。他那种亲切的样子反而让她对他产生了冷酷的心。
她来到他的房间,他已脱掉外衣。她没有注意他看着她的时候所『露』出那种完全因为憎恨而引起的奇异而又兴奋的目光。她站在门边,一只手放在身后。
“我一直在考虑,吉拉尔德,”她说,冷漠的语气中带着无礼,“我不应该回英国。”
“哦,”他说,“那你要去哪儿?”
但是她没有理会他的问题。她要把自己的话很有条理地讲出来,她必须把已经想好的话说出来。
“我看不出回去有什么意义。”她接着说,“你和我之间的关系已经结束了!”
她停下来,等着他开口说话。但是他什么也没说。他心中在想,“结束,是吗?我想一定是结束了。但是还没有结束,别忘了还没完。我们一定要用某种方式来最后结束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有一种结局,一种最终的解决措施。”
他心中这样自语道。但是,他嘴上却什么都没说。
“过去的都已过去了。”她接着讲,“我不后悔任何事情,我希望你也不后悔。”
她等着他说话。
“噢,我不后悔任何事情。”他很随和地说。
“那太好了。”她说,“那太好了,我们都毫不后悔了,就是该这样。”
她停了下来,整理思路。
“我们的尝试失败了。”她说,“不过,我们可以在别的地方再试试。”
他的心中隐约地又冒上了怒火。她好像是在故意地逗他,惹他发火。她干什么要这么做呢?
“什么样的尝试啊?”他问。
“做情人的尝试,”她回答说,略微有些不好意思,但是好像她并不把讲这事当成什么重要的事。
“我们俩成为情人已经失败了吗?”他大声地又说了一遍。他内心中自言自语地说:“我必须马上杀了她。现在只有一件事我需要做,那就是杀了她。”一种一定要把她置于死地的欲望完全占领了他的整个心灵。而她对此却一点都没有察觉。“不是吗?”她问道,“你认为这难道是一种成功吗?”这个无礼的问题所包含的侮辱又让他全身的血『液』都胀了起来。
“在我们的关系当中,也有一些成功的成分,”他回答讲,“结果——这,这本来是可以成功的。”
但是,在他说出最后那句话时,他停了停,甚至在他讲这句话之前,他都不清楚他要讲什么,他知道那是决不能成功的。“不,”她回答说,“你不会爱!”
“你能吗?”他问道。
她的那双圆圆的黑眼睛好像两个幽幽的月亮在看着他。
“我不能爱你。”她毫不掩饰地对他讲出了真情。
他的头脑中扫过十分夺目的闪光,他浑身却在震颤。他的心中燃有一团烈火。他的意识已经进入到他的手腕上,到了手中。他的心中只有一个欲望,那就是要杀她而不能够自制的欲望。他的手攥得紧紧地,只有当手在她的脖子上合拢的时候,他才会满足。然而,还没等他转过身子对着她,她的脸上有一种顿时醒悟的十分狡猾的表情,一眨眼她已经跑到了门外,她快如闪电地冲入了自己的房间时,把自己反锁在屋中。她心中特别害怕,但却很有信心。她知道,自己的生命在悬崖的边缘上打着颤抖。可是,她对自己的立足之地却有一种十分奇特的自信心。她知道她的聪明智慧会战胜他的。
她站在房间里,十分激动地不停地打颤,她明白自己最终可以战胜他,她可以凭借自己清醒、聪明的头脑。但是现在,她也清楚这是一场非常严峻的搏斗。一不注意,就有可能死在他的手上,她有一种既紧张又兴奋的病态的情绪,这就是一个人面临着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的危险,而并不向下看,不承认害怕的时候所具有的那种感觉。
“我后天就要离开这儿,”她自言自语道。
她只是不想让吉拉尔德认为她是害怕他,认为因为她怕他才逃走了。可是她一点都不怕他。她知道,逃避开他的人身侵犯只是她的一种防卫措施。不过,她甚至都不害怕他的人身侵犯。她想要向他证明这一点。一旦她证明了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一种人,她都不会害怕他,一旦她向他证明了这一点以后,她就远远地离开他,永远地。可是同时她也明白他们俩之间的斗争虽然是很可怕的,但并没有什么决定意义。她想建立起自信心,虽然她会遇到很多的威胁与困难,她都是不会被吓倒的。他既不能够吓倒她,也不能够控制她,更不能够对她使用任何权利。她要一直地坚持下去,直到她证明了这一点。一旦这一点被证明了,她就永远地摆脱开他了。
但是,她还没有向他或者向自己证明这一点呢,这就是之所以她仍然没有脱离和他的关系的原因。她受控于他,她不能够超越他而生活,她在床上坐着,身上裹着被子,脑子就这样没完没了地思前想后,一直这样呆了几个小时,却好像什么思路都没有。
“看起来他并不是真正地爱我,”她自言自语地说,“他不是,他希望他所遇到的每个女人都爱上他,他甚至并不知道他在这么做,但是,那就是他,在每个女人面前,他都要展示出他那男『性』的魅力来,表现出他极大的欲望,他希望每一个女人都能知道,和他相爱,那将是最美妙的事。他故意地不去搭理女人,这是他用的一种小把戏,他可从来不会不去注意女人的。他本应该是一只小公鸡,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可以在五十只母鸡——他的部下面前耍一耍威风。但是,真的,我的确对他这位唐璜没有了兴趣。我若扮演起女唐璜会超过他的唐璜无数倍,他很让我厌烦,你知道,他的男子汉的气概很让我厌烦,再没有比这更加愚蠢的了。他生来就那么傻,这么自以为是。真是这样,这些男人自以为是地不可救『药』了。这真是让人感到很可笑——这些神气的家伙们。
“他们都差不多一样。看着伯基,他们浑身上下除了有自负的骨头和肉,还有什么?的确,只有他们那滑稽的局限『性』和内部的空虚才会让他们这么自以为了不起。
“至于勒尔克,他的内心却比吉拉尔德要充实千百倍,吉拉尔德受了那么大的局限『性』,他已经到了头。他只会在古老的石磨上永远地磨下去。其实,根本没有任何谷粒在两个磨石之间,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磨了,可见他依旧在磨啊磨——提着同样的东西,相信着同样的事情,做着相同的事情——噢,我的天啊,就这样下去的话,连石头的耐『性』也会最终被磨光的。
“我并不是崇拜勒尔克,可无论如何,也是个十分自由的人,他不会死死地坚持着自己男『性』的自负。他并没有安分守己地在磨那古老的石磨。哦,天啊!我一想到吉拉尔德,我一想到他的工作——那些在贝德欧佛的办公室,还有那些矿井——我的心中就直恶心。我和那些有什么关系!——他还自以为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女人的情人呢!一个人还不如去找一个很自满的电线杆当情人更好呢。这些男人,靠着他们的永久的工作——他们那上帝的永久的石磨,连续不断地空磨着!太让人厌烦了。我怎么会看上他呢!
“至少在德累斯顿,一个人可以把所有这一切都抛于脑后,可以找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去做。如果去看看艺术体『操』的表演,看着法国的歌剧和戏剧,是满让人高兴的,去感觉一下德国艺术家的生活也会十分开心。而勒尔克是一名艺术家,一个自由的人。在那儿一个人可以避开那么多很可怕的、让人生厌的重复,看不见那些很俗气的言行的重复,这可是件最重要的事。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在德累斯顿找到永远的灵『药』,我不能这样自己骗自己。我知道那是不大可能的事。但是我可以离开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熟人、自己的这个和自己的那个。我将把自己安置于那些没有自己的财产、没有自己的家和仆人的人当中去,安置于那些没有名气和地位,没有身份、并不属于哪个范围的人当中去。哦!上帝啊!这种复杂的人使一个人的脑子如钟表一般地在不停地运转,机械,单调,没有任何意义。我是多么憎恨生活啊!我是多么憎恨啊!我是多么地恨象吉拉尔德这样的人!他们一点花样都不会改变。
“肖特兰兹!——天啊!想想看要住在那儿,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再一个星期。
“不,我不愿去想这件事——那让人太受不了!”
然后,她忽然停下来不去想了,很害怕。她不能再忍受下去了。
她想到了日子一天接一天,这样如此机械地永远地交替下去。她不禁地心咚咚直跳,心中感到十分忧虑,时间滴答滴答的可怕的束缚钟表时针的快速转动,这个时间的永远的重复——噢,天啊!这所有都是那么可怕,而且没有任何逃避的办法,不可能逃避。
她几乎是希望吉拉尔德现在能够和她在一起,把她从那可怕的想法当中拯救出去。噢!她是受了多大的折磨啊!孤独地躺在那儿,面对那可怕的时钟,听着它那没有休止的滴答声,她是受了多么大的折磨啊!整个生命,她的整个生命都融入其中,滴答,滴答,滴答,接下来的便是钟表的敲响,然后又是滴答,滴答,指针也随着移动。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