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成吉思汗-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影机前手舞足蹈,杂音却明显小得多——干扰仍然在,不过却变得若有似无,不仔细听,听不出来。我的直觉是:这个异象和先前珊嘉提到那副眼镜一样,不是巧合,就是珊嘉真有萨满法力。萨满在作法的时候,最讨厌电力在一旁捣『乱』,所以,她的精神力量压制了附近的电波干扰。
但这只是后来的臆测,我当时并没有计划要做点简单的实验,以搞清楚珊嘉的“法力”是怎么回事。说实话,真要这么硬干的话并不怎么得体。珊嘉的言行叙述很有说服力,而我也得到一个好机会,一窥成吉思汗时代的遗产,这就够了。事实很明显:珊嘉的家人、族人,都把这位“老婆婆”当成萨满精灵的化身,我看不出她有假冒的嫌疑,或是打着萨满的名号行骗。在部落族人的眼里,珊嘉是个未卜先知的活神仙,遇到疑难杂症,可以找她商量,她是他们信赖的朋友。珊嘉并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也因为人们的这种信仰,使珊嘉保存了成吉思汗以降的萨满传统。
珊嘉的家人非要保罗帮他们拍张相片,否则不放他走。他们面带微笑地排成一列,这会儿的珊嘉换上吐瓦的传统服装,怀里还抱了个裹着襁褓的娃娃。保罗跟我的感觉一样,都很喜欢这个不造作又和气的老人家。他问了她最后一个问题:你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她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会告诉他们,要尊重自然,因为你就是自然!照顾好给你水喝的小溪大河,照顾好让你暖和的空气,照顾好养育你的土地!”看来,这位吐瓦老婆婆的箴言真有流传的价值。
在蒙文中,这个词是“天子”的意思,而这位“天子”就是前文提到的大巫师阔阔出。
在蒙古,九是幸运数字,七,可不怎么好——原注。
这是一种把谷粒打下来的农具,由木柄和拍打器两个构件组成,但从后文看来,作者所谓的连枷,其实更像中国的拂尘。
珊嘉的家人非要保罗帮他们拍张相片,否则不放他走。他们面带微笑地排成一列,这会儿的珊嘉换上吐瓦的传统服装,怀里还抱了个裹着襁褓的娃娃。保罗跟我的感觉一样,都很喜欢。
第一卷 第十二章 永恒象征
我前往蒙古的主要目的,就是看看蒙古悠久的传统在现代还剩下多少。这一趟路跑下来,我并不失望。从我跟保罗骑马出了额尔登尼召的大门开始,屈指算来,一个多月了。我们和我们的蒙古朋友,赶着大批备马,首先在石龟的四周,绕了一圈,而那石龟却是克剌和林宫仅存的遗迹。克剌和林宫是为了纪念成吉思汗的丰功伟业而兴建的。在那段时间里,我们见识了杭爱高原繁花似锦的鲜丽景『色』,跟先前我们走过的肯特省、半冰冻的贫瘠土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们也拜访了饲养猎鹰的哈萨克猎户、访问过一位萨满传人、跟黑死病死神擦身而过,还惊喜地发现:七十几岁的老喇嘛,熬过20世纪30年代的整肃,满怀信心地要恢复蒙古的宗教传统。
在挥别珊嘉之后,我跟保罗、“大夫”回到了乌兰巴托,我们四处打探阿乌博德、巴雅尔和戴尔哲的下落,但始终没有他们的消息。问了许多人,每个人都摇头,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跋涉过那片不『毛』之地,显然,他们的估计不准,推进到巴颜乌古烈需要更多的时间。一直到第二年的1月,“大夫”写信给我,我才知道阿乌博德一行人在9月间才抵达目的地。“大夫”也不清楚他们究竟是在哪一天赶到巴颜乌古烈的。他不怎么瞧得起阿乌博德,不过,根据他的判断,还是有三个人完成了这趟艰苦的旅程。我想他没错,这趟旅行真的是有些折磨人。他们平均的速度只有阿乌博德跟葛瑞尔预估的三分之二。如果,他们真的要骑马远征西欧,我希望他们能把这次的教训记在心里。
阿乌博德在新年的时候,很礼貌地寄了张贺年卡给我。但是,他并没有描述旅程的经过,也没有再提及跨洲旅行的壮举什么时候展开。稍后,巴雅尔寄来一卷影片,我倒是从里面发现了一些信息。这是他在前往巴颜乌古烈的途中拍摄的,其中一景是:他们在为马匹钉马蹄铁。这跟他们原先的信仰不合,钉马蹄铁的手法也很生硬。马匹被缚捆好,掀翻在地上,马蹄铁也是因陋就简,找当地的铁匠胡『乱』打造一副,并不是出自远征队的成员之手。我想,以蒙古马的坚忍,被他们胡整一两次,应该还挺得住,但常常这样搞,又要这些马踏上跨洲的征程,大概没走多久,全都得跛脚。
从“大夫”的信上,我也知道我们的赠马还是被留在巴颜乌古烈过冬。看来那批伙伴终于克服了偏见,说服自己:哈萨克人其实并不吃马,因为在那附近可能找不到蒙古部落帮他们照顾马匹。他们终于学会了自助长途旅行必须经历的一课:要信任沿途民族的人们,跟他们合作。“大夫”并没有告诉我,葛瑞尔是不是打算重新归队,巴雅尔、戴尔哲明年会不会跟阿乌博德继续未完成的旅程,越过阿尔泰山,进入哈萨克共和国,一路杀到法国。从国际的角度来看,这趟旅程的可行『性』不高。他们必须横越的苏联领土上处处『骚』『乱』,经济失调,民族纷争不断,沿路的苏联加盟共和国『政府』自顾不暇,哪有心思照顾这批远道而来的过客?
苏联解体带来厄运。
蒙古的光景也大不如前,问题逐一迸发,前途晦暗不明。我和保罗在草原上驰骋的那个夏天,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最后的美好岁月,旧有的秩序大致完好,人民生活还算稳定,但是苏联的扶持与经济援助,在那时已经到尽头。苏联不只撤走了驻军与各种军事设施,对蒙古的援助也因为国内生产一落千丈而不得不大幅削减。以往,就个人的平均值来说,蒙古接受的苏联援助要比古巴高,称得上是东欧集团中最得宠也最引人注目的国家。
蒙古的厄运才正开始。苏联改口说,先前的援助并不是赠与,而是贷款,是要还的。蒙古『政府』当然还不起,苏联『政府』立刻施展铁腕,断绝油料供应。以往蒙古都是靠苏联提供油料,并没有别的来源,这一手顿时让乌兰巴托方寸大『乱』,蒙古的交通系统全面瘫痪,国家的分配系统也随之瓦解,依靠外来资源供给的区域,特别是首都,陷入一片恐慌。也因此,蒙古出现了一种极端不协调的现象:他们拥有比人口还多的牲口——羊、牛、马、山羊,首都人民却没有肉可以吃,更不用说蔬菜了。
“大夫”在信上说,乌兰巴托的人民已经开始领配给卡了。冬天才过了一半,国营商店的货架上就见不到羊肉了,只剩下黑市还有一些小贩在偷偷贩卖新鲜骆驼肉,可是数量也不多。面粉几乎找不到了,囤积是违法的。西方的媒体报道,乌兰巴托的主『妇』要很仔细地把阶梯上的面粉扫干净,
免得让人发现他们在黑市买面粉,留下把面粉袋扛进屋里的证据。
这个盛产牲口的国家,突然之间,面临了空前饥馑的困境。蒙古『政府』已经向日本寻求人道援助;没有食物,只好把一瓶瓶的『奶』酒分给大家。首都经济濒临瓦解,苦苦支撑,证明了我们的朋友康保先生——也就是先前提到的那个地方官员——确有先见之明:如果能改善牧民在原野间的生活,他们的日子还会比较舒服,犯不着挤到已经没有容身之地、大而无当的乌兰巴托去。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越是混『乱』、越是压力重重的年代,蒙古人民就越怀念成吉思汗。19世纪70年代,普热杰瓦斯基发现,蒙古人民始终相信,成吉思汗会复活,解民于倒悬;他认为这是人民不满满清『政府』的压迫所产生的一种反动思想。蒙古人民说,成吉思汗的不朽身躯还蛰伏在鄂尔多斯成陵中伺机而起,“成吉思汗仍在墓中沉睡,只是凡人不知道罢了”。1911年,也有类似的谣言流窜,当时的蒙古人民揭竿而起,反抗满清『政府』的统治,他们希望成吉思汗跨马而来,助他们一臂之力。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就连外国人都来利用成吉思汗的余威,不过,对成吉思汗奉之若神的蒙古人民来说,根本不在乎其中的差别。“疯男爵”恩琴自称是成吉思汗复生,尽管他是个白皮肤的巴尔干人,许多重要的大喇嘛照样支持他,使得乌尔戛一度混『乱』。
一个世纪之后,法国出现了一本名为《蓝蒙古人的蓝标准》(the blue standard of the blue mongols)的演义小说。在故事中,蒙古的男女变成了骑士淑女,技艺惊人,有着超人般的能力。这本小说没有半点根据,又是出自外国人的手笔,翻成蒙文之后,却成为当地的畅销小说。成吉思汗时代的行为模式和信条,依旧深深影响着蒙古人民,也难怪他们看到这本荒诞无稽的书,感到特别亲切。
全蒙古的共同认同。
成吉思汗的荣耀至今仍然深植在牧民的记忆里,掌握了这一点,我跟牧民共骑时,就更能了解他们的心态。他们的生活很固定,任何可以增添生活滋味的小趣味,对他们来说,都是莫名的惊喜。而尽管外界物换星移,变化得相当快,他们仍然坚持传统的蒙古生活。他们觉得,“真正的”蒙古人不会住在乌兰巴托,应该像他们一样,在原野漫游。不管是在肯特省,还是在杭爱省,不管是养羊、养牛还是养骆驼。我们在路上碰到的牧民,绝大多数都很赞赏我们的计划——骑马横越蒙古高原,唤起大家对成吉思汗的记忆,重建中古驿站传统。
奇怪的是,同一批蒙古牧民,对我们蒙古之外的行程却没多少兴趣,只是不断追问我们在蒙古旅行的各种细节:我们在蒙古要走什么路线?从这个爱马克到下一个爱马克要走哪条路?我们对曾经造访过的地方有什么观感?他们的好奇心让我们了解,这些牧民虽然东飘西『荡』,四处为家,但他们的足迹所及之处,也有一定的局限。他们并不会在蒙古各地放牧,多半会待在他们的苏木和爱马克附近,偶尔到乌兰巴托观光而已。他们也不怎么认识他们的国家,尽管蒙古有丰富多样的面貌,他们也只能从苏木中心的电视管窥一二。也许,对成吉思汗的追念是全蒙古共同的民族认同。蒙古人散布在高原的不同角落,平常并没有机会来往,成吉思汗是他们心灵上的交集。
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个历史上的代表人物,在蒙古,能一肩挑起这份荣耀的,当然非成吉思汗莫属。自蒙古有文字以来就维系不坠的祖先崇拜,更加深了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的追念。卢布鲁克的足迹遍及全蒙古,到处都看得到这种现象。糅合了转世思想的祖先崇拜,是喇嘛教的核心教义。在蒙古政教合一的领袖,是活佛,一直到这个世纪初,活佛转世这种继位方式始终奉行不逾。第八代呼图克图过世时,蒙古人民革命党甚至被迫公开宣称,活佛转世的系统至第八世而绝。为了说服一般的乡民,他们说第八代呼图克图放弃往生,要他们死了这条心。
对成吉思汗的记忆却没有这么容易根除。蒙古官方一度否认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共同祖先,但是对成吉思汗的思念,却依旧深藏在每个人的心中。与蒙古紧邻的中国曾经饱尝蒙古铁骑的侵略之苦,但他们反而尽力保护成吉思汗的遗迹,争取蒙古文化的正统。1939年,国民党『政府』把传说中的成吉思汗的“遗体”从鄂尔多斯高原移到较为安全的甘肃省。十年后,国民党政权还是觉得不安心,又把这“遗体”往西迁移。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把这副残存的骨骸送回到内蒙古,把成陵扩建成蒙古人民的信仰与朝圣中心。
要测量蒙古人民对成吉思汗的无尽追思,其实并不难。苏联控制蒙古的这七十年里,在泯灭成吉思汗的遗产方面称得上不遗余力。宣传整肃,外带全面的“现代化”,都没有磨损蒙古人民对他的记忆。在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中,蒙古的社会组织被彻底翻新,经济面貌为之一变,人民生活大幅改善,但是成吉思汗在这个古老国度的分量,不曾减轻一丝一毫。这趟蒙古寻根之旅目的是寻找蒙古文化的根,我亲眼看到苏联统治的负面影响。语言、民族艺术、区域特『性』、传统技艺、古老的传统信仰,被侵蚀得面目全非。看到我最感兴趣的文化特『色』逐渐没落,我当然心痛,但苏联进驻后,对蒙古人民有了正面助益。苏联顾问、苏联科技、苏联训练彻底改变了普热杰瓦斯基跟布斯卓眼中的蒙古,现代蒙古不再是落后、了无生气的穷乡僻壤。举个例子来说,布斯卓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一个奇怪的理论:蒙古人很少洗澡,是因为他们认为这辈子和水接触多了,下辈子会变成鱼。让这位女士震惊不已的“肮脏蒙古”,如今不复存在。
保罗跟我先前提过好几次,那一阵子,我们俩一天到晚都是脏兮兮的,特别是在吃饭时,尘土飞扬,不知道到底吞了多少泥沙。在那样的环境里,本来就很难把自己打理干净,加上一天到晚都在骑马赶路,日子过得异常简陋,也实在顾不了这么多。虽说如此,在蒙古原野上,懒得洗澡的人如今已经是异类了,因为大家都慢慢养成了卫生的习惯,城市阴暗角落的流民反而比他们更邋遢。只要我们在小溪或是湖边扎营,就能看到牧民在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总会拿着肥皂『毛』巾去洗个澡。
牧民和马紧紧相依。
在成吉思汗的时代,蒙古牧民赶着牲口,在蒙古高原漂泊,居无定所;如今的蒙古人无复古风,已经没有办法这样大规模地游牧了。最初是满清『政府』圈地,限定蒙古牧民只能在一定的范围里放牧。然后,喇嘛占去了蒙古大部分的土地,许多人沦为农奴,就算以放牧为生,也没人敢侵入喇嘛庙的产业。其实在成吉思汗时代,长距离的游牧也很少见。在蒙古的核心地带——肯特省与杭爱省,牧民干湿两季间的迁徙,常常只是近距离的搬家而已,与现代的放牧大队根据上级指示夏冬两季迁换牧地的范围差不多。现在的牧民一年大概移动蒙古包两三次,而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可能要逐水草移上个六次。在蒙古,处处可以见到传统游牧生活的遗迹:大部分人没有固定的居所,财产简单,可以随身带着走;贫富则依照牲口的数目来判定。游牧时代尊崇的价值:向往自由、个人独立负责、家庭自给自足,依旧散布在所有蒙古牧民的心中。
蒙古牧民完全符合我的期望:他们刻苦耐劳、友善好客。一般的蒙古人民至今还是在贫瘠的土地上讨生活,他们全力投入,使尽全身的精力,却不见得能挣到什么。首屈一指的蒙古专家兼旅行家——欧文?拉提摩(owen lattimore)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穷牧民才是真牧民。”他的判断放在现代蒙古来看,确实有道理。这个国家太穷了,没有足够的资源克服天然限制;蒙古虽然是亚洲的心脏地带,却是一颗不会跳动的心。人民以游牧为生,保留了大量中古时代的习俗。现代牧民虽然穿着工厂出品的靴子和衣服,用便宜的进口餐具吃喝,经常使用塑料制品,但基本上与他们的祖先没有两样,就只差在他的父兄以前是向中国商队买这些东西。他们住的毡帐、每天都离不开的马鞍、马缰及绑头发用的生皮,马衔上用的生铁,都是自己做的,跟中古时代的蒙古人一模一样。蒙古人最珍爱的小玩意儿——粉红盖的镶玉鼻烟壶、花式
![今夜有鬼----续2 寻找阴间 ([今夜有鬼系列ⅱ]第二部) by 黯然销混蛋封面](http://www.38xs.net/cover/noimg.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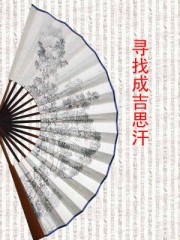
![[剑网三]寻找帮主夫人大作战封面](http://www.38xs.net/cover/8/854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