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成吉思汗-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一个坚忍无畏的英国女人,布斯卓女士(beatrix bulstrode)对蒙古人的印象也差不多。她在《蒙古之旅》(a tour in mongolia)里写道:“没看过蒙古人干过正经事,他们大概一辈子也不曾工作。”她曾经两度从中国到蒙古,足迹遍布蒙古草原。她第一趟旅行是靠牛车和小马,在内蒙古漫游。第二趟胆子就更大了,竟深入西伯利亚,直抵蒙古的首都乌尔戛(urga)。当时目无法纪的盗匪盘踞蒙古,内战冲突不断,所以,她在第二趟旅程开始前,准备了四把枪才上路:一把拆卸了的猎枪,塞进蓬蓬装的内衣周围;一把『毛』瑟枪(mauser);一把大型的柯尔特手枪(colt)放在她的大衣里。“口袋里还藏了把小家伙”。这个浑身都是武器的小辣椒,说服了《时代》周刊驻北京的特派员福雷瑟(david fraser),资助她写她的新书,福雷瑟对她的支持毫无保留,完全受她的蒙古观点左右。他说布斯卓“对蒙古人『性』格的分析,别具慧眼。蒙古人纯朴、天真、乐观,就是懒得厉害,不怎么实际。蒙古人的这种天『性』在过去、在未来,替他们惹了不少麻烦。简单来说,他们没有跟外界竞争的能力”。
《时代》周刊驻北京的那位特派员、布斯卓及其他批评者,都没有抓到蒙古的真精神,他们从自身的文化出发,怎么看都觉得蒙古人是个懒洋洋、不思上进的民族。根据他们的看法,这个民族惟一适合的工作,就是在草原放牧羊、牛、骆驼,依循时节变化,逐水草而居,自由自在;要他们安分下来耕地,会要了他们的老命。在蒙古人眼里,庄稼就是束缚,荷着锄头、翻田除草,就是奴隶。20世纪20年代初期,较为先进的耕种技术引进蒙古,但是蒙古的农民种植作物,也还是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种子撒好了,就不知道晃到哪里去了,再也没有回来照顾农田。
蒙古国的地位
从空中往下望,对现代蒙古的第一印象,还是一片空『荡』。在这个横跨三个时区的国家,只有一个地方堪称都市;有五百人以上的聚落,全国数一数,不超过五百个。机翼下是一片光秃的山脊,苍凉阴郁,渺无人迹,成群的小斑点是嶙峋石坡间觅食的羊群。每隔三四十英里,才见到一个圆圆的蒙古包,像是草原上迸发出的草菇,那是牧羊人的家。蒙古包是一种圆顶的毡帐,打从成吉思汗扬名立万前,它就是蒙古人的住处。西方人管它叫毡包(yurt),也是普热杰瓦斯基惯用的名词。乌兰巴托的住房短缺,是个始终解决不了的问题,上百个蒙古包于是堂而皇之地进驻城中街道与郊外的社区,大多通上了电,但是没有排水沟跟自来水,到了晚上,每个蒙古包里泛出隐隐的萤光,全都在看电视。在现代化的都市中出现蒙古包,仿佛时空错置;但蒙古点缀旋在苏联式的成排公寓之间,其实并不突兀。这里的公寓外表简陋,腐蚀的铸铁阳台下残留着一道道的锈斑,使它看起来更加狼狈。杂『乱』的天线电线纠结成堆,扭曲的涂鸦,脏『乱』的共通大门,让人望之生畏。不过这种水泥公寓里至少有中央空调跟自来水,冬天还算过得去。而住在蒙古包里的人,就只好在屋顶和“墙壁”上多蒙上几层毡毯,勉强过冬。
蒙古趁中国无暇外顾之际,宣布独立,结束了几世纪以来与中国的宗主关系。没过多久,1921年,『共产』党开始统治这个发展停滞的封建国家。当时,蒙古的独立意识弱不禁风,无力抵御从中亚席卷而来的俄国『共产』革命怒涛。就在同时,沙皇驻西伯利亚的部队崩解,沦为盗匪,从北边侵入蒙古国境。
在这些入侵者中,就数浑号“疯男爵”(mad baron)的恩琴(baron von unger…sternberg)行径最为嚣张,所到之处,几无完土。而他除了这块角落之外,也无其他容身之处。他率领了一支由波罗的海地区白军(white army)少壮军官组成的叛军,结合了支持沙皇的非正规部队,组成亚洲骑兵师(the asian cavalry division),夺取蒙古的政权。从他留下的照片看来,他有一张如鬼似魅的脸孔,大约四十岁,额头很高,发线后退,苍白的眼神闪烁出疯狂的光芒。他穿着传统的蒙古长袍,高领用常见的丝穗系住,胸口挂着圣乔治十字星勋章(star of the saint george cross)。中西合璧的怪异装扮,反映了他融合东方与西方世界的企图。他计划组成一支蒙古部队,重返西伯利亚,赶走红军,建立一个直抵亚洲海滨的国家,继续效忠沙皇。他在乌尔戛建立的政权虽然短暂,却杀人无数,将首都附近被劫掠一空,纵火烧尽。他手下的恶棍只要逮到疑似布尔什维克党员,不由分说,当场枪毙。恶名昭彰的疯男爵部队引起了蒙古人民的极度反感,所以,红军向蒙古首都挺进的时候,疯男爵的手下只得带了一些支持沙皇的新兵,仓皇撤退。1921年8月21日,恩琴被红军逮捕,送往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拘禁,几个月后,遭到处决。据说,在审判时,法官要他唱国际歌的第一段,唱得出来,『性』命可保。但他唱的却是俄罗斯国歌。就在这几个月里,红军利用西伯利亚通晓蒙古语的间谍,重新取得了乌尔戛的控制权,并改名为乌兰巴托。在红军的羽翼之下,幼弱的蒙古『共产』党宣布执政,使得蒙古成为世上历史第二悠久的社会主义国家。
自此之后,蒙古的历史就难挣脱苏联的阴影。蒙古人民革命党忠实的仿效莫斯科的一举一动,从斯大林主义,到布里兹涅夫(brezhnev),到最近的改革开放。理论上,蒙古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化、苏维埃化的国家,拥有新生的活力,把封建的过去抛在脑后,迎接社会主义的朝阳。但是,到了1990年的春天,西方的新闻媒体却报道乌兰巴托发生了第一起民主示威。人『潮』中,有人高举着一张海报:“蒙古男女,上马吧!”
他在《蒙古现代史》(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中写道:“文明世界的历史中,19世纪的蒙古史,堪称是最空白的一页。”——原注。
原文见《蒙古任务:十三、十四世纪方济修道士中国、蒙古传教书信与口述选》(the mongol mission: narratives and letters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in mongolia and china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christopherdawson编辑,sheed and ward;1955——原注。
欧洲最长的河流,注入里海。
与美国相比,蒙古的面积比阿拉斯加(alaska)略大百分之三,但是,人口密度只与内华达(nevada)一样——原注。
在古生物学中,很少见到aviraptor这个字。从这个字的字根来看,指的应该是一种会飞的掠食『性』生物;但是,从仅见的文献来看,这种恐龙究竟会不会飞还有待考证。而这个字在中文里也没有适当的翻译,在内蒙古戈壁沙漠中,古生物学家曾挖掘出大量的古似鸟龙,从地缘关系和特征看来,应该就是作者看到的恐龙化石。
mongolia; the tangut country; and the solitudes of northern tibet,e。 m。 morgan译——原注。
great captains unveiled; 1927——原注。
一种因为异常染『色』体受孕,导致先天智力不足、患者容貌鼻子扁平的症状。
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位女士勇往直前的强悍劲儿。第一趟旅行,这位女士是独自上路的,第二次,她找了个伴——任职中国海关的戈尔(edward gull)。戈尔说她是个“小辣椒”。后来,她嫁给戈尔——原注。
乌兰巴托的旧名。
就是在西部片里常见的六发左轮手枪。
这是一个从俄文演变过来的字,原意是居住、家。
mongolia; the tangut country; and the solit
第一卷 第三章 秘 史
在乌兰巴托,我跟阿乌博德第一次见面,正当我们两个吞吞吐吐,互相猜测对方的话意时,他的哥儿们葛瑞尔,就这么冲进我们的房间。葛瑞尔是典型的蒙古骑兵后裔,身高大约六英尺,跟一般蒙古人相比,他算是高的,全身紧绷,桀傲不驯,凶恶的脸庞上是一头狂放的深黑头发,长长的、油腻腻的,又留了个傅满州(fu manchu)式的胡子,怎么看,都觉得他有几分邪气。他讲话的口气跟吵架一个味儿,满腔怒气好像无法遏抑,随时会爆发出来似的。
葛瑞尔是职业雕刻家,纤细的手指,秀气的手掌,跟他粗野的相貌完全不搭调。他是个粗豪的汉子,绝不扭捏作态。他很『迷』打猎,雕刻的尽是些鹿、熊或是大角羊之类的动物,惯用的材料是骨头或是鹿角,完工的作品随意放置在石头、『毛』皮与羽『毛』之间。他『射』杀过十几只熊,其中一只的皮就铺在他小小的公寓地板上,猎枪则斜倚在沙发的背后,有人来,葛瑞尔就拿出他最得意的相簿炫耀,里面是看来有些粗糙的黑白照片,一张张记录着他的野营营地、猎友,少不了他踩在动物身上的骄傲时刻。
葛瑞尔与阿乌博德两人都是浪漫派。阿乌博德的梦想受困在办公室内,葛瑞尔则是一个职业向导,能用营火烧一桌好菜、在马背上打盹、轻易地缚好马鞍。他走起路来,总带着股神气劲儿,看得出来,他是个活力充沛、不知该怎么发泄的人。他的表情看起来让人不寒而栗,事实上,他很乐观,喜欢帮助别人,一心一意想走完这趟艰苦卓绝的旅程。只是启程前,他一直是愁眉苦脸的模样,话很少,神『色』严峻,眉『毛』始终纠在一起。
阿乌博德和我都觉得该把我们最新的计划方向,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一声;趁着这空当,他就去找些健壮的马匹及几个可以一道上路的伙伴,组成远征队。
试骑之旅
在我第一次到乌兰巴托之后,又在1989年10月与翌年4月,两度重返故地。每一趟,我都敦促他们定下清楚的行程计划,可每次所有的时间却都花在捉『摸』阿乌博德的心思上,试着为他伟大但空洞的想法理出个头绪来。或许通盘的计划,还需要从长计议,但我总希望,计划的组成要素能一点一滴地就位。由于行程展开在即,我建议他们利用一整个夏天,把马赶到蒙苏边界,把马匹留在那里休息给养。这个行程的目的是让我预估一下,骑马跨洲长征的可行度到底高不高;按照蒙古的老法子骑马到法国,又会碰上什么问题。但是,阿乌博德却不想进行试骑,打算先拖一年,再一鼓作气从乌兰巴托杀到法国,中间根本不作任何停留。他并没跟我解释为什么要拖上一年,我也始终没搞清楚,所以我花了好大的耐心说服他接受一步步来计划。
我每去一趟乌兰巴托,就会发现我的蒙古朋友信心更坚定了:他们一定要用蒙古的传统方法进行蒙古式的冒险。此时,我的心念一转,觉得当个观察者也很好,只要从旁提供咨询就行了,该我说的,我就说,其他时间袖手旁观,其实是一种奢侈。即使他们不理睬我的建议,可能也是因为,在蒙古的土地上,应该依照蒙古作风行事。这对我来说,是个观察现代的蒙古人如何安排长程旅行的绝佳机会。我对自己说,这支由阿乌博德和葛瑞尔率领的远征队,前途一片大好:阿乌博德是做官的,懂得行政协调;葛瑞尔是野外专家,有能力替行程打理具体事项。我的印象是这两个人有很长的合作历史——事后证明,我错了,他们只一起打过几次猎而已。
阿乌博德总算拿定主意了:计划的第一步,是7月出发,在夏天横越蒙古。葛瑞尔从旁建议,5月时我们可以有一次试骑,地点是肯特省(hentei,一拼成hentiy)的荒野,据说这是成吉思汗早年活动频繁的龙兴之地。这想法正合我意,我可以在野外实地测试装备,尤其是那部『迷』你摄影机,还可以观察有意加入远征的志愿者,掂掂他们的斤两。
还是一样,没有人清楚我们要去肯特省的哪里,距离大概有多远,更不用说地图了。或许是安全的原因,这里的地图不易取得,更可能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公开印行过。我只知道我们会花上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到乌兰巴托东北角的肯特省爬一座高山。葛瑞尔花了不少心思制作了两块椭圆形的青铜雕刻,每一块大概有十二英寸宽,这是他要放在那里的纪念品。第一块青铜刻的是少年成吉思汗,二十岁左右,英姿勃发,那时他正转战各个部落之间,威震大漠;第二块是成吉思汗晚年最著名的一幅画像,现存台湾的故宫博物院。成吉思汗的后裔在中国建立了正统的王朝——元朝,一个世代之后,宫廷画师根据文献完成了这幅作品。在成吉思汗晚年,蒙古铁骑正席卷华北,进占中都,南宋王朝岌岌可危。画像中的成吉思汗已是晚年,被画师诠释成传统的中国帝王相貌,慈眉善目,脸部线条柔和,留着一圈山羊胡,竟然还有几分儒者风范,完全不像是从草原奋战崛起的一世枭雄。
暮春5月,出发在即,距离我第一次到乌兰巴托,已经整整七个月。葛瑞尔蹲在两块铜雕前面,把它们放在一张有些斑点、满是破洞的防水胶套上面,小心翼翼地黏到大理石板上。这两块有点像墓碑的大理石板,稍后要在他们选定的地点竖立起来。大理石板上刻着垂直书写的蒙古文,行云流水,还用红漆仔细描过。这种蒙古文字是成吉思汗的直接遗产之一,也是现代蒙古文化变迁的见证。也许是因为处于文化的十字路口,蒙古人一向对文字有一种狂热,勇于尝试各种新的文字,于是源自西藏、近东及苏联的文字都成为他们取材的对象。在成吉思汗崛起的时代,蒙古是没有文字的,当时的蒙古人想来也用不着。后来,成吉思汗命令他的下属根据维吾尔人的文字制订蒙古文,从此以后,便以蒙古文作为这个庞大帝国的正式书写文字。成吉思汗逝世之后,继续流传了七百多年,直到『共产』党上台。当权的『共产』党采纳了苏联顾问的建议,废除传统蒙文,代以“现代的”斯拉夫拼音文字。
每个蒙古人都得学习这种斯拉夫拼音法,学校里再也不教传统的蒙文。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移植新文字的计划暂且搁置,但是,到了1945年,还是雷厉风行地推动起来,结果,这个草率的改革计划严重摧残了丰富的蒙语遗产。蒙语中许多发音跟细微的变化,无法在斯拉夫拼音中找到精确的字母,于是蒙语被迫简化或是改造,勉强套上这层语言上的紧身衣。深谋远虑的蒙古人,开始担心正统的蒙古文化后继无人,只好把孩子送到中国境内的内蒙古去受教育,说来讽刺,当地的蒙古土著倒还有机会学习正统的蒙古文。
一晃眼,五十四年过去了,这个政策终于得到了改正的机会。乌兰巴托当局宣布,决定将恢复传统蒙文作为蒙古改革措施中的一个环节。他们计划让传统蒙文再度成为蒙古的官方文字,只是没人了解具体的步骤。有人估计,单单更替『政府』单位里的打字机,就要花费两年的『政府』总预算。官方的事情,让做官的去伤脑筋,在葛瑞尔的青铜雕像上,如果出现来自外国的斯拉夫文,再怎么说,也不伦不类。
秘史之谜
葛瑞尔刻在青铜板上的文字,取材自一本研究成吉思汗生平的“圣经”
![今夜有鬼----续2 寻找阴间 ([今夜有鬼系列ⅱ]第二部) by 黯然销混蛋封面](http://www.38xs.net/cover/noimg.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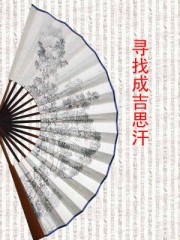
![[剑网三]寻找帮主夫人大作战封面](http://www.38xs.net/cover/8/854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