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成吉思汗-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个小时之后,那匹驮马终于想出报复的方法——逃走。它选走的时机很好:牧民牵它过河时,刚刚踏上另一边的河岸,它猛然掉头,牧民一个不留神,缰绳脱手,那匹马便朝来路狂奔而去,终于自由了。我们这支零零落落的队伍停了下来,看着那匹驮马越跑越远,消失在地平线附近。几个年轻人纵马或前或后地追赶上去,看来,他们早就想要自由自在地让马跑一下。现在是休息的好时机,我、保罗与并骑的巴雅尔抓住空当,赶紧下马。前面几个人也停下来了,看看我们身后抓马的年轻人,什么时候可以得手。身边有一棵老树干,我们三个就把马系好,坐在地上,伸伸酸痛的两条腿。
过了一会儿,我才想到当下正是写笔记的好时机,我一拐一拐地走到马旁,从鞍囊中取出笔记本。我们的三匹马挨在一块,我想也没想就顺手推开其它两匹马。这几匹马都是蒙古牧民精心挑选的好马,个『性』温和,从蒙古人的标准来看,是相当规矩的,但是,我马上就发现它们毕竟野『性』未驯。浪『荡』惯的蒙古马,有时是很偏执的。如果陌生人是很有自信、很缓慢地挨近蒙古马的身边,它还会安安静静的,就算是它觉得这个人穿著打扮、气味都有点古怪,还不至于发作。但是,千万不要在它屁股后面干什么,只要碰它一下,蒙古马都会发飙。
我在接近我的马时,不小心拂了巴雅尔的马屁股一下,这牲口的两只前脚立刻就立了起来,一脚踢到缰绳,细细的生皮缰绳应声而断,这匹马也跑走了。还好它只跑了几百码,跟前面的那群马汇在一起。一个艺术家顺手拉住了它。巴雅尔走过去想把它牵回来,但绑马尾的医生正好在马上,已经掉头把马牵了回来,半路上,医生的坐骑不小心踩空了,医生顿时从马鞍下滚了下来,马和巴雅尔都吓呆了,一回过神,发现两匹马都没命地往邻近小丘跑去。看到这般热闹的场景,保罗拿起身边的照相机,想要捕捉这混『乱』的一刻,但是,『骚』『乱』也吓到了他的坐骑,它也“啪”的一声,拉断了缰绳跑掉了。一时之间,我们有三匹脱缰野马在旷野上『乱』跑,每一匹马又吓到另外两匹,情况混『乱』,已到失控边缘,我们的向导翻身上马,在树丛和落石之间觅路前进,追赶我们逃走的马匹,没一会儿,他们也消失了。
半个小时之后,他们又出现了,牵着马,表情看起来有些严肃。他们跟巴雅尔说了几句话,巴雅尔的脸马上就垮了下来。他们告诉他,他最珍视的脚架原本挂在马背上晃『荡』,但现在怎么找也找不到。他的马老在树丛边跑来跑去,脚架可能被什么东西刮了下来,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巴雅尔的心情坏透了,那支古董脚架可是蒙古电视电影厂的宝贝,在这种国家,就连零件都没得换,更何况是整支脚架都不见了!等到那头捣蛋的驮马被牵回来,大家再度上马前进的时候,闷闷不乐的巴雅尔再也笑不出来了。两个小时之后,大伙儿停下来抽烟,休息完了之后,巴雅尔一上马,却发现脚架还在老地方晃『荡』。牧民的嘴都快笑裂了,他们把他的脚架藏起来,存心开他一个玩笑。蒙古人看起来一脸老实木讷,原来也挺有幽默感的。
在普热杰瓦斯基的笔下,一般的蒙古牧民被形容成:“宽阔平坦的大盘脸,颧骨很高,鼻孔贲张,眼睛细长,一对招风耳,黑『色』的头发看起来有些粗糙,有的留着疏疏落落的小胡子,有的蓄着络腮胡,皮肤晒得黝黑,体格粗壮魁梧,肩膀的宽度好像还长过身高。”他们毫不矫饰,待人和气,非常容易相处。蒙古牧民规矩负责,很尊重能干和有经验的人。在我们这个团队中,态势很明白,大家都惟视丹比多尔扎为领袖。他是个留平头的驯马高手,对于肯特省的荒野地形了若指掌,每天前进多少英里,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该停下来休息,全听他的,休息得差不多了,丹比波尔扎叽哩咕噜地说几个字,大家就会上马继续前进。
每次停下来休息的情况都差不多。丹比多尔扎闷不吭声地把他的马引到一边,勒住马缰,下马。他身后的牧民跟着下马,朝丹比多尔扎走去,这时,他应该已经坐下来了。他的坐姿很怪,一只腿伸得长长的,另外一只屈膝,屁股往脚跟上一搁,全身『乱』『摸』找烟。牧民会挨到他的身边,有的用同样的坐姿坐下来,围成一个紧密、体己的圈圈。香烟敬来敬去,一盒火柴传来传去,鼻烟壶也经常在这个场景中出现。
牧民身上零零碎碎的东西全部塞在腰带里,演进下来,腰带的前端变成了一个随身囊,从里面拿东西,与从别人手上接东西都有一定的规矩。比如说,把鼻烟壶递给别人的时候,要右手伸直,左手呈杯状,托在下面,才有礼貌;受者也要用同样的姿势,恭谨地接过来,把鼻烟壶放在手掌上,端详一下,称赞它的雕工精巧。然后,用一把细长的抹刀,挑开鼻烟壶盖,取出一点鼻烟,再用夸张的表情,深吸一口。最后盖上壶盖,右手托着鼻烟壶,用刚刚的姿势交还给鼻烟壶的主人。主人再次客气地把鼻烟壶递给下一个人,鼻烟壶一定要转一个圈圈才行,在这套繁文缛节中,他们的坐骑都在一旁乖乖地看,马蹄连扬都不敢扬,牧民手里牵着缰绳,好像身后跟了一头大狗。
我没想到单单是谨守传统、欣赏工艺,也能带给这批牧民这么大的乐趣。他们喜欢在马鞍两侧镶上银饰,只要看到了精巧的工艺品,他们都衷心艳羡。我们有个导游是爱打扮的小伙子。他穿了一件鲜绿『色』的丝质短马甲,亮得让人睁不开眼,高高的领子偏偏又是张扬的怒红『色』,还镶了一圈金边。他的刀可不是常见的现代产品,而是一把镶饰考究的古董刀,细细长长的,装在一个银鞘中,平常就看到他把这把宝贝刀『插』在身后的皮带里。银鞘上还特别剜出了两道凹槽,安放着镶了银边的象牙筷子,鞘上系了一根银练,画出一个半圆的弧形,拴着打火的燧石荷包。这荷包也是用银子镶过的。他的朋友相当欣赏他身上的小玩意儿,不是称赞两句,就是过来『摸』一『摸』,打量一番。有一两件细致的小玩意儿,大伙儿就已经够羡慕的了,如果还拿得出有点历史的古董,就更不得了。这种态度倒是跟蒙古官方相反,他们对历史没有好感,一讲到过去,就让他们联想到蒙古落后的封建制度。
治马之道
牧民对他们的马匹不特别体贴,也不特别坏,只把它们当成草原游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但也因此就必须细心照顾它们,否则很难在草原上生活下去。他们没有其他交通工具,草原茫茫,都得靠马匹来帮他们运输、工作。就算只有二十步的距离,能骑马,他们绝不走路,马鞍始终放在马背上,马匹随时待命奔驰。所以,蒙古人一般就是在马背上上下下,有许多备用坐骑,一般来说,牧民懒得给马取名字,不过却一眼就认得出自己的马。蒙古牧民多半在腰带前面『插』一支破破烂烂的单筒或双眼望远镜,远远看到一群马在吃草,他们会策马跑上个五六英里,根据颜『色』、体态和走动的样子,找出属于自己的马匹。这些牲口都是他们自己养的,有什么特征一清二楚。新诞生的小马,也只能在妈妈身边待上一个星期,适应环境之后,就会由牧民接手管教。马儿生病了,也没见过他们用现代的医疗方式或器具,全靠老祖先留下来的传统方法医治。马蹄长脓,他们就端来一盆营火余烬,把马蹄往里面一按;背疼,就用盐水擦洗,简单极了。
放血,在蒙古几乎被视为万能疗方。第一天旅程刚刚结束,丹比多尔扎就认定这批马的情况不好,经过长期寒冬的煎熬,它们必须放血。他和三个牧民悄悄走近马的身边。这些马刚刚被放开,缓跑几步,舒活筋骨,在草原上吃草,浑然不知危险已近。放血之前的准备动作,看得旁人心惊胆战:只见几个人猛然揪住马匹的鼻箝,再在它的下颚加了一道生皮缰绳,死命地往下扯,让它的嘴巴张得开开的,丹比多尔扎用布把刀裹得紧紧的,只『露』出大约一公分的刀尖,看准了马匹的上颚,然后在马齿的后端猛然一刺,一串血滴就这么滴了下来,马好像一点也不疼,反而一个劲儿地『舔』血。然后,牧民给这匹马套上特殊的头套,要不就是塞个粗木头到它嘴里,让它合不拢嘴,直到伤口自然凝结,才会让它自由。
五个小时的奔驰之后,我们在溪边觅得了一处营地。一道小溪藏身在一块冰雪下面,汩汩流出,让马匹跟骑士都有水可喝。除了拿支好像在赌场收赌注的抹板,轻轻地替马匹刮掉干了的汗渍之外,蒙古人不怎么照顾坐骑,他们就只是放开马匹,任它们散散步,吃点草。特别顽皮的马就不能自由了,如果它不安分,蒙古牧民会把它和另外一匹马绑在一起,头贴着头,让它不能『乱』跑。可是蒙古小马好动成『性』,不是那几道枷锁拘束得住的。就算是跟另外一头马绑在一起,它还是伏在地上撒野,打个滚,全身『乱』扭,想甩掉拘绊,直到快把同伴勒死才肯罢手。然后,这两头倒霉的马只好像兔子一样地跳,找点草吃,活像是两人三脚的竞赛者。我从没见过蒙古人多喂什么秣料、谷物、干草给他的爱马,就算是牧草藏在冰雪之下,已经完全冻毙,牧民照样袖手旁观,让马匹在一天的清晨与奔驰过后的傍晚,自己找吃的,自己休息。这样的马匹第二天还能跑上八小时。
简陋的饮食习惯
巴雅尔在营地旁边,把炉子支好了。炉子是四方形的,不用的时候,可以拆成几块,平放在驮马的背上;这种炉子还附有三截锡制的烟囱,设计得相当有效率。木材塞到炉子里面点燃,就可以准备吃的了。一大壶的水往炉子上一放,只消十分钟,就煮滚了,咕噜咕噜的直冒泡。巴雅尔开始煮茶,这还是我们这一天第一顿餐,他从一个好像是装烟草的布袋中,拿出一块茶砖,茶品质之差,前所未见。
蒙古牧民可不在意。他们对简陋的生活习以为常,早期到过蒙古的旅行家就感叹过这一点。“他们没有蔬菜、『药』草,什么东西都没有,有的就是肉,能吃的很少,别族的人靠这么点食物,大概早饿死了。”这是卡庇尼的感想,别忘了,他是修道士,早就习惯俭朴的生活,隔三差五还要斋戒,但是,连他也受不了蒙古的食物,而且还嫌蒙古的卫生环境很差:
他们不用餐巾,没有桌布……两只手脏得要命,都是动物的油脂,胡『乱』往绑腿上擦,或是抓把青草一抹……他们从不洗盘子,顶多就是用肉汁冲一下,里面的残肉还会流回锅里。偶尔他们也会想到要洗洗锅子、调羹或是其他厨具,但仍是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
普热杰瓦斯基对蒙古人煮茶的方法也很反感,提起来就犯恶心。“煮茶的过程可怕极了,”他是这么写的:
煮茶的壶从来没有洗过,顶多就是用干马粪、牛粪擦一擦。煮茶通常用盐水,找不到盐水,他们就在水里加点盐。先用刀从茶砖上砍一块下来,放进臼中捣一捣,接着把茶叶倒到滚水中,加几碗牛『奶』。茶砖硬得像石头一样,为了让它能软一点,蒙古人会把茶砖放在新鲜的马粪或牛粪中,吸点湿气,但是,粪便的味道也就沾染在茶砖上了。这还是第一阶段,如果看开点,本质上和我们煮咖啡或巧克力的方法一样,没有多少差别。但是,蒙古人还会把切成块状的肉及炒过的粟米放在碗中,以便增添风味,最后,他们还要放进一团牛油,或把油腻腻的羊尾巴油脂放进茶中。读者现在可以想像这一碗脏兮兮的东西,对外国人来说,有多难接受了,但是,蒙古人一喝就喝一大缸!
普热杰瓦斯基说,一般蒙古人喝个二三十碗,不算稀奇。蒙古有钱人用的碗,精雕细琢,镶金包银,喇嘛用的是人头饮器,头颅切成一半,再镶上银座。
保罗和我一人分到一个小铜碗,传统造型,却是现代产品。我们也高兴地发现,蒙古的卫生状况比起普热杰瓦斯基时代改善多了。我们饿得要命,一整天没吃东西了,什么东西放在面前,大概都会风卷残云,一扫而空。但我们很快就发现,打从普热杰瓦斯基那时开始,有一件事情倒是一点也没有变:蒙古人煮菜的方法还是那一套,煮开一锅水,把食物往里面一扔就完了。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发现蒙古人根本懒得去炙烤,就算有油,他们也不会炒一炒。我听到的理由是:蒙古牧民讲求效率,没有时间做顿好吃的,但是,就算他们回到蒙古包,还是用这种方法填饱肚子。我的亲身经验却不是如此,尤其在这漫长无聊的傍晚,我的感受特别强烈,
我觉得蒙古人就是喜欢吃煮的东西,其他做法都勾不起他们的食欲。我们那位爱钓鱼的“大夫”,有一次一口气钓到十来条看起来很像鳟鱼的鱼,但是,他们的做法依旧没变:先把内脏掏出来,该砍的砍,该剁的剁,然后往滚水里一扔,煮熟的鱼一点鲜味都没有了。
队里有几个人对“大夫”钓上来的鱼有点猜疑,他们比较喜欢——事实上,只要有机会,他们一定会吃——羊肉,对别的肉类没半点兴趣。虽然根据卡庇尼的记载,那个时候的蒙古人还喜欢吃狗、狼、狐狸、马,甚至于体虱。“虱子吃我孩子的肉,喝我孩子的血,我为什么不能吃它?”卡庇尼冷酷地记载道,“我看过他们吃老鼠。”
羊肉与茶
我们的蒙古朋友说,他们也喜欢吃牛肉和骆驼肉,实在没东西吃了,他们也会吃马肉。但是,羊肉始终是他们的最爱,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向客人展示“正确”的宰杀和烹煮羊的方法,观者的胃一定要很强韧,才不会吐出来。宰羊之前,要先把羊翻过来,用膝盖抵住这只可怜的动物,像是摔跤手制服对手一般,然后用利刃飞快地在羊腹上剖一刀,在羊还没死透之前,伸手进去,一直伸到心脏的大动脉附近,用力一揪,把心脏揪下来。死掉的羊还会颤抖好一阵子,整个过程没看到多少血溅出来。羊皮很快就被剥掉了,胃里还没消化完的草料,被扔到一旁,其他部分——内脏、头颅、肉、骨头——全都可以吃,迟早也都扔到大锅子里。在如此严酷贫瘠的游牧世界中,只要能放进口中——也许羊耳朵例外——都不能浪费。卡庇尼说得好:“不管是吃的,还是喝的,没有好好利用,就是罪过,连骨髓都要吸出来,才能赏给狗吃。”卡庇尼的观察相当透彻。几个星期之后,我们一群人坐在帐棚里,分食煮得半熟的羊内脏,羊尸体就放在帐棚中间的地上。大伙儿吃饱了之后,有人把剩下的内脏往帐棚外扔,给两只一直在帐棚外打转的狗吃,但我发现,狗不怎么想吃羊的内脏。
好吧,就算有人觉得吃两顿羊内脏没什么,他大概也没有办法忍受千篇一律的菜单。一般来说,暮春时节牧民只吃两样东西:羊肉和茶。你可以先来一块煮羊肉,再来一碗油腻腻的『奶』茶;也可以先来一碗『奶』茶,再吃一块羊肉。有一次早餐,我有意外的惊喜,丹比多尔扎竟把一个羊头往火堆里一掼,我想,这次可有烤羊头当早餐了。别高兴得太早,他只是想把羊『毛』烧掉而已。稍后,他用树枝把这颗焦黑的羊头从火堆里夹了出来,用刀剔出羊头上的碎肉和脑髓,往微温的茶里
![今夜有鬼----续2 寻找阴间 ([今夜有鬼系列ⅱ]第二部) by 黯然销混蛋封面](http://www.38xs.net/cover/noimg.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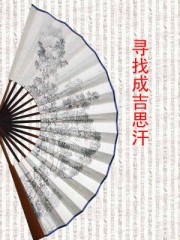
![[剑网三]寻找帮主夫人大作战封面](http://www.38xs.net/cover/8/854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