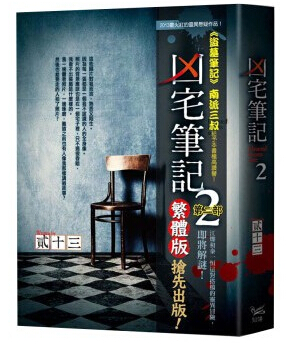情爱笔记-第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很想跟你一道出去旅行一次。”他信口说道,过了一会儿,他觉得睡意渐渐要把他压倒了。“到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去,完全是异国情调的。那里谁也不认识咱俩,咱们也不认识任何人。比如,去爱尔兰。也许,年底就动身。我可以用一个星期或者十天。你愿意吗?”
“我更愿意去维也纳。”她说,舌头不大灵活,是不是睡意袭来了?是不是做爱之后总是让她感到慵懒?“去看埃贡·希勒的作品,去参观他工作过的地方。这几个月来,我整天听人说起他的生平和绘画。结果,惹起了我的好奇心。阿尔丰索对这个画家的神魂颠倒,你不感到惊讶吗?据我所知,你一直就不大喜欢埃贡·希勒。那阿尔丰索的迷恋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耸耸肩膀。这孩子从什么地方染上这个爱好的,他连一点印象也没有。
“好吧。那咱们十二月去维也纳。”他说。“去看希勒的绘画,去听莫扎特的音乐。的确,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希勒的作品;但是,可能现在开始让我喜欢了。如果你喜欢,我也会喜欢的。我不知道阿尔丰索这股热情是从哪里产生的。你睡着了吗?我不会放开你的,跟你再说一句:晚安,亲爱的。”
她嘟嚷一声:“晚安。”她翻过身去,把脊背贴在丈夫的胸膛上。他早已经侧过身来,弯曲了双腿,让她好像坐在他膝盖上一样睡在怀里。分居前的十年里,二人一直是这样睡觉的。
从前天起,他和她又恢复了这个姿势。堂利戈贝托一只手越过卢克莱西娅的肩头,摸着她的乳房;另一只手抚摸着她的细腰。
附近的猫们已经停止战斗或者性交。马达们的轰鸣或者嚎叫消失了好大一阵工夫。由于这个与自己身体紧密相连的可爱形体所产生的温暖和越来越温暖,堂利戈贝托有这样的感觉:在一片静静的浅水中,在一股亲切的惯性推动下,他在飘浮,在滑动;或许是在星星的空间里,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向那些寒冷的星星奔去。这样心灵充实、和谐平静、与生命共振的感觉能够持续多少天?能够持续多少小时而不被打乱呢?好像回答他这个心中默默的发问似的,他听到卢克莱西娅太太这样在问:“利戈贝托,你一共收到我多少封匿名信?”
“十封。”利戈贝托回答说,身体猛烈一颤。“我还以为你已经睡着了呢。你问这个干什么?”
“因为我也收到了你十封匿名信。”她回答说,身于一动也不动。“我猜想这叫做爱好对称。”
这时,身体变得僵硬的是他了。
“你收到我写的十封匿名信?可我从来也没有给你写信啊!连一封也没写过!无论匿名的还是签名的都没有写过。”
“我早就知道了。”她说道,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不知道实情的就是你了。你是一无所知啊!你还不明白吗?我也没有给你寄过匿名信。一封也没有!但是,我敢打赌,唯一的一封真信,肯定没有到你手中!”
时间过去了两秒、三秒、五秒,二人既不说话,也不动作。虽然可以听到大海的涛声,可是堂利戈贝托却觉得夜空里弥漫着公猫发怒的尖叫和母猫发情的干嚎。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终于,他低声问道,尽管他很清楚卢克莱西娅是非常严肃地说出这番话的。
她没有回答。她如同他不久前那样地平静和保持沉默。那令人端不气来的幸福是多么地短暂啊!利戈贝托,真实的生活又回来了,它艰难又严酷!
最后,他建议:“要是你没了睡意,现在我也不困了,与其像有人那样用数羊群的方法入睡,还不如咱俩把事情弄个明白呢。干脆,现在就说。当然这要听你的,如果你乐意的话。
因为假如你宁可忘掉它,那咱们就忘掉它!今后永远也不再说这些匿名信的事情了。“
“利戈贝托,你很清楚:咱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些匿名信的。”妻子肯定地说道,口气里露出倦意。“你和我都很明白无论如何得办的事情早晚要办,那干脆现在就办!”
“那么,好吧!”说着,他坐了起来。“看看那些信吧!”
天气变凉了。二人走进书房之前,穿上了晨衣。卢克莱西娅太太带上装有热柠檬汁的保温瓶,给丈夫治疗所谓的感冒。互相拿出那些信之前,他和她又用同一个林子喝了几口热柠檬汁。堂利戈贝托把那些匿名信都收藏在最后那本笔记中了,空白的纸上还没有写上注释和补遗;卢克莱西娅则把信放在一个手包里,用一条深紫色的绸带捆在一起。二人看出信封都是一样的,信纸也相同;这种信封和信纸在中国人开的杂货铺里用四个雷阿尔就可以买到。
但是,字体是不同的。当然,卢克莱西娅太太那封信,唯一的真信,是不包括在其中的。
“这是我的字体。”堂利戈贝托低声说,一面克制着自以为可以克制的惊讶程度,结果还是惊讶不已。他非常仔细地查看了第一封信,几乎不理睬内容,而是仅仅集中研究书法。
“好啊,实际上,我的字体是最一般化的了。谁都能模仿。”
“尤其是一个爱好绘画的少年,一个小艺术家。”卢克莱西娅太太下结论说,一面挥动着那些所谓由她写的匿名信,她刚刚翻阅了一遍。“这封信却相反,是唯一我写给你的信,他没有交给你,因为他不想让你拿这封信同其它的信做比较,免得发现这个骗局。”
“这字体有点像你的。”堂利戈贝托纠正她的看法;他早就拿着放大镜在仔细研究了,好像集邮专家看珍稀邮票一样。“总之,是一种圆体字,很像绘画。是那种在修文学校、可能是索福亚农式的学校里读书的女子的字体。”
“以前你不认识我的字体吗?”
“不,不认识。”他承认道。在这个连连让他大吃一惊的夜晚里,这是第三次惊讶了。“现在我才发现不认识你的字体。根据我的记忆,你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信。”
“这些信也不是我写给你的。”
接下来,在多半个小时里,二人都一言木发,默默地阅读着各自的信,或者更确切地说,阅读着自己不了解的那另外一半的匿名信。他和她紧挨着坐在大皮沙发上,背后有靠垫,旁边有一台立式高脚台灯,玻璃灯罩上画着一群澳大利亚土著部落的人像。巨大的圆光把俩人都笼罩在光环里。他俩不时地喝一口温热的柠檬汁。还不时地地或者她发出一声嘻笑,而另外一个并不扭头问问“你笑什么?”因为他或者她不断地由于惊异、愤怒,或者出于一时感情脆弱、柔情、宽容、惆怅而变换着表情。俩人不时地侧视一下对方,感到疲惫不堪、困惑不已、犹豫不决。从哪里开始呢?
“他钻到这里来了。”利戈贝托终于说道,一面指书房,指指书柜。“他翻腾过我的东西,也看过我写的文字。这些笔记中最神圣、最秘密的内容,他都看到了。甚至连你不了解的东西,他都知道了。那些所谓我给你的信,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我的,虽然不是我亲笔写的。因为我敢肯定:信中所有的句子都是他从我的笔记中抄录的。他做了一个俄式冷盘,把思想体系、引言语录、笑话、游戏、自己和他人的思考都混杂在一起了。”
“所以那些游戏、那些命令,我觉得像是你的。”卢克莱西娅太太说道。“相反地,这些信,我不明白怎么会让你觉得像是我写的呢?”
“我那时急得发疯,很想知道你的情况,很想得到你发来的信号。”利戈贝托辩白道。“落水的人会抓住任何眼前的东西,不管是不是让人恶心。”
“可是那咬文嚼字的风格呢?那附庸风雅的文字呢?不是更像科林·德亚多的东西吗?”
“有些文字像是科林·德亚多的。”堂利戈贝托说道,同时在回忆,在联想。“几个星期以前,科林·德亚多的小说开始出现在家里。那时我还以为是女佣或者厨娘的呢。现在我知道这些书是谁买的、又是做什么用的了。”
“这个坏小于!我要宰了他!”卢克莱西娅太太叫起来。“居然拿出科林·德亚多来!我发誓要宰了他!”
“你还在笑?”他吃惊地问道。“你觉得有趣,是不是?咱们应该祝贺他?应该奖励他?”
这时,她真的笑了,时间很长,比前一次更爽朗。
“说真的,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利戈贝托。肯定这没有什么好笑的。那难道应该哭鼻子?
应该生气?好吧,如果应该生气,那就生气吧!那明天你就跟他生气?大吵一通?狠狠惩罚他?‘“堂利戈贝托耸耸肩膀。他也很想大笑一阵。可他觉得自己很愚蠢。
“我从来没有惩罚过他,更没有打过他,所以不知道拿他怎么办才好。”他坦白地说,有些不好意思。“因此只好听之任之。说实在的,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他。我猜测无论他干什么,总是他胜利。”
“好啦,既然如此,这一次咱们也有得分的地方。”卢克莱西娅太太依偎在丈夫怀中后为他已经搂住了她的肩膀。“咱们这不是和好了吗?如果事先没有这些匿名信,你绝对不敢给我打电话请我去白房子喝茶。对不对?没有这些匿名信,我也不会去赴约。肯定不会的。
这些信铺平了道路。咱们不能抱怨,因为他帮助了咱俩,让咱俩和好了。因为咱俩和好了,你是不后悔的,对吧?利戈贝托。“
他最后也笑了起来。他用大鼻子摩擦妻子的脑袋,感到她的头发弄得眼睛痒痒。
“不后悔。永远也不会后悔!”他说。“好啦,经过这么多激动的事情以后,咱们终于赢得了可以做好梦的权利了。这一切都棒极了!可是,夫人,明天我还得去办公室啊!”
两个人手拉着手回到了黑暗的卧室中。她又大着胆子开了这样一个玩笑:“十二月咱们带阿尔丰索一起去维也纳吧?”
这真的是玩笑吗?堂利戈贝托立即排除了这个坏思想,然后高声宣布:“不管怎么说,咱们组成了一个幸福家庭!是不是?卢克莱西娅。”
1996年10月19日于伦敦
附录:情爱的诱惑
—关于《情爱笔记》的采访录
1997年春,巴尔加斯·略萨发表了他的新作《情爱笔记》,立刻引起轰动,在西班牙和伊比利亚美洲成为最畅销书之一。西班牙《阅读指南》杂志记者埃尔维拉·韦尔维斯就这部被称之为《继母领》续篇的又一部艳情小说采访了巴尔加斯·略萨;请作者本人来评论一下这部作品,下面便是他们的谈访录。
埃尔维拉·韦尔维斯(以下简称埃):有人断言《情爱笔记》是您的最后一部艳情小说。
巴尔加斯·略萨(以下简称已):“最后”这个词我从来不用。我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最后的,特别是在文学上。写这部作品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愉悦。我写得很高兴,这种情况对我是少有的,因为写小说总是令我充满激情,我在构思和写作时精神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可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差事。相反,这次我真的写得心旷神信,因为我觉得书中的幽默风趣跟情爱占据着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是说,《情爱笔记》绝不仅仅是一部艳情小说,尽管情爱的描写是作品重要的组成部分。
埃:当然,从正面意义上讲这部小说也是有分量的。您是不是想把这部作品写成您的另一部作品——《继母颂》的续篇?
巴:《继母颂》开头是计划两个人合作写的,另一个人是我的画家朋友,名叫费尔南多·德西斯罗。但是,这个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尽管我们作了最大的努力,还是难以在一起工作,我们两个人都感到有点别扭,不舒服,结果最后放弃了这个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打算要写一部以绘画和其它艺术形式为基本内容的小说了。
埃:在您所有的创作中,性罪错的描述都占重要成分,这部作品也是如此。也许您认为《情爱笔记》中性罪错的描写是最立竿见影,换言之,是最大胆直露而不可辩驳的吧?
巴:除非在最原始的社会,人类的性生活并不仅仅表现在兽欲上。在原始社会之后,当社会开始丰富它的知识,完善它的组织机构、它的神话和它的文化的时候,性爱便逐渐地不再仅仅局限于肉体活动,而是增添了一系列的其他成分;在这些成分中,有各式各样的体验,文化乃其一。这正是《情爱笔记》所要表现的:肉体的爱,亦即情爱是基础,尔后由于文化领域中的各种礼仪,虚构和幻想,这中间包括文学和艺术,爱情便扩大到了一个不同的范畴。而《情爱笔记》主要是利用文学和艺术这两个手段使主人翁堂利戈贝托建造起他幻想和虚构的爱巢。奥地利表现主义回家希勒和一维也纳分离派“画家克里木特、智利诗人聂鲁达、法国画家居斯塔夫·库尔贝和英国诗人济慈不都是塑造了此类形象吗?
埃:大概会有人怀疑,您在书中的描写会不会是为不满50岁的入开脱,因为您知道,现在谈到性似乎已不那么重要了,原因是在生活中已有其它一些吸引入的事,如金钱、度假、权利等等。
巴(抗议地):可是我认为性是重要的!性是重要至极的!问题是在看到性的重要性的同时,如果性脱离了所有那些装饰,所有那些神话和所有那些礼仪,它便成了纯粹的动物交媾,就是说,是最原始的形式,最快的形式,在性交的时候没有多少愉悦,不是这样吗?如果是简单的动物性交,欢愉就可怜至极了,不是吗?
埃:我们面前摆着的是一部艳情小说,它写得很美,很有趣,但是,它不是一部消遣性的小说。您认为艳情小说和消遣性小说的区别何在?
巴:我很高兴您告诉我在您看来《情爱笔记》不是消遣文学,因为我认为它的确不是。恰恰相反,出现在堂利戈贝托生活中的书籍、约会、音乐、图画和思想,不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智力和情感游戏,而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理性展示,就是说,那正如一池池泉水,让他的生命在里边洗涤,因为正是这样,他抵御着不幸,缓解着他身体和灵魂上的种种欲望。作为一家保险公司里的职员,他的生活是平庸、单调而乏味的,根本没有可能使他的那些欲望得到满足。这就意味着,对堂利戈贝托来说,艺术和文化是人性体验和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像食物和呼吸的空气一样所需要的东西。
埃:堂利戈贝托不想伤害任何人,也不想排斥任何人,但是,应该看到,一个人力争独立自主的企图是势所必然地要伤害人和排斥人的。
巴:对,这种要求独立自主的特性……我认为一个人是要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的。这本书,如果我们要认真读一下的话,它是竭力保护个人的,是保护群体对个人自主性的威胁的,是遏制部落对个人的凝聚的。堂利戈贝托就是不懈地与这种巨大危险作斗争,小说自然也想对这种危险予以揭露。
埃:在您的其它作品中,您更关心的是集体道德和政治品德,而在这部小说中,您更关心的却是私人道德的培养和陶冶。举例说,我认为问您的《酒吧长谈》和1962年获简明丛书奖的《城市与狗》相比都是这样,您似乎对公共的事业——特别是令您大伤脑筋的政治冒险——感到厌倦了,有点支持不住了。
埃:对,这话一点不错。这部小说写的是私人氛围,重要的事件不是发生在大街上,不是发生在社会机构中,也不是发生在任何公共场所,而是发生在一个家庭内部。家庭这个组织目前正遭受着激烈的批评和反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