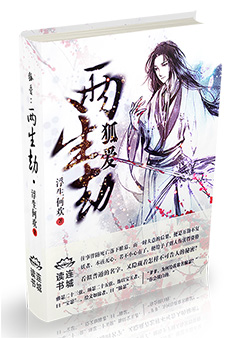我的前半生-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三 母子之间
三 母子之间
我入宫过继给同治和光绪为子,同治和光绪的妻子都成了我的母亲。我继承同治兼祧光绪,按说正统是在同治这边,但是光绪的皇后——隆裕太后不管这一套。她使用太后权威,把敢于和她争论这个问题的同治的瑜、珣、瑨三妃,打入了冷宫,根本不把她们算做我的母亲之数。光绪的瑾妃也得不到庶母的待遇。遇到一家人同座吃饭的时候,隆裕和我都坐着,她却要站着。直到隆裕去世那天,同治的三个妃和瑾妃联合起来找王公们说理,这才给她们明确了太妃的身份。从那天起,我才管她们一律叫“皇额娘”。
我虽然有过这么多的母亲,但并没有得过真正的母爱。今天回想起来,她们对我表现出的最大关怀,也就是前面说过的每餐送菜和听太监们汇报我“进得香”之类。
事实上我小时候并不能“进得香”。我从小就有胃病,得病的原因也许正和“母爱”有关。我六岁时有一次栗子吃多了,撑着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隆裕太后只许我吃糊米粥,尽管我天天嚷肚子饿,也没有人管。我记得有一天游中南海,太后叫人拿来干馒头,让我喂鱼玩。我一时情不自禁,就把馒头塞到自己嘴里去了。我这副饿相不但没有让隆裕悔悟过来,反而让她布置了更严厉的戒备。他们越戒备,便越刺激了我抢吃抢喝的欲望。有一天,各王府给太后送来贡品'注',停在西长街,被我看见了。我凭着一种本能,直奔其中的一个食盒,打开盖子一看,食盒里是满满的酱肘子,我抓起一只就咬。跟随的太监大惊失色,连忙来抢。我虽然拼命抵抗,终于因为人小力弱,好香的一只肘子,刚到嘴又被抢跑了。
我恢复了正常饮食之后,也常免不了受罪。有一次我一连吃了六个春饼,被一个领班太监知道了。他怕我被春饼撑着,竟异想天开地发明了一个消食的办法,叫两个太监左右提起我的双臂,像砸夯似的在砖地上蹾了我一阵。过后他们很满意,说是我没叫春饼撑着,都亏那个治疗方法。
这或许被人认为是不通情理的事情,不过还有比这更不通情理的哩。我在八九岁以前,每逢心情急躁,发脾气折磨人的时候,我的总管太监张谦和或者阮进寿就会做出这样的诊断和治疗:“万岁爷心里有火,唱一唱败败火吧。”说着,就把我推进一间小屋里——多数是毓庆宫里面的那间放“毛凳儿”的屋子,然后倒插上门。我被单独禁闭在里面,无论怎么叫骂,踢门,央求,哭喊,也没有人理我,直到我哭喊够了,用他们的话说是“唱”完了,“败了火”,才把我释放出来。这种奇怪的诊疗,并不是太监们的擅自专断,也不是隆裕太后的个人发明,而是皇族家庭的一种传统,我的弟弟妹妹们在王府里,都受过这样的待遇。
隆裕太后在我八岁时去世。我对她的“慈爱”只能记得起以上这些。
和我相处较久的是四位太妃。我和四位太妃平常很少见面。坐在一起谈谈,像普通人家那样亲热一会,根本没有过。每天早晨,我要到每位太妃面前请安。每到一处,太监给我放下黄缎子跪垫,我跪了一下,然后站在一边,等着太妃那几句例行公事的话。这时候太妃正让太监梳着头,一边梳着一边问着:“皇帝歇得好?”“天冷了,要多穿衣服。”“书念到哪儿啦?”全是千篇一律的枯燥话,有时给我一些泥人之类的玩意儿,最后都少不了一句:“皇帝玩去吧!”一天的会面就此结束,这一天就再也不见面了。
太后太妃都叫我皇帝,我的本生父母和祖母也这样称呼我。其他人都叫我皇上。虽然我也有名字,也有乳名,不管是哪位母亲也没有叫过。我听人说过,每个人一想起自己的乳名,便会联想起幼年和母爱来。我就没有这种联想。有人告诉我,他离家出外求学时,每逢生病,就怀念母亲,想起幼年病中在母亲怀里受到的爱抚。我在成年以后生病倒是常事,也想起过幼年每逢生病必有太妃的探望,却丝毫引不起我任何怀念之情。
我在幼时,一到冷天,经常伤风感冒。这时候,太妃们便分批出现了。每一位来了都是那几句话:“皇帝好些了?出汗没有?”不过两三分钟,就走了。印象比较深的,倒是那一群跟随来的太监,每次必挤满了我的小卧室。在这几分钟之内,一出一进必使屋里的气流发生一次变化。这位太妃刚走,第二位就来了,又是挤满一屋子。一天之内就四进四出,气流变化四次。好在我的病总是第二天见好,卧室里也就风平浪静。
我每次生病,都由永和宫的药房煎药。永和宫是端康太妃住的地方,她的药房比其他太妃宫里的药房设备都好,是继承了隆裕太后的。端康太妃对我的管束也比较多,俨然代替了隆裕原先的地位。这种不符清室先例的现象,是出于袁世凯的干预。隆裕去世后,袁世凯向清室内务府提出,应该给同、光的四妃加以晋封和尊号,并且表示承认瑾妃列四妃之首。袁世凯为什么管这种闲事,我不知道。有人说这是由于瑾妃娘家兄弟志钅奇的活动,也不知确否。我只知我父亲载沣和其他王公们都接受了这种干预,给瑜、珣皇贵妃上了尊号(敬懿、庄和)瑨、瑾二贵妃也晋封为皇贵妃(尊号为荣惠、端康);端康成了我的首席母亲,从此,她对我越管越严,直到发生了一次大冲突为止。
我在四位母亲的那种“关怀”下长到十三四岁,也像别的孩子那样,很喜欢新鲜玩意。有些太监为了讨我高兴,不时从外面买些有趣的东西给我。有一次,一个太监给我制了一套民国将领穿的大礼服,帽子上还有个像白鸡毛掸子似的翎子,另外还有军刀和皮带。我穿戴起来,洋洋得意。谁知叫端康知道了,她大为震怒,经过一阵检查,知道我还穿了太监从外面买来的洋袜子,认为这都是不得了的事,立刻把买军服和洋袜子给我的太监李长安、李延年二人叫到永和宫,每人责打了二百大板,发落到打扫处去充当苦役。发落完了太监,又把我叫了去,对我大加训斥:“大清皇帝穿民国的衣裳,还穿洋袜子,这还像话吗?”我不得已,收拾起了心爱的军服、洋刀,脱下洋袜,换上裤褂和绣着龙纹的布袜。
如果端康对我的管教仅限于军服和洋袜子,我并不一定会有后来的不敬行为。因为这类的管教,只能让我更觉得自己与常人不同,更能和毓庆宫的教育合上拍。我相信她让太监挨一顿板子和对我的训斥,正是出于这个教育目的。但这位一心一意想模仿慈禧太后的瑾妃,虽然她的亲姐姐珍妃死于慈禧之手,慈禧仍然被她看做榜样。她不仅学会了毒打太监,还学了派太监监视皇帝的办法。她发落了我身边的李长安、李延年这些人之后,又把她身边的太监派到我的养心殿来伺候我。这个太监每天要到她那里报告我的一举一动,就和西太后对待光绪一样。不管她是什么目的,这大大伤害了皇帝的自尊心。我的老师陈宝琛为此忿忿不平,对我讲了一套嫡庶之分的理论,更加激起了我憋在心里的怒气。
过了不久,大医院里一个叫范一梅的大夫被端康辞退,便成了爆发的导火线。范大夫是给端康治病的大夫之一,这事本与我不相干,可是这时我耳边又出现了不少鼓动性的议论。陈老师说:“身为太妃,专擅未免过甚。”总管太监张谦和本来是买军服和洋袜子的告发人,这时也变成了“帝党”,发出同样的不平之论:“万岁爷这不又成了光绪了吗?再说大医院的事,也要万岁爷说了算哪!连奴才也看不过去。”听了这些话,我的激动立刻升到顶点,气冲冲地跑到永和宫,一见端康就嚷道:
“你凭什么辞掉范一梅?你太专擅了!我是不是皇帝?谁说了话算数?真是专擅已极!……”
我大嚷了一通,不顾气得脸色发白的端康说什么,一甩袖子跑了出来。回到毓庆宫,师傅们都把我夸了一阵。
气急败坏的端康太妃没有找我,却叫人把我的父亲和别的几位王公找了去,向他们大哭大叫,叫他们给拿主意。这些王公们谁也没敢出主意。我听到了这消息,便把他们叫到上书房'注'里,慷慨激昂地说:
“她是什么人?不过是个妃。本朝历代从来没有皇帝管妃叫额娘的!嫡庶之分要不要?如果不要,怎么溥杰不管王爷的侧福晋叫一声呢?凭什么我就得叫她,还要听她的呢?……”
这几位王公听我嚷了一阵,仍然是什么话也没说。
敬懿太妃是跟端康不和的。这时她特意来告诉我:“听说永和宫要请太太、奶奶'注'来,皇帝可要留神!”
果然,我的祖母和母亲都被端康叫去了。她对王公们没办法,对我祖母和母亲一阵叫嚷可发生了作用,特别是祖母吓得厉害,最后和我母亲一齐跪下来恳求她息怒,答应了劝我赔不是。我到了永和宫配殿里见到了祖母和母亲,听到正殿里端康还在叫嚷,我本来还要去吵,可是禁不住祖母和母亲流着泪苦苦哀劝,结果软了下来,答应了她们,去向端康赔了不是。
这个不是赔得我很堵心。我走到端康面前,看也没看她一眼,请了个安,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皇额娘,我错了”,就又出来了。端康有了面子,停止了哭喊。过了两天,我便听到了母亲自杀的消息。
据说,我母亲从小没受别人申斥过一句。她的个性极强,受不了这个刺激。她从宫里回去,就吞了鸦片烟。后来端康担心我对她追究,从此便对我一变过去态度,不但不再加以管束,而且变得十分随和。于是紫禁城里的家庭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我和太妃们之间也恢复了母子关系。然而,却牺牲了我的亲生母亲。
四 毓庆宫读书
四 毓庆宫读书
我六岁那年,隆裕太后为我选好了教书的师傅,钦天监为我选好了开学的吉日良辰。宣统三年旧历七月十八日辰刻,我开始读书了。
读书的书房先是在中南海瀛合补桐书屋,后来移到紫禁城斋宫右侧的毓庆宫——这是光绪小时念书的地方,再早,则是乾隆的皇子颙琰(即后来的嘉庆皇帝)的寝宫。毓庆宫的院子很小,房子也不大,是一座工字形的宫殿,紧紧地夹在两排又矮又小的配房之间。里面隔成许多小房间,只有西边较大的两敞间用做书房,其余的都空着。
这两间书房,和宫里其他的屋子比起来,布置得较简单:南窗下是一张长条几,上面陈设着帽筒、花瓶之类的东西;靠西墙是一溜炕。起初念书就是在炕上,炕桌就是书桌,后来移到地上,八仙桌代替了炕桌。靠北板壁摆着两张桌子,是放书籍文具的地方;靠东板壁是一溜椅子、茶几。东西两壁上挂着醇贤亲王亲笔给光绪写的诚勉诗条屏。比较醒目的是北板壁上有个大钟,盘面的直径约有二米,指针比我的胳臂还长,钟的机件在板壁后面,上发条的时候,要到壁后摇动一个像汽车摇把似的东西。这个奇怪的庞然大物是哪里来的,为什么要安装在这里,我都不记得了,甚至它走动起来是什么声音,报时的时候有多大响声,我也没有印象了。
尽管毓庆宫的时钟大得惊人,毓庆宫的人却是最没有时间观念的。看看我读的什么书,就可以知道。我读的主要课本是十三经,另外加上辅助教材《大学衍义》、《朱子家训》、《庭训格言》、《圣谕广训》、《御批通鉴辑览》、《圣武记》、《大清开国方略》等等。十四岁起又添了英文课,除了《英语读本》,我只念了两本书,一本是《爱丽思漫游奇境记》,另一本是译成英文的中国《四书》。满文也是基本课,但是连字母也没学会,就随老师伊克坦的去世而结束。总之,我从宣统三年学到民国十一年,没学过加减乘除,更不知声光化电。关于自己的祖国,从书上只看到“同光中兴”,关于外国,我只随着爱丽思游了一次奇境。什么华盛顿、拿破仑,瓦特发明蒸气机,牛顿看见苹果落地,全不知道。关于宇宙,也超不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如果不是老师愿意在课本之外谈点闲话,自己有了阅读能力之后看了些闲书,我不会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位置,也不会知道大米原来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当谈到历史,他们谁也不肯揭穿长白山仙女的神话,谈到经济,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一斤大米要几文钱。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总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库伦吃了一颗红果生育出来的,我一直以为每个老百姓吃饭时都会有一桌子菜肴。
我读的古书不少,时间不短,按理说对古文总该有一定的造诣,其实不然。首先,我念书极不用功。除了经常生些小病借题不去以外,实在没题目又不高兴去念书,就叫太监传谕老师,放假一天。在十来岁以前,我对毓庆宫的书本,并不如对毓庆宫外面那棵桧柏树的兴趣高。在毓庆宫东跨院里,有棵桧柏树,夏天那上面总有蚂蚁,成天上上下下,忙个不停。我对它们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时常蹲在那里观察它们的生活,用点心渣子喂它们,帮助它们搬运食品,自己倒忘了吃饭。后来我又对蛐蛐、蚯蚓发生了兴趣,叫人搬来大批的古瓷盆缸喂养。在屋里念书,兴趣就没这么大了,念到最枯燥无味的时候,只想跑出来看看我这些朋友们。
十几岁以后,我逐渐懂得了读书和自己的关系:怎么做一个“好皇帝”,以及一个皇帝之所以为皇帝,都有什么天经地义,我有了兴趣。这兴趣只在“道”而不在“文”。这种“道”,大多是皇帝的权利,很少是皇帝的义务。虽然圣贤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之类的话,但更多的话却是为臣工百姓说的,如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在第一本教科书《孝经》里,就规定下了“始于事亲,终于事君”的道理。这些顺耳的道理,开讲之前,我是从师傅课外闲谈里听到的,开讲以后,也是师傅讲的比书上的多。所以真正的古文倒不如师傅的古话给我的印象更深。
许多旧学塾出身的人都背过书,据说这件苦事,确实给了他们好处。这种好处我却没享受到。师傅从来没叫我背过书,只是在书房里念几遍而已。
也许他们也考虑到念书是应该记住的,所以规定了两条办法:一条是我到太后面前请安的时候,要在太后面前把书从头念一遍给她听;另一条是我每天早晨起床后,由总管太监站在我的卧室外面,大声地把我昨天学的功课念几遍给我听。至于我能记住多少,我想记不想记,就没有人管了。
老师们对我的功课,从来不检查。出题作文的事,从来没有过。我记得作过几次对子,写过一两首律诗,做完了,老师也不加评语,更谈不上修改。其实,我在少年时代是挺喜欢写写东西的,不过既然老师不重视这玩艺,我只好私下里写,给自己欣赏。我在十三四岁以后,看的闲书不少,像明清以来的笔记、野史,清末民初出版的历史演义、剑仙快客、公案小说,以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等等,我很少没看过的。再大一点以后,我又读了一些英文故事。我曾仿照这些中外古今作品,按照自己的幻想,编造了不少“传奇”,并且自制插图,自编自看。我还化名向报刊投过稿,大都遭到了失败。我记得有一次用“邓炯麟”的化
![[转世·重生] 重生娱乐之巨星降临 作者:绝不斯文(起点中文网vip2014-09-17完结)封面](http://www.38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