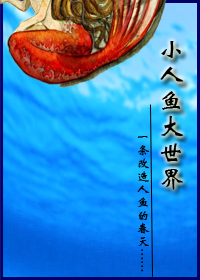世界历史名人丛书:西蒙娜 德 波伏瓦-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到了校方和学生家长的反对,人们接受不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新思想,校方甚至向她提出了严重警告。但波伏瓦面对校方的强硬态度,也不甘示弱,她决不退让。校方见她固执己见,也只好对此事不了了之了。
在蒙格朗中学,人们对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指责还不仅于此。人们不仅对她在课堂上否定传统道德,宣扬自由主义思想的做法表示了不满,而且也极看不惯这位喜欢标新立异的女教师那无拘无束、不顾平时生活细节方面的言行。西蒙娜平时在蒙格朗中学喜欢独来独往,且从不结交他人。她总是独自一人去看电影、去咖啡馆、去食堂。在周围人看来,她总是显得有些特别,总是处处与众不同。每逢节假日,她总是单独消遣。她常常在星期四或星期天穿上旧裙子,背上布提包,徒步出门旅行。这种旅行使她一次比一次走得更远。她计划走遍当地的每一个角落。她常常独自一人翻山越岭、爬山涉水,在野外宿营。有时她还拦过路的汽车,搭乘司机们的便车旅行。在旅行中,她也常常遇到不测的险境,但她对此并不畏惧。
对于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远足,周围的人们议论纷纷。许多善意的人提醒她需小心,以免发生意外。而恶意的人则借此散布她的谣言,乘机对她的行为加以渲染,到处说三道四。
随着时间的流逝,西蒙娜·德·波伏瓦在蒙格朗中学执教已逾一年。一年来,她从不顾及他人对她的看法,而只求自由自在,用我行我素的方式去面对一切。然而时间一长,人们对她的行为举止居然也见怪不怪了。而波伏瓦的发式、装束、爱打网球的嗜好,以及幽居独处、清高洒脱也渐渐都成了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慢慢地,人们开始以一种新奇的目光注视她,欣赏她。蒙格朗中学的学生们也开始学着模仿她的一举一动。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蒙格朗中学执教的一年期间,她时常在假期去和萨特会面。而且他们也一直书信频频,仍保持着精神上的默契融洽。萨特在此期间,正在写一篇“偶然『性』”的论文,这篇论文是他后来的著名小说《恶心》的初稿。而西蒙娜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尝试写小说。她从事写作主要是为了在幽居独处中同自己对话,另外也把自己对生活的体验通过文字表达出来。
1932年9月,西蒙娜·德·波伏瓦离开了马赛的蒙格朗中学。她欣然北上,前往法国东北部的卢昂城去接受一个新近谋到的教师职位。卢昂城与萨特所在的勒阿弗尔市毗邻。从勒阿弗尔到卢昂乘火车只需一个小时。这样,西蒙娜和萨特就可以经常相聚。而且从卢昂至巴黎的交通也很便利。西蒙娜对自己这次的选择十分满意。
西蒙娜·德·波伏瓦这次执教的学校是卢昂的贞德中学。这是法国的一所名牌学校。从1932年至1936年,波伏瓦一直在这所中学教书。初来学校后,西蒙娜一改其在马赛蒙格朗中学时的那种我行我素的生活方式,这次她不再独往独来,不再把自己封闭在狭窄的单人居室里。来到贞德学校,她对女教师科莱特·奥德丽组织的一个先锋派小团体挺感兴趣,于是就努力接近这个团体,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在此期间,她还与巴黎的先锋派导演夏尔·迪兰建立了联系。此外她还接触了一些在卢昂从事革命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
随着这种开放式生活的继续,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交往范围也越来越大,她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个活跃人物。其中应特别提到的是,一些在法国避难的德国『共产』党员也经常参加他们的聚会,与他们探讨改造社会的政治问题。与这些激进分子的交往,使西蒙娜·德·波伏瓦上了中学校方的黑名单。校方对西蒙娜参加政治活动表示了极端的恼怒。此外校方还指责波伏瓦在讲课时宣传自己的主张,即女『性』要争取自由、平等的权利,拒绝社会强加给女『性』的义务。正是她的一系列主张,激起了校方的极大愤慨,使得校方命令西蒙娜和其他教师,必须对学生进行鼓励生育的宣传。然而西蒙娜对校方的指责不仅给予极端蔑视的态度,而且还公然违抗其郑重的命令。她首先对校方的旨意尽情地嘲讽了一番,继而进一步向学生宣称,女人并非是生儿育女的工具。她甚至建议女学生步自己的后尘,解放自己,寻找情人。因此,从表面上看,来到卢昂后,波伏瓦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态度,但在本质上,在她的精神世界里,蒙格朗中学讲台上的主张却始终动摇不了。结果,可想而知,在贞德中学,波伏瓦因思想激进再一次遭到了守旧派人士的攻击和诋毁。个别教师指责她根本不称职。
这期间,西蒙娜·德·波伏瓦对工作、对社会活动投入了全部的热情。她不再像在蒙格朗中学时那样,在周末和假日里单独外出,去徒步旅行,而是经常泡在保尔饭店的餐厅里写作。西蒙娜喜欢那里的清静,并曾在那儿完成了一部小说。她此时对现实生活的兴趣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即便在和萨特通信时,或与他聚会时,也常常喜欢探讨一些社会问题,表现出了对外界、对社会诸多方面问题的高度关注。西蒙娜时常和萨特一起探讨如何深入到人和社会生活的内部去分析和探索问题。他们常常搞些社会调研工作,经常专心阅读刊登社会杂闻的刊物,而且研究产生诸多方面社会问题的社会机制。波伏瓦甚至提出了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种种方案和设想。她对当权阶级表示不满,认为只有打倒他们才能改变社会。这一期间,她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密切交往也充分反映了她对政治和社会活动,对改造社会问题表现出了较大的兴趣和热情。
在卢昂中学执教期间,西蒙娜·德·波伏瓦发现自己所置身的这个社会处处对自己充满敌意。基于对社会的不满,她开始探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她认为这个社会充满了偏见和不公正,需要进行改造。但正如萨特向她指出的那样,她不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不是她所属的阶级的斗争方式。而知识分子唯有保持自由,才能免于被社会异化。在与萨特的反复探讨中,她不断地回味着这一思想,始终思考着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与社会对抗,并且渐渐地对知识分子这一特定的形象有了加深的理解。是的,最可贵的是自由,保持自己精神的自由和独立,只有这种精神的自由和独立,才能使他们超越一定的社会准则之上而不受其支配。而这不正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她本人所坚持的一贯作风吗?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超凡脱俗、我行我素,使她拒绝按照社会的意志,公众的舆论改变自己。而一旦她把这种个『性』带进了生活中,不仅引起了卢昂贞德中学同事们对她的非议和疏远,而且也引起了萨特对她的忧虑。一次,西蒙娜·德·波伏瓦穿着一双『露』出一个大洞的长袜与萨特去一家豪华饭店吃饭。萨特见她衣着随便、马虎,拒绝陪她前往。西蒙娜向萨特申辩道:别人的看法对他们没有丝毫的影响。然而萨特则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西蒙娜的所作所为已经使他受到了指责。但西蒙娜·德·波伏瓦仍然在生活中,骄傲地我行我素。
波伏瓦在卢昂贞德中学教书期间,萨特离开了勒阿弗尔去德国留学。波伏瓦自从与萨特相识以后,和萨特离多聚少。其间她既要忍受分离的痛苦,又要忍受萨特移情别恋『插』曲的烦恼。1934年萨特在柏林留学时又爱上了一个同事的妻子。波伏瓦闻知此事后,于1934年2月动身去柏林探望萨特。她的到来及时阻止了这场事件的发展。在柏林期间,波伏瓦和萨特对柏林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但此时,德国的纳粹主义势力日益猖獗,萨特和波伏瓦不得不中止在德国的逗留,提前返回了法国。
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萨特从德国归来后,继续在各自的中学执教。萨特归国后已不愿为中学教师的职位所束缚,他渴望自由,希望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哲学研究中。他正着手写哲学论文。而波伏瓦在这一期间,既要忙于教学、忙于写作,还要忙于辅导她的一位女学生奥尔加·高萨绮薇茨。
奥尔加是俄罗斯贵族的后裔,大革命时举家流亡法国,后落破于卢昂,故她不得不寄宿于贞德中学。这个美丽的金发少女多愁善感而又倔强易怒,不由引起波伏瓦对自己少女时代的共鸣。在发现她有学习哲学的素质后,波伏瓦决定培养她,后经其父母的同意,进而成为奥尔加的监护人。萨特在这期间常从勒阿弗尔来卢昂探望波伏瓦,因此也开始结识了奥尔加,他甚至与波伏瓦一起为奥尔加制订了学业计划,并一起承担了对奥尔加的学习辅导。然而此景不长,随着对奥尔加学业辅导的失败,萨特却对这个热情的少女产生了爱恋。在他不惜一切的『迷』狂般的进攻下,奥尔加与萨特走到了一起。于是西蒙娜、萨特、奥尔加,这一对监护人及其被监护人开始出演了一曲一家三人的三重奏生活,但这种生活到了1936年却无论如何维持不下去了。恰巧这时波伏瓦奉令调离开卢昂,前往巴黎的莫里哀中学任教。而萨特因不愿被派往里昂的中学,便在拉昂的一所中学找到了教师的职位。就这样,西蒙娜只身又回到了巴黎。
在巴黎的莫里哀中学,西蒙娜·德·波伏瓦继续任哲学教师,这是她任职中学教师的第五个年头了。这期间,她曾在法国两所名牌学校任过教。但在莫里哀中学,她仍难逃脱被学生们终日议论的命运。莫里哀中学是巴黎一所具有传统风格的学校,这里的学生已习惯了教师们审慎、稳重的传统形象,因而对这位28岁的,留着冠冕型新发式,而风度优雅的女教师感到惊奇。尤其当学生们听说,这位年轻的女教师与某个男教师同居而不结婚,只忙于写作而拒绝干家务、下厨房的消息时,他们就对她另眼看待了。但西蒙娜·德·波伏瓦在任何新的环境中是从不会在乎公众舆论的。她仍和在马赛、卢昂一样,毫不理睬这些流言蜚语。她在上课时,仍然一贯采用启发式、开放式的方法进行教学,她的教学内容常常超出教材的范围,课堂上,她喜欢旁征博引,喜欢给学生开出一些长长的必读书目。她的课尽管很高深,但却极大地开启了学生的智慧,她使学生了解了许多当代文学、当代哲学的思『潮』。
来到巴黎莫里哀中学执教后,西蒙娜·德·波伏瓦又回到了从前她所习惯的生活圈子里。她在盖得街的罗阿尔·布列塔民族馆租了个房间,过着独立的生活。她经常去蒙巴那斯剧院,观看先锋派戏剧。由于早年受父亲乔治的影响,多年来,她亦像当年的父亲一样,对戏剧非常热爱和着『迷』。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西蒙娜的妹妹海莱娜已经成为了先锋派画家。在妹妹的陪同下,她有机会经常出入先锋派画室。回到家乡后,西蒙娜终于找回了往日在蒙巴那斯做姑娘时的生活习惯。在巴黎,人们不像在外省那样,用一种异样的目光去看待她,在这里,波伏瓦又找到了她理想中的“自由”。
然而,这种自由的生活刚刚开始不久,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平静生活却又被搅『乱』了。奥尔加不顾父母的阻拦,乘火车来到巴黎与波伏瓦相聚。她渴望过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更渴望独立,为了自谋生路,她先在蒙巴那斯区卖茶水的舞厅里当招待员。波伏瓦试图劝说她谋求一个职业,但被她拒绝。此后波伏瓦再次鼓励她去听先锋派导演夏尔·迪尔的课。终于在波伏瓦的帮助下,奥尔加最后进入了夏尔·迪尔的剧院,成为了一名演员。
这一期间,由于社会生活的丰富,波伏瓦也十分忙碌。首先她每周要完成莫里哀中学16课时的教学任务,要定期出席先锋派导演夏尔·迪兰及其情人西蒙娜·约利韦的活动,观看他们剧院的排练。她要应酬与艺术家、名流朋友们的交往,要照顾奥尔加的生活。此外她还不愿放弃享受巴黎这个文化之都现代生活的机会,因此要用许多晚上光顾咖啡馆、剧院、电影院。但是,更重要的是,她还要挤出相当的时间,用于发奋写作上。1938年萨特因发表了《恶心》和《墙》两部作品而在法国名声大振。与此同时,西蒙娜也根据她与萨特、奥尔加三人的特殊经历,也着手写一部自传体小说《女客》。
1939年3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6月23日,法国与英国、土耳其签订了一项互助条约。9月法国宣布参战,部长会议颁布了总动员令。萨特必须参军,上前线。西蒙娜在送别了萨特之后,继续留在了巴黎。在战争空气最紧张的阶段,她仍常去蒙巴那斯车站旁的三剑客咖啡馆里写作。当战争的阴云笼罩着巴黎时,每个人心中都抹不去死亡的阴影。西蒙娜也常常思忖着自己的处境,但她仍能平静地一如既往地正视着现实。“现在我将置身于战争这种存在中,尽管它对我来说是凶多吉少。”在紧张的战争期间,西蒙娜表现出了从来未有过的镇定和勇敢。她一方面努力地重新寻求自己正常的生活,一方面借此特殊的环境深入地进行一些人生的思考。白天她写小说、教课、看朋友、到餐馆去吃晚饭、上咖啡馆、进酒吧、去电影院以及参加大家的各种活动。深夜回到那自己的一隅,则握笔沙沙,冷静地注视着和书写着这现实的一切。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西蒙娜·德·波伏瓦始终未离开塞纳河左岸的蒙巴那斯区,在那里工作着、忙碌着。她没有被战争所吓倒,没有受恐惧感所左右,而这本身就是对这场罪恶战争的最大蔑视。
战争期间,波伏瓦有时也设法弄到通行证,前往前线去看望萨特。他们继续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尽管战火连绵,他们仍设法频繁通信,甚至在信中继续讨论着他们共同的写作计划。1940年6月,法国军队自认为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被德军出忽意料地攻破了。萨特与马其诺防线的守军一起进了德军的战俘营。波伏瓦得知此讯后,万分焦急。但后从萨特的来信中,得知萨特也和自己一样,虽然被战争中所发生的意外事件所左右,但从未丧失对未来的信念。他在集中营中,仍在撰写着哲学论著《存在与虚无》和小说《自由之路》。西蒙娜受萨特顽强的生存意志的鼓励,更加忘我地工作。她每天早晚必坐在多姆咖啡馆里进行写作。1941年3月,萨特因视力欠佳和借口文职人员而获释返回巴黎,回巴黎后,继续在巴斯德中学任教。这次战争使萨特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在战争前,萨特是个个人主义者,他认为他自己并不与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系。而二战的经历使萨特突然明白了自己仍是一个社会的动物,因此必须干预生活。前线的经历,使萨特对当时巴黎城中弥漫的妥协气氛极度不满,于是他开始与巴黎的抵抗运动组织取得联系。西蒙娜在萨特的影响下,也参加了抵抗运动组织。她积极协助萨特与“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取得联系。萨特在这一时期还开始向法国左翼组织——法国『共产』党靠近,试图与他们建立一个联合阵线。但左翼组织却一直怀疑萨特的获释可能与德军有一定的联系而对萨特的行动持不信任的态度。因此,萨特不得不通过文学创作活动的形式宣传他的抵抗思想。而西蒙娜这时也坚信,作家应该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行动。自此,她更加把写作视为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1941年至1944年,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