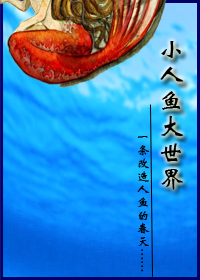世界历史名人丛书:西蒙娜 德 波伏瓦-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二次大战前,我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一个个体,我完全看不到我个人的存在与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之间有什么联系。……我建立了整套理论:我是‘孤独的人’,就是说,是一个因其思想的独立『性』而与社会相对抗的人,这个人不欠社会任何情分,社会对他也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他是自由的。”当然,西蒙娜并不是“三重奏”的发起者和倡导者,她只不过是在不自觉中被卷入其中。她并没有像萨特那样对这种“三重奏”的意义认识得如此清楚。
“三重奏”对波伏瓦来说,最后已谈不上痛苦,只是复杂罢了。但它发生与否,对波伏瓦却完全不一样。“三重奏”的发生,在西蒙娜看来,是一次情感教育的良好机会。经历了它,每个人都受到了一次情感上的洗礼。对她本人来说,这种情感教育的最大结果是促使她获得了精神上的独立。在“三重奏”出现以前,波伏瓦在行动上可以说是独立的。她可以独自远足、独立工作、独自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然而在思想上、情感上,她对萨特却有强烈的依赖『性』,她重视自己在萨特心目中的位置,关注萨特的想法,希望萨特来影响她的行动。但“三重奏”生活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触动了波伏瓦的思想,使她不自觉地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这就是西蒙娜与传统女『性』的不同之处,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抱守残缺,以哀怨来代替反抗。
西蒙娜·德·波伏瓦基本上于1937年开始了写作,这也是她与萨特爱情关系中“三重奏”频频发生的时期。在她的写作生涯中,萨特曾建议她把自己的经历写入作品。于是在1938年,在萨特的启发下,西蒙娜开始以她与萨特及奥尔加的“三重奏”为背景,构思一部自传『性』小说。这部小说于同年10月动笔,历经近3年,于1941年终于完成,西蒙娜命名之为《女客》。小说描写了一对年轻的情人弗朗索瓦兹和皮埃尔,他们出于同情收养了一个名叫格扎维埃尔的17岁的少女,并负责她的学业,充当她的监护人。这位姑娘就是书中所指的“女客”。这位女客拒绝接受弗朗索瓦兹和皮埃尔为她安排的前途,拒绝从事任何有意义的学习和工作,而只愿意按照自己的想法随心所欲地生活。出于对少女的同情和怜悯,皮埃尔对格扎维埃尔关怀备至。然而不久却身不由己地狂热地『迷』恋上她。于是弗朗索瓦兹和皮埃尔遂尝试了一种打破常规的生活,创造了“三人行”……
很明显,小说的素材基本取材于波伏瓦、萨特、奥尔加“三重奏”的真实生活。书中的女主人公弗朗索瓦兹就是波伏瓦,男主人公皮埃尔就是萨特,而格扎维埃尔则是奥尔加。在作品中,波伏瓦将几个月的“三重奏”生活中困扰自己心灵的万般情感体验凝聚于笔尖,将小说中独特的组合关系下,充满矛盾的人物之间各自的心理过程和情感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对小说中“三人行”的人际关系从亲密的朋友,发展到产生妒意,继尔到怨恨的发生这一过程,西蒙娜用细腻的心理分析方法作了透彻的分析,她还深刻剖析了女主人公弗朗索瓦兹那爱恨交织、欲语不能的复杂心态。当然,作为小说,波伏瓦对作品的结局也作了虚构化处理。在《女客》的结尾,女主人公受难抑的妒恨驱使,终于将房间里的煤气阀打开,以残忍手段,将情敌格扎维埃尔谋杀。这显然与现实生活中的“三重奏”的结局不相符合。但波伏瓦敢于在小说中,大胆地以自己为原型,将主人公塑造成一个谋杀者的形象,也无不反映出她那敢于蔑视社会道德的胆量。尤其是小说中,波伏瓦将弗朗索瓦兹在谋杀格扎维埃尔过程中的犯罪心理,挖掘得深刻、细致、真实、准确,无不衬透出她那种认真揣摩、记录人物的情感、行为,准确把握和『逼』真刻画人物『性』格心理的创作功底。
在《女客》这部作品中,波伏瓦几乎倾注了她的全部心血和感情。因此这部作品中也包含了她所经历过的、感受过的、体验过的一切心态和情感。从某种程度而言,它是一部以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西蒙娜·德·波伏瓦人生重要历程的断代史。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波伏瓦,无论是在情感还是在行为方面,都超过了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形象。她的真实生活要远比小说中的形象,更具有启迪和教育意义。
1936年至1939年的“三重奏”『插』曲过后,紧接着二战爆发了,萨特被应征入伍。经历了情感教育和战争风暴之后,西蒙娜和萨特的爱情又有了新的升华和发展。回首战前的“三重奏”生活,虽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相继结束,但其中确实包含了一定的哲学『性』意义。从表面上看“三重奏”只表现出了男女关系的复杂『性』,它更多地涉及男女关系中,异『性』相悦的自然属『性』一面。然而,导致“三重奏”失败终结的真正原因,也许并不是外部的因素,也不是生理学方面的因素。这要涉及西蒙娜·德·波伏瓦与让-保尔·萨特之间爱情关系的本质。西蒙娜和萨特所签订的爱情契约从本质上说,虽然不排斥对其他异『性』在男女相悦上的追求。但它更重在强调和维护双方在精神上的自由和融洽。从西蒙娜和萨特一相识起,两人就始终在追求目标、精神思想方面寻求一致,而努力达到情感上的高度融洽和默契。这种寻求精神上的共鸣关系是他们爱情关系之所以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基础。而从“三重奏”失败的事实来看,西蒙娜与萨特之间的精神合作关系也确实是其他关系所代替不了的。关于这点,萨特后来在其晚年的作品《七十岁自画像》中曾提到过:他常把他确定的或尚未确定的思想向西蒙娜表达。因为唯有她对于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认识达到了与他同等的水平。他把西蒙娜视为最理想的对话者,他与西蒙娜总是处在对等的关系中。
尽管在西蒙娜与萨特后来的生活中,“三重奏”仍然还会出现,但无论现实中他们各自与其他情人的关系如何发展,西蒙娜与萨特之间却始终保持着最初的爱情契约,终生相伴。他们在精神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一生中,相互欣赏、相互理解、彼此宽容。正如萨特所言,他们不是两个,而是一个“我们”。在20世纪的初叶,西蒙娜和萨特的契约式爱情,不仅给人们提供了两『性』关系的新模式,而且也引发了人们对于男女关系、爱情关系本质的新思考。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西蒙娜 德 波伏瓦 第七章存在主义
1943年前后的战争期间,对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尔·萨特来说,是一个迭宕起伏、荣辱俱存的时代。这期间,既值波伏瓦因莫里哀中学之控而弃教失业,及萨特于战中被俘而身陷囹圄的多事之秋,也是西蒙娜的《女客》出版和萨特一系列文章完成的丰获之年。更重要的是,这一年是他们发起著名的存在主义运动的标志点和里程碑。
萨特自因释回国后,积极地参加巴黎的地下抵抗运动。他四处呼吁,奋力笔耕,用文学的形式宣传他的政治主张,支持抵抗运动。该年初,他参加了全国作家委员会,并为法共领导的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报》撰稿。同年4月,他的三幕剧《苍蝇》发表。该剧于6月2日在西岱剧院上演。彩排那天,在大厅里,萨特与年轻的阿尔贝·加缪初次结识。《苍蝇》的上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使萨特成了巴黎记者争相采访的热点人物。同年10月,萨特的哲学论著《存在与虚无》出版,该书的题辞是献给波伏瓦。此书的出版,又引起了巴黎文化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当时,评论界把萨特在这本论著中所阐明的哲学称之为存在主义。萨特对此表示抗议,他反驳批评界:“我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哲学。‘存在主义’我不知道这算什么学说。”不管萨特本人乐意不乐意,但他已被报界、评论界视为二战期间法国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人物。萨特的声名鹊起,对西蒙娜·德·波伏瓦是极大的安慰。这一年,西蒙娜在经济上主要依赖于萨特。在萨特的鼓励下,她也开始结交巴黎名流,经常出席朋友、名人的聚会。在二战行将结束的最后一年,任《战斗报》编辑的阿尔贝·加缪常常请西蒙娜和萨特撰稿。为此,他俩在《战斗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报道巴黎解放的文章,这些文章极大地鼓舞了巴黎人的斗志。
二战结束前的最后一年及战后,西蒙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一时期被她自己称为“道德时期”,实际上是其存在主义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时期。1944年波伏瓦发表了一篇哲学随笔《庇吕斯与西奈阿斯》。在这篇哲学随笔中,波伏瓦阐述了“境况”的概念。她在文章中分析了人在现实中所处的种种境况,指出了人在境况中作出选择与行动的重要『性』。在《庇吕斯与西奈阿斯》中,波伏瓦对比了庇吕斯与西奈阿斯的人生态度。西奈阿斯否定选择行动的意义,他认为:假如人们为了要回自己的家,那又何必出行;需要停下来休息,又何必开始行动。而庇吕斯则肯定行动、选择的意义,他主张人活着就应该赋予其生命一种意义,而通过行动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波伏瓦在文章中阐述了在同一类境况中,不同的选择会导致境况的变化。她对“境况”的阐述,对后来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波伏瓦有关境况的概念的启发,后来萨特创立了一种新剧种——“境遇剧”。此剧专门把人物置于某一境遇中,促使人物作出某种行动或选择。萨特在其境遇剧中,提倡了自我选择的意义。
二战结束后,法国经济萧条,社会动『荡』,战争和德国法西斯的统治给法国人民造成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而这一时期,法国报纸披『露』了德国集中营中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新闻媒界对集中营的报导不断引起了人们的震惊。加之美国在二战末,将第一颗原子弹投到了日本的广岛。新型杀人武器的使用使人们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新的认识。一种厌战,逃避现实的情绪在法国蔓延。而战后的现实又使人们看不到希望。因此,这一时期,悲观主义、虚无主义思想抬头。人们重新又生活在一种新的恐惧、厌恶、绝望、消极的状态中。面对这一现实,萨特、波伏瓦和他们的朋友梅劳·庞蒂、雷蒙·阿隆等人共同创办了《现代》杂志。他们试图给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帮助人们消除一些消极的心理。1945年10月15日,萨特在《现代》杂志第一期上阐述了其介入文学的思想和作家的革命作用。此后,萨特又发表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而在同一个时期,西蒙娜·德·波伏瓦创作的剧本《白吃饭的嘴巴》上演了。这个剧本采用借古喻今的形式,揭示了战争中屠杀行为对人们心灵的重创,表现了战争的悲剧『性』和残酷『性』的主题。该剧本描写了战争中,许多『妇』女、儿童、老人、残废人,被视为“白吃饭的嘴巴”,他们被当局默许杀害。在战争期间,这种对无辜平民的屠杀不仅被默许,而且还被视为壮举。西蒙娜·德·波伏瓦试图在剧本中,探求这种野蛮、残忍行为背后的意义。该剧的上演与萨特的著名讲演《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终于引发了“存在主义”运动。尽管萨特和波伏瓦拒绝存在主义这个标签,但他们最终不得不再次拣起了这个标签。在这场存在主义运动兴起的过程中,萨特被视为存在主义的教皇,而波伏瓦则被封为圣母。波伏瓦也成为了萨特麾下的一员战将。
1945年是西蒙娜颇为忙碌,收获甚丰的一年。她于同年二月应邀去西班牙与葡萄牙作关于占领时期的报告。她在这两国的逗留期间,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摧残给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回到巴黎后,她撰写了系列报道。在文章中,她谴责了战争,也批评了『政府』在战争中的行为。尽管这些文章的内容遭到了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政府』的干预,但波伏瓦还是将它们发表在米歇尔·柯里莱主编的《意愿》杂志上。这又一次充分体现了波伏瓦的一贯作风和对社会事务敢于介入的态度。
1945年9月,波伏瓦又出版了她的第二部小说《他人的血》。这部小说比《女客》更受欢迎。该作品主要描写了二战期间,巴黎被德军占领时期,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的业绩。小说通过五个青年男女在被占领期,德国法西斯力量嚣张时期,每个人各自的人生选择,探讨了自由和责任的问题。小说中,这五个青年都是通过自我选择,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和生活意义。男主人公让在战前曾参加了『共产』党,积极组织了工会运动。但后来因为自己的朋友雅克在罢工中的牺牲,使他因不希望见到他人的血而退出『共产』党,不再过问政治。但在巴黎被占领时期,法西斯甚是嚣张,让又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留在了巴黎,建立了地下抵抗组织,领导巴黎抵抗运动的战士,开展反法西斯斗争,为保卫巴黎,他作出了行动和选择。小说的女主人公海兰娜在战前是一个只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自由主义者。她只关注个人,从不认为自己与社会有关系。战前,她在爱情上作出了自我选择。她抛弃了自己的男友保尔,而选择了保尔的朋友让。让不爱她,但她认为,自己选择让是她个人的自由,她可以作这种选择,而并不需在乎让的看法。在二战期间,让被征入伍上了前线。海兰娜通过关系把让调至了巴黎,她不愿让男友牺牲在战场上。结果让与她发生了冲突,最后两人决裂。在沦陷区,海兰娜试图通过求助于占领军,离开巴黎到柏林去。后出于民族的自尊心,她放弃了这种打算,转而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组织。她的女友——犹太姑娘要遭到法西斯的逮捕。为了保护女友免遭迫害,她开始了营救工作。后来海兰娜在执行任务时牺牲。在这部小说中,西蒙娜提出了存在主义的文学主张,提出了自我选择的意义。她在小说中主张自由选择要与社会责任、人类命运结合起来。
1945年,小说《他人的血》和剧本《白吃饭的嘴巴》的出版与上演,在法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推动了这一时期法国的存在主义运动。西蒙娜·德·波伏瓦也和萨特一样,成为了法国存在主义运动的重要代表。诚然,在这场存在主义运动中,由于萨特的声名显赫和宏大影响,使评论界对波伏瓦的作用,有些估计不足,并常把她视为萨特的追随者。事实上,虽然,在法国存在主义运动的发展时期,西蒙娜常常追随在萨特和加缪的左右,但她确也以她自己的方式积极地参予和推动了这场运动。1945年12月,她曾作了两场关于存在主义小说和哲学的演讲报告,因为当时法国的报界以及社会舆论对存在主义哲学的毁誉、对萨特和波伏瓦的人身攻击越来越厉害。当时对存在主义的攻击来自四面八方,人们纷纷指责存在主义哲学是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哲学,是不道德的哲学,是毫无价值的、下流的、卑鄙的哲学。有人甚至攻击波伏瓦与萨特的爱情生活,他们把西蒙娜说成是一个具有放『荡』习『性』的女怪人、女疯子。针对社会舆论对存在主义哲学和小说的曲解,波伏瓦举行了这两次报告会。她要为存在主义哲学辩护。她认为存在主义哲学教给了人们“全面深刻地面对责任感”的意识,每个人都应该在行使自由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