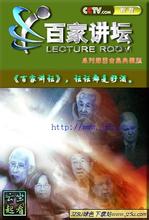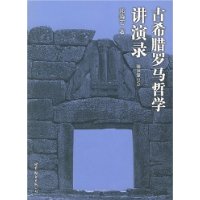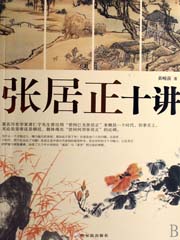张居正十讲-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嘉靖二十六年,世宗已经四十一岁,他逐渐厌倦了皇帝的生活。
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居然有人会厌倦当皇帝?其实,如果有人这样问,他只是站在平常人的角度在看问题。如果换成明世宗的角度,就不难理解他的厌倦了:整天都大权在握,待在一个高得不能再高的位置上,长久下来肯定会失去上进心,会觉得生活很无聊。这个时候,如果再有繁杂的政务,那就会更加加深他的厌倦感。
事实上,从嘉靖十八年开始世宗就不再上朝,后来甚至连宫内也不住,干脆搬到了西苑万寿宫。
可以想见,这个时期的政务,他几乎是理都不想理。那么,这时期,他又在干吗呢?
原来,从嘉靖二年起,世宗就开始修醮(音同“交”),也就是修行道教,整天跟道士混在一起。可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明世宗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政权。尽管世宗一心向道,但是对于政局,他仍然牢牢地把持着。
因此,应该这样理解他:他只是厌倦了政治生活,但却没有厌倦到抛弃的地步。毕竟,当皇帝还是可以享受到很多优越的生活条件的。
可是,就算这样,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明世宗的大权毕竟有些旁落了。试想,那么多精明能干的大臣在身旁,一旦皇帝无心政事,他们能不趁机捞取政治权力吗?
事实的确如此,这个时期的政权就逐渐落在了一个大臣的手中,他就是显赫一时的严嵩。那么,这个严嵩又是怎样一步步取得这样大的权力的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需要先了解明朝的政治制度。
明朝政治的核心是内阁。这个内阁可不是西方国家的内阁,它只是皇帝的一个秘书厅,专门负责为皇帝起草诏谕。
内阁里的成员称为内阁大学士,也就是皇帝的秘书。内阁成员的数目多的时候有八人,通常只有四五人,有时仅有一人,他们都是由皇帝任命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因此在内阁讨论问题时,经常会出现意见上的很大分歧。在争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领袖制度,这就是明朝著名的首辅制度。
首辅是个什么样的政治角『色』呢?其实,他就是皇帝的秘书长。由于他的这个地位,因此在内阁起草皇帝的诏谕时,事实上都是由首辅一人拟稿(被称为“票拟”),其他人只有偶尔提些无关紧要的建议。
关于首辅的产生,长期以来的习惯是根据内阁学士的资格,谁资格越老,谁就能当上首辅。其余的人,就被称为次辅。
这就是作为明朝政治制度核心的内阁。虽然由于内阁成员是由皇帝任命的,因此权力仍然低于皇权,但是由于内阁负责着诏谕的起草,因此事实上掌握着很大的权力。
另外,由于内阁首辅在内阁起草诏谕中的优势地位,因此内阁以及内阁首辅就成为了明朝政治权力争夺的中心。
每个进入政坛的人都知道,只要能够进入内阁,就意味着这个人已经进入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只要能够当上内阁首辅,就意味着这个人已经拥有了对于大臣来说最高的政治地位。
首辅政治的残酷『性』正是由于内阁首辅的重要政治地位,再加上首辅和次辅的职权划分一直都没有明文规定,因此在内阁里面,就存在着首辅和次辅的权力之争:次辅因为想要当上首辅,就会攻击首辅;首辅因为感到次辅的威胁,也要想办法驱逐次辅。
他们的办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取悦于皇帝,以求得皇帝的信任,同时降低皇帝对自己对手的信任,从而借助皇帝打败政敌。于是,在这个明朝的政治核心里,就充满了血腥浓重的明争暗斗,这里常常潜伏着诬蔑、谗毁和杀机。
严嵩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中逐渐掌握大权的。在张居正当上庶吉士那年,也就是嘉靖二十六年,内阁中的大学士除了严嵩以外还有一个人叫夏言。严嵩和夏言都是江西人,一个来自分宜,一个来自贵溪。但是,这两人却毫无同乡之谊,只有相互的敌视。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嘉靖二十三年以后,严嵩曾经当过一年有余的首辅,但到了嘉靖二十四年九月,皇上就让夏言进了内阁,由于他曾经当过三年首辅,资格比严嵩老,因此严嵩只好退为次辅。
从这之后,两人就结下了仇怨。尤其是严嵩,一有机会就会攻击夏言。正好夏言又是一个『性』格刚强傲气的人,自认为君子坦『荡』『荡』,这就给了『奸』佞的严嵩很多机会。
一次,世宗戴着香叶冠醮天,一时高兴,就做了几顶分赐大臣。第二天,严嵩戴着香叶冠到西苑来了,可夏言竟没有戴。当世宗问他为什么不戴时,他却说大臣朝天子,用不着戴道士的衣冠,惹得世宗心里非常不快。
严嵩看出了世宗的不快,就借机会向世宗哭告夏言欺负他。世宗本来就不爽夏言,于是便把夏言斥逐了,这是夏言的第一次失败。
夏言走后,内阁成了严嵩的天下,一时间贪污腐化成风,这时世宗才想起夏言,让他又进了内阁。
可是,经历了失败的夏言仍然是那个『性』格,决不讨好皇上的内宠。比如,世宗派小内监到他们家去时,夏言把他们当奴才看。严嵩却与小内监并坐,小内监走的时候,他更是送给他们很多的金钱。
由于这样的原因,夏言得罪了许多内监。这些人就经常在世宗面前说他的不是,再加上严嵩借在外患问题上世宗和夏言的矛盾,极尽其诬告的能力,最终使得世宗龙颜大怒,下令杀死了夏言。
可以说,夏言的失败,并不是失败在他的能力上,而是输在了他的『性』格上。
从那之后,严嵩再次当上了首辅,再没有谁能够跟大权在握的他硬碰硬,明朝的政局就这样被他一直控制了十五年之久。
这里有一个问题:夏言和严嵩进行你死我活的政治权力之争时,张居正在干吗?他对当时的政局又有着怎样的政治态度呢?
我们知道,张居正参加会试,考中了二甲进士,因而在当上了庶吉士之后,按照当时的惯例,他实际上是待在翰林院里的。
明朝的翰林院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呢?一般说来,翰林院是新科进士向其他官职升转的一个中间机构,因此对于实际的政治,它并不承担任何职任。
在翰林院里,新科进士同以前进来的士人们一起研讨诗文,过着悠闲的日子。
然而,这并不是说翰林院里养的只是一些会『吟』风弄月的酸文人,这里同样有一部分士人在研讨朝章国故。因此,准确地说,翰林院是一个既培养文人,也培养政治家的地方。
这样的情况,在张居正进入翰林院的时候一样存在着。大多数的进士们,都颇有兴趣地讨论着怎样才能做出西汉的文章、盛唐的诗句。
张居正并非不热心这些活动,只是在他的目光里,正在关注着更为紧要的事情:明朝当时的政治局面。他正在注意观察那些握有实权的人,仔细寻找着自己应该依附的“大树”。
要知道,对于一个有着宏伟抱负的读书人来说,是绝不会只用心于诗词歌赋的。无疑,在这样复杂的政治格局里,应当怎样保护自己进而从容向政权的最高处上升,才是此时的张居正最热衷的事情。
既然如此,张居正不能不知道朝廷当时的一些大事:他肯定已经了解到了在内阁里面那场血雨腥风的斗争,也知道了夏言的失败和严嵩的胜利。虽然对于当时的政治局面,张居正作为一个新科进士,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但是他对于时局还是有了如此的认识。
那么,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张居正又会有怎样的政治态度呢?他肯定也听说过严嵩的『奸』佞,那他又会对严嵩抱持一种什么态度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张居正在翰林院期间,不可能不跟严嵩发生联系。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在于:严嵩作为内阁大学士,同时也是翰林院的长官,他的一切公务都是使用翰林院的印,因此在严嵩往来于内阁和翰林院办公时,张居正跟严嵩发生联系是很正常的。
其次,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张居正在与严嵩的交往中,采取的是何种态度呢?
我们从张居正留下来的《圣寿无疆颂》、《得道长生颂》和《代谢赐御制答辅臣贺雪『吟』疏》(均见《张文忠公全集》)几篇文章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张居正对当时权倾朝野的严嵩采取的是合作态度,因为这些文章都是代严嵩做的。
张居正虽然知道严嵩并非良臣,甚至就是一个坏主之臣,但是他没有傻到直接与之对抗。因为他知道,跟严嵩对抗没有必要,再说也对抗不起。在自己的实力没有足够大时,只能保存力量,不能急于暴『露』自己的立场。从这方面看,张居正还是比较沉得住气的。
并且,从后面的历史来看,张居正对于严嵩的这种合作态度维持了很久,甚至后来出现了“庚戌之变”,他也没有跟严嵩决裂。这样的态度,很好地体现在了严嵩当权时期张居正的一些政治行为上。
先来看一下张居正上《论时政疏》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张居正进入翰林院时是庶吉士。按照明朝的制度,庶吉士只是一种学习的官员,在翰林院中称为“馆选”,等到三年期满后就要“散馆”,这时候凡属于二甲进士的,都要赐予编修的官衔。因此,到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时,张居正就成为了翰林院编修。
然而,此时的他仍然没有实权。他只能上些奏疏,不能参与实际的政治决策。
尽管如此,一心为国为民的张居正仍然上了许多疏,充分表达了自己对时政的见解,初步显『露』了自己的才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论时政疏》。在这个奏疏中,他指出了当时政治的五种臃肿痿痹的病况,这些病况分别是:“其大者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疾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亏,其他为圣明之累者,不可以悉举,而五者乃其尤大较著者也。”
张居正指出的五种政治病状分别是:宗室势力过大、官员不尽职、吏治不好、边境守备不严和财政开支太大。紧接着,他还指出了政治上应该作的改进:“五者之弊非一日矣,然臣以为此特臃肿痿痹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气升降而流通,则此数者可以一治而愈。夫惟有所壅闭而不通,则虽有针石『药』物无所用。伏愿陛下览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广开献纳之门,亲近辅弼之臣,使群臣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虑,君臣之际晓然无所关格,然后以此五者分职而责成之,则人人思效其所长,而积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
张居正将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喻成使身体血气畅通的方法,认为要想解决政治上的问题,只有“通上下之志,广开献纳之门,亲近辅弼之臣”才能实现。
从后来张居正留下的奏疏看,这是他第一次上疏,对问题的分析十分到位,说明他的确很留意政治上的缺陷。但是,这些都不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张居正在这个奏疏中提到的问题,不是只有他一人才看见的,其他一些清廉的官员比如海瑞等,也十分清楚地向皇上指出了。
与张居正不同的是,这些清廉的官员大多没有因为上疏得到好结果,相反还身遭刑狱之灾,甚至还丢了『性』命。可张居正却安稳如泰山,既没有得罪明世宗,也没有得罪严嵩,却仍然把该说的话都说了,这不能不说是张居正的过人之处。
的确,海瑞这些清廉的官员是做到了直谏,但是却没有收到相应的好效果,反而祸及自身,却又何必?对于张居正的如此作为,我们只能从保存自身力量,留待他日使用的角度来理解。如果他不这样做,日后或许就没有神宗年间短暂的天下太平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在他的上疏中,张居正对严嵩还是采取了合作的态度。
或许是他知道这样的上疏迟早会惹祸,因而在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张居正再也不对时政发一言一语,只是埋头钻研朝章国故。
在严嵩当权期间,另外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明张居正对严嵩的合作态度。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正月是严嵩七十岁的生日,文武百官都前来向他道贺,有的人甚至借助这样的机会极尽巴结之能事。
张居正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不会落后,他给严嵩写了一首名为《寿严少师三十韵》的贺诗,其中有这样几句:“握斗调元化,持衡佐上玄,声名悬日月,剑履『逼』星缠,补衮功无匹,垂衣任独专,风云神自合,鱼水契无前。”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对严嵩得宠的地位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世宗对严嵩专有的信任。在这首诗中,张居正还有这样几句:“履盛心逾小,承恩貌益虔,神功归寂若,晚节更怡然。”(均见《张文忠公全集》)这几句诗表面上虽在说严嵩在皇上面前的谨慎和虔诚,实际上表达了张居正对严嵩的一些好感。
的确,张居正就算知道严嵩是个『奸』臣,会误君误国,但是一方面因为皇帝还没有完全放开权力,另一方面严嵩也没有『奸』邪到非除不可的地步。
而且,严嵩并没有构成对张居正的直接危害,因此张居正犯不着跟严嵩过意不去。更何况,他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呢!
然而,如果张居正对严嵩就这样一直采取合作的态度,那么历史上顶多只会出一个『奸』臣,决不会有明末的张居正改革,明朝或许就会提早灭亡了。
那么,张居正对严嵩的态度是何时改变的呢?这要从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说起。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间,蒙古族的俺答攻下大同,八月攻下蓟州。蓟州失陷后,敌人再从古北口取道通州进攻,很快就对北京形成了围攻之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庚戌之变”。
然而,当时的明朝,武备已经松弛,大不及从前。等俺答打到北京近郊的时候,兵部尚书丁汝夔(音同“葵”)只整编出五六万人的军队,而且大多数是老弱残兵。
眼看敌人就要攻进城了,无可奈何之下,明世宗只好下诏勤王。很快,大将军咸宁侯仇鸾就从大同带了两万大军前来救援。
可是随着勤王军的陆续到来,军队的给养成了问题。
士兵吃不上饭,也没力气打仗,因此仇鸾也不敢开战,只好派人和俺答谈判,只要不攻城,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俺答回答说要明朝给他们进贡,于是明世宗只好召集大臣们商议对策。前来商议的有大学士严嵩、李本以及礼部尚书徐阶。
看着忧心忡忡的皇上,严嵩宽慰道:“这是一群饿贼,皇上用不着『操』心!”
可徐阶却严肃地说:“军队一直驻在北京城外,杀人如割草一样,这不仅是饿贼了。”
世宗点点头,转脸问严嵩看到俺答的《求贡书》没有。
严嵩从衣袖里抽出一份说:“求贡是礼部的事。”
“事是礼部的事,但是一切还要皇上做主。”徐阶接过话。
“本来是要和你们商议的。”世宗说。
“敌人已经到了近郊,要开战,要守城,什么都没有准备,目前只有议和,但是唯恐将来要求无厌,这是最大的困难。”徐阶说出了心中的焦虑。
“只要于国家有利,皮币珠玉都可以给。”世宗很慷慨。
“只是要皮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