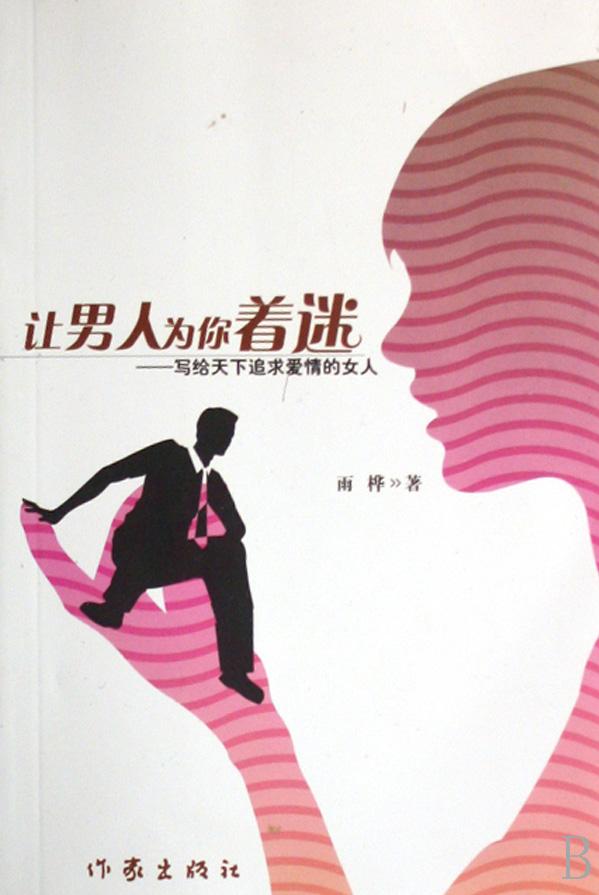遭遇爱情-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黑:(目瞪口呆)
林:你瞪眼看着我干什么?劳伦斯他多个鸡巴。
黑:(不相信地)你说什么?
林:我说劳伦斯他多个鸡巴。
黑:··我可算是服了你了,很有教养的小女人,怎么能够出口说出这么脏的话?林:哎哎哎,这可是你先说的呀9你躲在外文单词里口淫着,而我只不过是用汉语把它直截给说破罢了。至少我还有跟你同等说话的权利吧?黑:我又没有剥夺你的权利。
林:可是你为什么听着受不了呢?你是不是只期望我回应你的话,希望我以诗朗诵的形式赞美它,就像赞美一朵花?
黑:就算是那样吧,又有什么不对的呢?林:劳伦斯总让他的男主角说野蛮粗鲁的话,又总是让康妮用诗意的语言回敬他。把他两腿中间的那玩艺赞美得跟什么似的,这不是阳具又是什么?跟手淫又有什么区别?
黑:(思忖)晤……对,劳伦斯的确是就多了个鸡巴。他不多个鸡巴还能多什么。
林:哈!明白了就好,别总以为自己多点什么呢。
黑:好了吧?这回来吧。 Come on。黑戊把身上的机器重新启动起来,吭防吭味地把林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给辗轧了。
这个刺猥似的小女人究竟有什么地方吸引了他,让他死缠住她不放呢?除了她和他之间的十余年的年龄差,他被她的热情奔放迷惑住外,更重要的是,语言,是语言让他们之间相互纠扯着难以分开。有许多思想的火花便在这语言的较量和交锋中无形地产生了。书读得太多以后,他感觉着自己的话语场就整个儿的跟常人对接不上了。如同高手和大师们总是要在高处默默地悟道参禅,是因为他们在修炼成功之日起,便把值得一打的对手无形之中给失去了。俯视脚下芸芸众生,他们除了空怀绝技手握空拳嘴唇空张,既失手又失语外还能干些什么呢?
担心自己会肌肉萎缩、哑然失者的巨大恐惧深深地把他擒住了。林格看见他是那么焦虑急切忧心忡忡地说着,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地说着,捶胸顿足扼腕律眉地说着,振聋发腔义愤填膺地说着,小题大作没屁硬挤地说着,看似扈了解牛实则瞎子摸象地说着,不分时间和场合,人来齐了就开说,把“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挂在唇边上絮絮叨叨念来念去地磨嘴皮子,像是在练着灌口盥口或者洋绕口令。叩,简直是说得比唱得都好听了。
他的脸色这会儿怎么变得这么忧郁苍白啊,就像患了什么贫血症似的。林格一面隐隐地替他的身体担心着,一面将他说的这些话语—一记录下来,转换成书面文字的形式,帮他拿到各种报刊上去发综述文摘和报道。黑戊博士的话语雪片般铺天盖地连篇累牍地印刷出来,占满了各种学术杂志文学月刊的版面头条。她听到报社的同事一边翻看着杂志一边发牢骚:“怎么回事啊?怎么到处都是文学博士黑戊的文章啊?没劲。”
她又听他拿起另一本刊物翻着发牢骚:“怎么回事啊?怎么连文学博士黑戊的文章都没有啊?没劲。”
林格听得暗暗地笑了。看来走红并不一定就是好事情,这年头人们追星的口味已经大大提高了,见不着的时候虽然想得慌,可若是表演得太多了又实在是遭人烦死了。怎样才算适中又适量?一星期之内亮几次相,搞几次演讲,发几篇文章,撅起尾巴做几次秀来摇几摇,拿着旗杆晃几晃,才能让观众看着既解闷儿又过原,回味深长心里老是在挂想?
作为与黑戊狼狈为好一丘之貉的新闻发布人专职谈话记录者林植小姐,如今愈发失去对黑戊言行的把握了,只能任由他抓叽叭叽上下嘴唇不住窈动使劲地说,她只能闷头猛记笔走龙蛇。
他说我们的确应该在国人当中倡导一些俄底铺斯杀父娶母情结,是时候了。不推翻那些占着茅坑拉不出屎来的老不死的们,青年人就永远别想称爸当爹称霸为王翻身得解放。江浙一带的小帅哥才子们的破破烂烂的童年回忆录里,已经可以榨挤出不少“伊狗”“里比多”“杀父娶母”意识了,要赶紧组织评论,加以疏通、引导、光大,说晚了就赶不上世界新潮了。
(记录这些话时林格暗暗为他捏着一把汗,她注意到座下两位资深老先生的脸色已经开始变白了。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里,谁敢不忠不孝而且还要娶他妈妈,这不是成心不想活了吗?完了,江南那帮小作家们要倒霉了,林格可不能眼看着他们被乌队深渊却撒手不管。于是她便思忖着,怎样在文字记录上把他的话给国一国。)
林格没有想到,自己的担心纯属多余,黑戊倡导够了俄底浦斯后,话题一转,马上就变到宏扬国学方面去了。“我们应当想法给孔子和耶稣两位老人家对调一下工作。”他说。
他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呢?林格听得俗里份恒的,笔尖在纸面上艰涩得划不动步了。座下的其他人似乎也一下子没听太明白。
“进入初世纪以来,洋玩艺攻入得太的太厉害了,不是洋枪洋炮的轰,就是彩电汽车的送,而我们能回敬出去的,除了中医烹调,太极气功,也就剩下孔夫子一人能与基督耶稣相匹敌了。”他说。
林格勉强听出了个眉目,原来他这是要就地倒卖祖宗了。这也不啻是杀父的一条捷径啊!
“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依我看连半部都用不了,有一两句就足够了,绝对是打遍江湖无敌手。”黑戊满怀信心地握憬着。“如果对世纪全体北美和欧洲人民全都信奉起孔教来,那该是一个何等壮观的情景啊!全体地球村的人民一打开自己的电脑信箱,就能看见一个梳着疙瘩髻,满脸都是稻的古代小老头出现在彩显屏幕上,兢兢业业口若悬河地给大家讲着克己复礼的道德文章。圣诞节的时候又是这个小老头戴上了小白胡子,挨家挨户往儿童们的袜子里塞线装本的(论语》和(诗经》三百首,大人小孩读了以后就都淡泊自守,一点脾气都没有地一草食一壶羹滋溜滋溜喝坚硬的大锅稀粥,后工业时代喝酒吃肉撑出来的物欲横流的麻烦事就全都一扫而空啦。” “哗”
座下传出掌声惊叹声一大片。黑戊这小子也太他妈的聪明了,我们怎么就没能及时想到呢!人们众口一辞地称赞着,全都被他口吐白沫的演讲吸引去了。你还真别说哎,亚太地区腾云驾雾委起来的那几条小龙,全都是有儒学在背后当脊梁骨支撑着呢,向西方学习过的皮毛小事简直就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不组织起来成立个“国际儒联”呢?虽然听起来跟“国际足联”有点像,但这可是头和脚的区别差着天上地下呢。看样子足球一时半会是没法踢出亚洲了,不妨就把儒学先踢出去解解闷吧!黑戊兄弟,就委托你来当黑马,挂职联长领我们一道干一场。 “不行不行不行,”黑戊客气地摆摆手,“还是请老先生来,请老前辈出任吧,我充其量也只能当个秘书长,帮着跑腿打打杂什么的。”
林格“吃吃吃吃”地窃笑着,看见黑戊缺少血色的苍白俊逸的脸,在众声合鸣中已经兴奋地转红了。她怎么看他怎么像一个奥导演,为了节省经费省时间,也为了把自己的才能穷显摆,就把一出戏里所有人的声音全由他一人给配了。所有人的身份便都会并成了他一个人的身份,像是多次曝光的幻影游动,简直分不清他的真身在哪里了。林格:你到底想要说什么?你到底要担当几种角色?黑戊:我想到了什么就说什么。多有几重人格面具又有什么不好的。林:你能不能把你的话想好了再去说?你能不能老老实实担当好一种角色?黑: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话已经在我想的前边自己抢先说出来了。天已经降大任于斯人。我怎么能够不去担当?我怎么能够保持缄默?林:你能不能把话少说点?话说多了自然就要有漏洞的,自然不能自圆其说。黑:我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我干嘛要少说呢?我是非说不可了。林:“非说不可”是什么?就是脑袋上缠着白布条,跑到广场上充旗杆,镜头面前留个影,然后便去等待大赦拿绿卡吗?黑:你不要理解得这么偏狭。我只能如此,非如此不可。
林格不能再跟他辩下去了,“非如此不可”,他已经开始背诵米兰·昆德拉的话。他的脑袋里被各式各样哲人名人的论断塞满了,他能脱口而出背诵出来,引用得准确得当,不用查原文也知道连标点符号都不带引错的。可是这种搅和到一块的引用和背诵,产生的效果却是那么的奇异和混乱,简直让人不知所云,也让他自己不知所措,仿佛他只有不停地说,说,用他自己制造出的噪音把自己的视听充塞住,这样才能感到安全些,否则他简直就要惶恐死了。
他似乎也并不在乎自己说的是什么,只要还在不停的说,口舌还在蠕动着,满嘴里还在飞唾沫,他才能认明自己还活着,否则的话他可真的要死了。
话语简直成了他最好的润滑剂,涂上它,他便可以在艰涩滞重的现实隧道中轻快畅美地游七摩拳,擦出不尽的快感一浪高过一浪,一波连着一波。
他一会儿说要杀父娶母,一会儿又说要弘扬国学;一会儿说他离不开他妻子,一会儿又说他深爱着林格。他说他真是没办法离开他那温柔贤惠的沪籍陪读夫人,她对他爱护关怀备至,每天为他洗衣煮饭,擦鞋修面,甚至连牙膏都替他挤到牙刷上,把漱口水端到他面前。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出了什么意外,他的妻子儿子还说不定难过成什么样呢。
他一面无比深情地回顾着,同时又说他感觉着自己真是承受不住妻子过分期待的目光了,那目光简直就像一个大气压强,拼命地把一些稀哩恍叽的纯蓝墨水压入他腰间那只笔上,让他简直就没有饱满的精力自由挥洒,明显感觉着自己要变得稀软了。
好花还须绿叶扶,他说林格只有你才是我最心爱的,只有你才最懂我的心,才是跟我最默契的一个人。有你在身边我就谁都不需要了。我是不会允许别的男人娶了你的。你若是跟了别人我会发疯的,我会闯入你们婚礼的洞房,骑一匹白马把你抢出来··他已经完全想得出神火化了,完全没有注意到林格一旁忍俊不禁的快乐眼光。一把茶壶四个碗,一个男人八个妾的遥想简直把他神往坏了,根本就不考虑是否有足够的水份去暇给,还以为自己是个自来水管,龙头一拧开就能哇哇哇哗哗哗自动流着往外淌呢。
林:(伸出手来在他眼前来回晃)醒来吧,哥哥!还发痒症呢?革命家史痛说完了吗?你以为你是谁,大博士化装成白马王子了?一般来说只有和尚取经时才爱骑白马呢。
黑:(无限深情地)格格我不是在痴人说梦,我的确是在这么想。天底下没有比咱们再合适的一对了。
林:算了算了吧。你能把书一顺水的读到今天,没有人家的红袖添香能成吗?你们不也是拓着双打配合走过来的吗?
黑:那可不一样。林:有什么不一样的?你还当我不知道你在妻子面前的表现哪?暗,你连她的梳子都仔细摘好了,生怕有我的头发落里边。你这么小心翼翼生怕伤害了她,干嘛还到我这儿来说闲话?黑:格格,你为什么不肯相信我?我是真心爱着你,我真想向全世界骄傲地宣布我们的爱情。林:我说先生体行行好吧,是不是又想亮出大裤权来当旗帜了?是想宣告你比别人有种,你的行为能力比别人的一强是吧?你就是不去招摇的话,谁又能把你当哑巴卖了是怎的?本姑娘将来还要出嫁呢,让你这挑旗一搅和可谁还敢要哇。
黑:你要是跟上了别人我非嫉妒得把你杀了不可,或者是我自己痛苦得死掉。林:(嘻皮笑脸)那么还是你自己一个人先死掉了比较清静。黑:(扬起拳头,恐吓)我揍死你!
林:嘻嘻……
林格知道他不过是口里说说耍耍贫嘴罢了。从思想到行动之间还隔着老大一段距离呢,那几乎就是一条十分险恶的天河在横亘着。他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在语言的此岸逍遥着,巧舌如簧,指手划脚,冥想着自己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角色。可是真正让他揭竿而起斩木为兵付诸行动时,他却连一点泅渡的勇气都没有了,只能是眼巴巴地遥望着彼岸,咀嚼着青紫的嘴唇不敢上前,甚至连胜水湿一下鞋的勇气都没有了。
弄潮儿向滩头立,手把旗杆脚不湿。她知道他一向如此的。他这滥情的誓言她都听过不知有多少遍了,她根本就不期图他会把什么许诺给兑现。他一边尽心尽意孝顺着他那亲爱的好老婆,一边又用甜言蜜语把林格哄得像棉花糖似的,拿着她们当成他事业长跑马拉松时的滋补营养液。他的自私和孱弱林格早就看明白了。可她为什么还不尽早抽身离开?是什么东西还在使她恋恋不舍?难道说她还心有所托,她的探索还没有结束吗?
有一种过失不能弥补,不断忏悔又全心投入,委身成蛇一样彻骨的虚无。心动之后,再也没有圆寂的净土。
要想戳穿一个已婚男人信誓旦旦的爱情谎言简直太容易了,只要不小心跟他怀上一次孕就可以完全试得出来。每一个失足爱上别人丈夫的姑娘大概都有这种体验。林格拿着化验单平静地从医院里出来。她想她应该把这个不幸(!)或幸(?)的消息告诉给他吗?其实根本用不着他帮忙,她也完全有能力把问题自己解决了。现代医学已经把堕胎的痛楚减小到了最低程度,那也不过是打上一针麻醉剂,如同昏死一样睡去又醒来的短短几分钟的手术过程。
但是,这个过程若是她自己独立完成了,若是不看一看她的探索对象在一次小小灾变面前的最真实而深刻的表演,那么她的仪式会结束得圆满吗?
她想他本该用他散文松松垮垮的经线,和夸夸其谈的纬线,来编织出逻辑严谨推理缜密的一出出谎言,诸如他对她的爱情海枯石烂永不变,诸如让他们结婚吧,他会永远守护她们母子平安到永远,最次也该是:他真恨不能代她去上手术台,让一切过失都由他来承担。事实上他心里也应很明白,依照林格的脾气和能力,是不会给他添太多的麻烦出来的。
可是站在她面前的这个男人为什么这么虚弱啊?他面色苍白完全脱去了熠熠生辉的黑马形态,有些犹疑,有些无奈,有些心神不定,有些自怨自艾,眼神半晌不离开那化验单,竟然不敢抬起头来用目光跟她对视儿眼。他的噪音暗哑了吗?他的喉头阻塞了吗?他平时的那些真情话语都是无聊之际用来插科打诨的吗?
林格笑了,十分沉静地笑了。她隐约地感觉到,终结的时候到了。一次赴汤蹈火凤凰涅槃的生命体验马上就会有个完结了。
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寂灭。唯有心灵不可言说。
现在,她仰倒在一张巨大的手术台上,四周围是一片刺目的苍白。她的眼睛也很空涂地自了。覆盖在她身上的那张洁白的单子应该是她的裹尸布吧?她已经被诗洞穿过了,不在乎再被无谓的散文结击伤。他没有来,他有足够的话语编织成理由不能够陪伴她来,实际上他已因嚼着不能够说出什么了。他已哑然失语,他已经神思冻结,他根本不愿经受一次小小的对他不利的失误或失败,他只会仓皇的躲避和逃逸,也许是已返身逃回了他妻子那个慈爱的怀抱,吊在那两只硕大温暖的乳房上,做浪子归家扣打门环状。
麻醉剂应该发挥作用了,可她仍旧有着敏锐的触觉,她的心是那么无比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