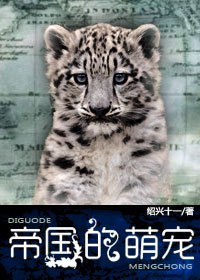慢船去中国-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声音。范妮对爷爷说:“他们也还是老样子。”
爷爷说:“他们不可能再变成别的样子。”
范妮心里动了一下,她想爷爷的意思是,她还可以变成另外一种样子的。就象离开上海的时候爷爷希望的那样,但是,现在她已经知道,爷爷所向往的脱胎换骨的艰难和痛苦,还有它的不可能。
“你那时候回上海来,是为什么?”范妮问。
“我想要做个新人。我的想法,和爱丽丝留在美国的想法差不多,想自己更新成一个新人。”爷爷说,他谨慎地看了看四周,防备有人听到他的话,“我不是不知道格林教授写的那些事,我爹爹从前过阴历年的时候,家里人都要穿中国礼服,祭祖宗。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时候,还要祭社神和关帝,这都是宁波人的传统。美国人来给爷爷拜年,也要行中国大礼。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所以,买办的家庭里不一定就全盘西化的。到我爹爹这一代,已经是在上海出生的第二代人了,但宁波人的传统还在我家保留着,我家冰箱里终年有臭冬瓜存着的。我爹爹虽然是留美学生,但他看不惯交谊舞,自己一直穿长衫。但我家一直也是好几家新式学堂的校董,这也是事实。但是,这些都不能抹杀我们家是靠害中国人发家的历史。这永远是王家不能原谅的污点。我不会因为后来共产党请我吃苦头,就象维尼那样瞎讲。”
“但是后来不是王家的航运公司也将英国人的航运公司并吞了吗,照共产党的逻辑,我们还赤手空拳地打败了洋人,为国争了光呢。”范妮依稀记起格林教授书上的一些段落,说。
“那也不能混为一谈。”爷爷坚持说,“我们的原始积累不好,就象一生下来就是怪胎一样。”
那么,爷爷认为到美国,就可以做到更新。他的失败,只是因为他选错了地方。范妮想。尽管爷爷经历过许多,可他还是天真。而经历过和鲁在一起的日子,范妮感到自己一点也不天真了。
一直到范妮吃完饭,她都没再说什么。爷爷也没说什么,他接着翻格林教授的书。范妮发现,他把奶奶的照片夹在里面,当书签用。范妮端详着奶奶的脸,她发现奶奶的脸上有一股象被抱在手上的小孩才有的那种恬然的静气,活泼和时髦的神情象恬然上的枝条和树叶一样摇曳闪烁。这是自己脸上不会有的。范妮认为,自己脸上的静气里面有怨恨,活泼里面有算计,时髦里面有势利,更象她认识的席家有个老姨太太的脸相。范妮想,这就是两个范妮的不同之处。
吃完饭,范妮对爷爷说,想要到街上去散散步。“回上海一次,总要看看上海的样子吧,哪怕是半夜,也是好的。”范妮说。
爷爷突然敏锐地飞了她一眼,他接住了这个信息。但他没有说什么,只是殷勤地合上书,收了碗筷,陪范妮一起去。
他们两个人,象从前一样。范妮突然想,奶奶要是回家来了,一定不认识这么破旧的楼梯,楼梯上还用受潮变形了的纤维板草草做成的门。她以为自己是在看《孤星血泪》。而自己要是回到奶奶在上海的时候,一定也不认识那个又新,又干净,又漂亮的art deco式的楼梯,维尼叔叔说甚至在楼梯的长窗上,他小时候的家都挂着白纱帘。自己会以为在看《雾都孤儿》。爷爷总是对维尼叔叔不以为然,对那个历史研究所的人对维尼叔叔的回忆感兴趣不以为然。然后,范妮看到花园里没有水的石头喷泉,那是爷爷对纽约的纪念。又看到弄堂口用原来的门房间改成的小裁缝店,那是范妮对上海的纪念。小裁缝店里面,在式样难看的录音机里,永远播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那是维尼叔叔最轻蔑的音乐。
第五章 No verse to the song(15)
爷爷和范妮此刻来到了红房子西餐馆的门前。即使是午夜时分,餐馆已经关门多时,他们还是走了过去。他们看到,红房子西餐馆糕点间的玻璃窗里,所有装蛋糕和面包的白铝盘子都腾空了,倒扣在柜台里。红房子西餐馆总是生意很好,新鲜的蛋糕和面包,总是当天就买完了,有时去得迟了,还要买不到。范妮依稀记起来,那个卖蛋糕的女营业员是个少妇,她烫着上海年轻女人喜欢的长波浪头发,很正式,很隆重的长波浪,将白色的小帽子轻轻压在头发上,生怕把长波浪压瘪了。她是一个矜持的人,在比较洋派的地方工作的人,总是比
在饮食店里卖生馄饨热包子的人要矜持些。在经过红房子西餐馆的时候,范妮好象闻到了食物的气味。从前,范妮第一个反映过来的,总是咖啡气味,但这次却不是。范妮第一个分辨出来的,是乡下浓汤里酸酸的番茄汁气味。红烩明虾里有番茄汁,红烩牛肉里也有番茄汁,难怪叔公说,这里的菜越来越象罗宋大菜。范妮想起来,贝贝曾经说过,要是他有钱,一定到红房子西餐馆里要一客乡下浓汤吃,那是最便宜的菜。贝贝说,他最喜欢到最贵,最有情调的地方去,哪怕只能点得起最便宜的东西,也要享受做人上人的感觉。贝贝的理想是有一天可以象巴黎从前的画家那样,在能整天混在红房子里画画,喝咖啡。“连头发里都粘着西餐馆的气味,才叫高级。”贝贝那时说。到红房子西餐馆去,对大家来说,都不算件小事情。连那里贴的毛主席语录纸,都比一般店里要好看些。更不用说在那里看到的人。范妮想,在纽约,再也找不到一个象红房子西餐馆这样的地方,看到你想看到的人,也将自己展示给别人看,彼此都是知音。纽约没有这样的地方。也许那里有,但不是为范妮这样的人准备的。别人看不懂她,她也看不懂别人。那里没有她知根知底的世界。
“那么你自己呢?你想要做什么?”范妮问。
爷爷说:“我一辈子其实都很喜欢吃面。头汤的阳春面。以后我要是有一点钱,有机会的话,就要开一家面馆,不用大的面馆,但是面烧得很地道。”
“这面馆开在中国还是美国呢?”范妮问。
“当然是中国。我也没有资格到美国去。”爷爷说着,回过头来,睁大他的眼睛,笔直地看着范妮。范妮发现,爷爷的眼睛象午夜的猫眼一样,是雪亮的。
深夜的街道上到处倒映着水洼。长乐路就在前面,梧桐后面,就是黑黢黢的新式里弄。在夜色里,她看到那里的窗台上放着花花草草,那里的阳台里,衣架上吊着衣裙,竹竿上晾着枕套和毛巾。打开的窗子都暗着,在路灯下能看到里面窗帘的浮动。在那些失修多年,或者被国营的房管所越修越坏的老房子里,在拥挤的房间中间,唯一一小块空地上,点着暗绿色的三星牌蚊香,它们散发着灰白色的烟色,还有带着烟火气的除虫菊香,从小闻它度过夏天的人,会习惯和喜欢这蚊香的气味。在那样的气味里感到安心。弄堂里的人,守着他们的梦想,欲望,和失意,都睡着了。从新式里弄出来的人总是懂得实惠,也懂得分寸和自持。那样的弄堂,虽然不如解放前那么小康,但还是聚居着各种各样的规矩人家,小心本分,机灵精明,过着实打实的日子。不过,范妮心里并不真正看得起住在那里的人,她以为自己比那里的人优越。然而,就象她会偷偷通过澳大利亚广播电台听邓丽君和刘文正的流行曲一样,她对里弄里的生活,蚊香的气味,还有那里的人世故的态度,抱着熨贴的感情。美国罐头就是一个新式里弄里出来的人,中学里的班主任也是新式里弄里出来的人,甚至家里的钢琴,也是捐给了一家开在新式里弄里的幼儿园。和这样的人相处,范妮才真正得到过爱惜。要是没有在新式里弄里活生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范妮认为自己就不会有优越和清高。
“我对自己的儿子不报希望。他们都没能上大学,没有教育。这种惩罚的意思是,让我们这样的人家,永远不再有出头的那一天。”爷爷说,“不过我不怨他们不争气。是我们家的从前拖累了他们,就象你爸爸一直认为是他拖累了你们姐妹。现在时代不同了,是摆脱的时候了。”
“你说的摆脱,就是不做王家人,连中国人也不要做,对吧?”范妮问。
“一张纸,写了擦,擦了写,就脏了。除了换一张新的纸,没有别的办法。”爷爷说。
“但是不管怎么说,你还是个中国人的脸啊。”范妮说。
“你的孩子也可能是个金发的孩子,我看鲁。卡撒特是北欧的人种,不是拉丁血统的。也许从你的孩子开始,就不是纯粹中国人的脸了。上海对他来说,就只是种传说了。”爷爷说。
范妮和爷爷都沉默下来。他们在那一刻都明白,最重要的话已经说了出来,其他什么都不用再说。范妮把手插到爷爷的臂弯里,他们拐过长乐路,来到陕西路上,远远的,他们又看到红房子西餐馆了。然后,又看到贝贝家的尖顶房子了。深夜的马路上,没有行人。路灯迷离。夜色将许多细节掩盖住了,街道变得象空中楼阁那样。他们听着自己的脚步在街上响着,好象是另外两个人正在离开他们的脚步声。
这个夏天的深夜,当爷爷和范妮在薄雾沉浮的街道上静听自己脚步的时候,王家还有一个人醒着,那就是简妮。其实,范妮还没起床的时候,简妮就已经醒了。与就是醒来,也不会马上睁开眼睛的范妮不同,简妮总是先突然睁开眼睛,然后,意识才醒来。她先看到了窗外发红的夜空中广玉兰阔大的叶子,那些叶子有着杏黄色的背面,看上去更象是枯叶。简妮吃惊地看着窗外的树叶,简妮虽然已经回到上海两年了,但在午夜梦回的时候,还是为自己身处与阿克苏的干燥黑暗截然不同的地方而迷惑,在阿克苏团部中学的教工宿舍,深夜的房间里看不到一点点光亮,更看不到树影婆娑。然后,意识回来了,她知道自己这不是在阿克苏,而是在上海的老家。四周充满了上海弄堂深处那种沉夜的寂静,空气里能闻到混杂在一起的树的气味,楼下天井里升上来的潮湿水气,阳台的竹竿上晾着过夜的衣物散发出来的洗衣粉芳香添加剂的气味。此时,简妮还在半睡半醒的时候,她觉得自己象一粒沙子被席卷而来的沙暴裹夹一般,被心里滔滔而来的无助吞没了。这种无助的感情,是简妮到现在为止的生活中最熟悉的感情,从她懂事时起,她就在父母的身上学到了,体会到了,但她自己并没有体会,她觉得自己是与其他孩子一样快乐的小孩。等她按照知青子女满十六岁可以回上海的政策,如愿回到上海,在从新疆来的火车刚刚进站,她刚刚看到月台上汹涌的人流,这种无助就象花一样,从她心里盛开出来。一离开新疆,简妮的心底里就爬满了无助,这是简妮最真实的情况,也是最大的秘密,谁也不知道,即使是她自己,也不想正视。因为她觉得这是荒唐而古怪的感情。每一次,当它从心里升起,象开水上的蒸汽,简妮就会“扑”地一口将它吹开。这样,简妮就真的醒过来了。她不是真正的午夜梦回,而是有事,她今天要给她的推荐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的武教授打电话,告诉他自己的签证情况。
第五章 No verse to the song(16)
简妮靠在枕头上,就着路灯射进房间来的光亮,看看手表。她要等到美国时间的中午时分,这是合适打电话的时间。
将要过去的一天,对简妮来说,漫长得不可置信。好不容易等到了经济担保,唯一的,但是被再次拒签。当自己大声争辩的时候,她看到一同等待签证的中国人眼睛里的慌乱,那台湾人刻薄地微笑着注视着她,但旁边的中国人却被她的宣言吓得直眨眼睛。然后,叔公去
世了,看他的样子,好象只是屏住呼吸而已。但是医生却说,这就是死。那时,她听到医生的声音,想到的却是自己,她感到自己也象医生宣布的那样,结束了,一片漆黑。其实,在对那该死的台湾人大声吼叫的那一刹那,她的眼前也是一片漆黑。然后,爸爸妈妈默默坐在窗边,什么也没有说。简妮看着他们的背影,还有老房子前的树,那是棵广玉兰,在初夏的时候开大朵的白花,将要谢的时候,那些花瓣变得焦黄,并且失水,就象惨痛的记忆那样凋败而哀伤。他们看着那些花,简妮看着他们,突然猜想,当年他们被逼到新疆去的时候,是不是也曾站在这个窗前,默默望着那棵花树不说话。这间屋,是二楼最好的一间,原先是爷爷和奶奶的卧室。简妮又想起来,自己很小的时候,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公报在晚上八点的中央电台新闻节目里广播时,他们正在新疆,爸爸妈妈站在自家窗前,打开了窗,听外面拉线广播转播的中央台八点重要新闻,他们也是这样默默的,象昏了过去的鱼。他们的背影上,总是密密麻麻写满了简妮不忍心看的失望和希望。简妮假装睡午觉,其实是不想再看到他们,她紧紧闭着眼睛,看着眼皮上的那团红色。然后,全家都听到爸爸和范妮的争吵,他们说的那些话,简妮知道全家这时都开着各自的房门,都在听。让简妮深以为耻的是,爸爸已经不对简妮的出国抱希望了,简妮和范妮一样,也在整个二楼的铜墙铁壁般的寂静里,听出了全家对自己的放弃,还有全家对范妮的希望。简妮那时也躺在自己窗前的小床上,装作继续睡觉的样子,她直挺挺地躺着,觉得自己就象是一只死河蟹,纵是活着的时候身价再高,味道再美,不能爬了,也就被抛弃了。
简妮的心里,有着范妮万万体会不到的沧桑。
但简妮到底是新疆回来的,她不光从小就体会过无助的感情,也从小就见识过即使是毫无希望,也要死命挣扎的奋争。她见到过在来往于上海和新疆的长途火车上,妈妈是怎么躺在行李架上,连滚带爬,披头散发,为了在爸爸没把带到新疆的包裹行李拿上车前,先抢好放行李的地盘。她见到过爸爸躺在硬座的椅子底下,脸枕在一堆垃圾旁边打盹,她自己,就是爸爸妈妈和他们的新疆同事们从车窗上塞进车厢里的,因为整个过道上都挤满了人,根本上不去了,当她被人七手八脚举着塞进臭气熏天的车厢里时,她看到过一个年轻的阿姨被人从月台上挤了下去,掉到火车下面去了。在范妮的哭声里,简妮决定,一定要给武教授打个电话,告诉他,获得他的同情。
简妮与武教授认识,是在人民公园的英语角。武教授来上海为美国公司做市场评估,他听说在英语角可以和普通的上海青年交流,就找了一个时间去看。那天,正好简妮也去英语角。事情也是凑巧,当时和武教授一起去的,还有几个白人,英语角的上海人一拥而上,抢着跟那些白人说话,将中国南方人长相的武教授渐渐挤到简妮的身边。简妮闻到了他身上的香味,是叔公从香港带回来的剃须水的香味,她看了他一眼,正好看到他被冷落以后脸上自嘲的微笑,于是,简妮向他挑了挑眉毛,表示同感。于是,他们就开始交谈起来。
“上海的小市民就是这样的,我抱歉。”简妮说。
“没有,没有,”武教授笑嘻嘻地摇头,“全世界的小市民都是这样的。看到上海的小市民和全世界的一样,我才感到高兴。要不然这里反倒不象人间。”武教授说。
武教授长着一张鼓舞人心的热情的脸,让简妮心里感到温暖和希望。当武教授告诉她,自己是商学院的教授时,简妮马上说:“对的,我就是准备去读商科的。” 当时,她只是想让武教授感到志同道合的亲切,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