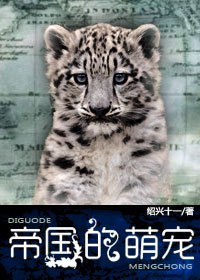慢船去中国-第5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很多目光落到她身上,那是在看她的美式装扮,那是上海人精明而饥渴的目光,简妮意识到了。简妮的步子轻盈起来,她脸上浮现出喜洋洋的友善和好奇,还有天真,就象个真正的美国人。她看到同一架飞机上的美国人也是这么做的。
这时,简妮看到一个穿简单套装的女子,手里举着写自己名字的纸牌:〃MS。 JENNY WANG。”
“嗨!。”简妮走过去,招呼她,“我是简妮王,从挪顿兄弟公司的纽约总部来。”
“你好,我是外事科的小刘。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工作。”她犹豫了一下,也跟着简妮说起了英文,“一路上还好吗?”
“好啊,非常好。”简妮说着,深深喘了口气,“只是一出机舱就不行了,空气里真湿啊,觉得喘不过气来。”
刘小姐笑了:“这是地道的上海气候,雨季的时候,就是这样湿湿的。”她的英文让简妮想起自己的交大时代,她在 th 上的上海口音让简妮想起了自己的,同学们的,老师的,和爸爸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将舌尖放到齿间发 th 时,都是笨拙的,所以发出来的那个音也是笨拙的。很多人都偷懒,将舌尖随便一顶,就算了。刘小姐学英文的时候,一定也是个用功学生,努力地发出 th 的音。随着这个音,简妮想起自己苦读英文的过去,甚至初到美国的时候。海尔曼教授被汗水浸湿的衬衣后背。简妮奇怪地想,自己竟然一点也没觉得高兴,反而是厌恶的。她厌恶听到这种口音的英文。
刘小姐将简妮引到大厅外面,让简妮在出租车站点边上等一等,自己去停车场,叫厂里的车开过来。
机场外面到处乱烘烘的,太阳被闷在厚而灰白的云层里,空气中好象有层薄雾。简妮觉得脸和脖子上有点黏糊。出租车在排队,乘客们拖着行李左奔右突,到处都是横冲直撞,大声说话的人们,还有满脸诈色,堵在门口兜生意的出租车司机,柏油路面上,有一滩滩出租车漏下的汽油污渍,食品店的玻璃门上,能看到手指的污痕。有人撞到了简妮的身体。“遗憾的。”简妮说着往旁边让了让,但那个人连看也没有看简妮一眼,却挤过简妮让出的路,向马路对面的停车场走过去。简妮刚想站回原来的地方,但又有一个人撞了简妮一下,想要拖着他的行李箱,从简妮让出来的地方过去。简妮突然怒火中烧,她侧过肩膀,也狠狠地撞了那人一下,将那人撞得往边上一歪。简妮心里一紧,准备好道歉。但那个人将自己身体移正,象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继续挤过简妮的身边,向前走去。简妮又惊又怒,她刚站定,又有个人从后面重重擦到了简妮的背包。简妮觉得自己的寒毛一下子都炸了起来。她回过头去,对那人怒目而视。她没想到,那个人也正张口指责她:“你拿那么许多的箱子挡在路上,别人不要走路啦。”那是个年轻的女孩,穿着一条象范妮那样的蓬蓬裙,手里挽了一个瓦伦提诺的白皮包,将眉毛拔得细细的,眉眼很凌厉。
“你最好打招呼,但不要碰到我和我的东西。这是我的东西,你懂哇?你不能随便碰别人的东西和别人的身体,你懂哇!”简妮对那女孩说,她说的是上海话,被迫的,愤怒的,简妮有点语无伦次。
“噢哟,象真的一样。你不挡我的路,我要碰你做什么?你当你那么香啊?”那个女孩丢下一句话,轻盈地走开去。
好在这时,刘小姐带着工厂的车来了,她将肩膀探在车窗外,向简妮挥手。“母狗。”简妮忍不住低声骂。
他们好容易将简妮带来的几只大箱子都安顿到车上,坐定。简妮望着窗外混乱的人流和车流,到处都能看到被粗暴挤压过的行李箱和旅途中格外卑琐的人脸。她想起了在世贸中心楼下的地铁站里那些沉默着迅疾向前的人们,还有在耳边简约的一声“Excuse me”,然后尽量让过别人的身体,尊严的样子。简妮想,纽约人的冷漠里有着尊严,而上海人的冷漠里却是卑琐的。
第十章 买办王(3)
“这真是个不可置信的乱世。”简妮忍不住说。她觉得自己就象一块豆腐掉进煤堆里。她预见到自己对上海大概会不适应,但还是没想到,心里会有这么大的失落。她简直觉得自己被打了一闷棍似的。
“我们去哪里?”刘小姐问。
“去我爷爷家,这是地址。”简妮将写着爷爷家地址的小条子交给刘小姐,“我们家有十几家亲戚在美国各地,就剩下我爷爷一家留在上海。这次我来,大家都给他带礼物来。”
偏偏刘小姐不知趣,她说:“研杵先生说,他的新秘书将能听得懂上海话,而且就是从上海出去的。王小姐其实也是阿拉上海人吧?”她说着,就转成了上海话。
“I Was。”简妮勉强回答说。
“噢。”刘小姐盯了简妮一眼,“你的意思是,你过去是上海人。”
简妮没有回答她,她甚至没有再看刘小姐的脸。
简妮看着窗外,汽车离开虹桥机场,进入市区。简妮又看到自己熟悉的景物,灰色的火柴盒式的房子,是七十年代的式样,门窗涂的是鲜绿色的油漆,带着农民的审美。绿叶婆娑的梧桐树遮暗了街道,在梧桐树叉上,有沿街人家晾着的衣物。武康路上红砖的旧公寓,让简妮想起了靠近哈雷姆区的旧公寓楼,在如今风尘仆仆的旧阳台上,破旧的搪瓷脸盆里养着宝石花和仙人掌,甚至仙人掌还开了大朵的黄花。简妮又看到漆着蓝色横线的 26 路公交车,它带着尖利的刹车声向车站蠕动着靠过去,售票员将手从车窗里伸出来,乓乓有声地拍打洋铁皮的车身,提醒车站上的乘客不要向前挤。简妮想起来,自己刚回上海时,爸爸请爷爷教自己如何挤车的事。爷爷说:“我在江南造船厂工作三十年,从来都是让挤我的人先上,我不懂怎么与别人挤。”开始,简妮觉得那是爷爷的“雷锋精神”,当自己不得不象猴子上树那样挤在人群中的时候,简妮才理解到,那是因为爷爷不肯变得如此不堪入目,所以才不肯与人挤拼。然后,简妮想起了婶婆衬托在蓝色软缎上那微微发紫的,一丝不苟的雪白卷发。汽车经过淮海中路时,她看到第二食品商店的橱窗里放着雀巢速溶咖啡的标志,还有美国的气味,她想起来在国际市场营销学课上说到过的,在盛产新鲜橘汁的南美怎样打开气味的市场事。简妮记得自己当时说,中国市场对一切外来的东西都是饥渴的,如干燥的海绵。汽车离家里已经很近,高大的梧桐树后面,能看到破旧的洋房,只种着最低档花木的小街心花园,还有到晚上才开门的小酒吧和咖啡馆。简妮又感受到了淮海中路那种陪着小心,又藏着不屑的风格。她没想到上海竟然这样捉襟见肘,简妮的心紧缩起来,象石头那样又冷又硬。
甚至比记忆里的上海更脏,更乱,更粗鲁。她渐渐发现在那熟悉的旧街景里,有许多裸露在外的挖烂马路,浮尘飞扬的建筑工地,许多街区的房子外墙上都用红油漆写着巨大的“拆”字,触目惊心。简妮想起来小时候在新疆,法院贴告示,就在死刑犯的名字上用红笔这样圈了。远远的,能看到有工人抡着长柄铁锤,象雷电华电影公司出品的电影开头那样,曲线优美地击碎租界时代带着西化风格的旧房子。从工地源源不断开出的卡车,不停地将烂泥摇晃到马路上,被迫经过的人们,象小鸡一样在烂泥中间跳着,躲避着。“这不是乱世,又是什么。”简妮心里说,灿烂阳光下一尘不染的美国草坡浮现在她的心里。
车子渐渐逼近爷爷家的小马路,远远的,看到弄堂口了。简妮突然看到自家弄堂口有熟悉的身影,那是爸爸妈妈。她没让他们去机场接,她跟他们说,美国公司会派车去接她的。爸爸还在电话里笑,说:“我们简妮现在是衣锦还乡了。美国公司派车去接飞机。”她没想到,爸爸妈妈会在弄堂口等着自己。爸爸撑了一个木头拐杖,他的肩膀象落汤鸡那样耸着,也许因为撑拐的关系,他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在唐人街上的露天摊上,十元各自的,买一个获得一个。简妮心惊肉跳地去看他的脚上,果然,他穿了白色的运动鞋, Adidas 的。妈妈穿了出客时穿的好衣服,简妮第一次发现妈妈那件最重要的哔叽呢外套,实在很是呆板难看。能看出来,妈妈甚至用了些口红,但那口红反而点明了她一脸的风霜。他们俩郑重其事地站在弄堂口,翘首以盼。简妮将自己的头向后仰了仰,恨不得自己是在梦里。司机对这些小马路并不熟,眼见得已经开到弄堂口了,却拐到另一条小马路上。简妮送了一口气,听任他和刘小姐一边对地图一边找,不发一言。
但他们的车很快又转了回来,他们在爸爸妈妈怀疑的目光里缓缓开进弄堂里,停下。
简妮赶快卸下自己的箱子,她听到弄堂口的小裁缝叫:“你家小新疆回来了!”
她看到爸爸妈妈急急绕过满地发黄的广玉兰落英向她赶来,妈妈扶着爸爸,爸爸却摆动手肘,松开妈妈的手,示意妈妈先跑。简妮简直不能看爸爸走路时的样子,他突然变得那么慢,那么小心,他在那场车祸中还被撞断过锁骨,所以现在他的肩膀斜了,他整个人都有点象快要散架的椅子,吱吱哑哑地响着,带着不堪一击的僵硬。妈妈的衣服让简妮想起来自己离开上海的那天,妈妈就是穿着它去机场送她的,那件衣服是妈妈最重要的衣服,是外婆给妈妈在“朋街”定做的上衣,用的是五十年代“朋街”店里最后一批真正的英国呢存货。他们一定已经在弄堂里宣传过了,所以,三三两两的邻居,都从后门出来了。他们中的有些人,曾经管简妮叫“小新疆。”简妮从小就不喜欢她们,她们最喜欢问范妮奇怪的问题,比如:是不是新疆人一辈子只洗三次澡,每个人都在鞋子里插着尖刀。她们的脸很刺激地皱成一团,等着她的回答,不论她回答什么,她们都用被吓了一大跳的表情接受,将嘴缩起来,“丝丝”地吸着气,好象听到的永远是最不可思议的答案。
第十章 买办王(4)
妈妈叫:“简妮啊!”简妮远远望着,竟然不是阳光晃白了妈妈的头发,她的头发是真的白了。妈妈整个人,也象旧娃娃一样,褪了色,白的地方不白,黑的地方也不黑了。
简妮放下箱子,绕过车和刘小姐,向爸爸妈妈跑去。
她过去抱住爸爸妈妈,消毒水的气味扑面而来,逼得简妮不得不侧过脸去,她脸腮边上
的寒毛一根根地竖了起来,她知道这种消毒水气味是由自己的心理创伤,在美国时候就知道了,但她却控制不住自己。她与爸爸贴了贴脸,就象与婶婆见面那样。简妮拼命忍着,才没从爸爸妈妈手臂里抽出身去。当挪顿公司的车在弄堂里那口被水泥填掉的井前,勉强掉了头,要离开的时候,简妮心里真想跟他们一起走。从美国带来的那些箱子竖在湿漉漉的弄堂里,把手上吊着 JFK 机场红色的Heavy警告牌,鲜艳夺目,就象安徒生童话里所描写的,从天堂落下来的碎片。
二楼窗台上,还吊着用竹片做的十字架,只是它变得发黑了。那上面还晾着妈妈水红色的棉毛裤,裤裆长得不可思议,只是它褪色了,象开败了的月季花。爷爷蓝色的确良咔叽的中山装挂在铁丝做的衣架上。为了保持它的平整,在湿的时候就把衣扣都扣上。即使是洗过了,晾在衣架上,那衣服还是保持了颓唐而不甘的样子,那就是爷爷的样子。
厨房的下水道已经老得不能用了,所以在墙上挖了个洞,将下水道的管子通出去。那管子节约地做到接近地面的地方就断开了,厨房的污水就直接流到外墙上,再流到下水道里。无风的时候,那条露天的下水道在后门那里散发着带着油腻的淡淡污浊之气。有太阳的时候,能看到在墙面上沾着已经干结了的鱼鳞,花涟鱼,青鱼,或者黄鱼的,它们在脏脏的墙面上闪闪发光。从第一次看到这房子,简妮就觉得这房子旧得不可救药,她没想到,它们还能继续旧下去,而且越来越旧,越来越脏。
天井里那个长满青苔的西班牙式喷泉上搭着底楼人家的抹布,简妮这时看懂了它的身世,也看懂了它的脏。那石头应该是微微发黄的,能看到里面有星星点点云母的微光。那边缘应该挂着清亮的水流,象透明的帘子一样。简妮看到,搭在喷泉上的抹布是一件穿旧的汗衫,肩背上大大小小,破洞连连。
爷爷站在楼梯口候着简妮,他拍拍她的肩膀,对埋头将箱子搬进门槛的简妮说:“当心。”简妮将头埋着,表面是奋力搬东西,实际上更是怕看到爷爷眼睛里的失望,他希望简妮永远都不要再回上海了,他还希望简妮永远不要再与王家有什么干系。但简妮拂了他的意。简妮决定要回上海的时候,是理直气壮的,但她见着爷爷那阴影重重的身影时,心里咯噔一跳,她此刻不能说爷爷肯定错了。甚至她想,也许爷爷当初从美国回上海的悲剧,就要在自己身上重演。要是当初爷爷没有理想,不拂逆曾祖的意思,他也不必回上海。要是爷爷知道前途将是万丈深渊,他也不会回上海。简妮相信爷爷和自己一样,当初都是干干净净回上海来的,都是一心要追随自己的天命,带着美国教给自己满怀的天真。
“爷爷,我的签证是随时可以回美国去的。”简妮放下箱子,说,“我的合同是六个月的,也许我六个月以后就会离开的。”简妮第一次想,这六个月也是漫长的啊。
“那就好。”爷爷应道。
进得家门,简妮吃惊地看到,爷爷房间里坐着一个男孩,正伸着头向她笑着招呼,手里握着一卷书。爷爷现在居然也在家里收了学生,教英文。那个男孩,就是准备暑假签证去美国读书的医大学生。当年,爷爷连自己家的孩子都不肯教,现在倒从外面收学生回来,让简妮吃惊不小。简妮看了看爷爷,他脸上还与从前一样沉默。
“Hey!”简妮冲男孩挥挥手, 〃What‘s up?〃
“Plenty well。”那男孩响亮地回答,到底是爷爷的学生,听上去没有跟磁带学出来的那种做作的声调。
爷爷相帮着简妮将箱子搬到为她准备下的房间,那男孩见状连忙跑出来接下爷爷手里的箱子,他和简妮合力抬着箱子,问:“你是从美国回来的?”他指了指箱子把手上 〃Heavy〃 警告下面的 JFK ,表示自己知道这缩写的意思。
“是的。”简妮答道。
“你家好容易团圆,是不是我改日子再来?”男孩问跟进来的爷爷。
“不必。”爷爷说。
简妮听到爷爷的英文,想起了婶婆,他们的口音真是相象,一样的清晰而缓慢,咬文嚼字的。那男孩脸上谦恭有礼,敬爱有加的微笑,让她想到自己对武教授的微笑。她太熟悉那样的微笑了。他们这样的孩子,心里本能地相信,这样的忘年交,能象一根靠美丽微笑点燃的道火索,使自己一飞冲天。爷爷说话的声音,因为说了英文的缘故突然变化了,那声音轻柔快速,不象是一个老人的。
“老莫的第二个春天。”朗尼叔叔从自己房间里踱出来,他的眼眶下有一圈很深的棕黑色,看上去脸色阴沉晦暗,他望望爷爷的背影,对简妮刻薄地说了个台湾电影的名字。简妮却在爷爷的背影里真的看到了依稀的矫健,婶婆照片夹子里的那个唱老生的青年身影。爸爸妈妈埋头为简妮将东西收拾到她的房间里,不搭朗尼叔叔的茬。爸爸说:〃我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