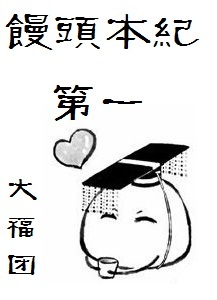权臣本纪-第1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叫什么花?”
小姑娘仰起面来,十二、三岁的模样,一双眼睛烟白分明,怯生生看他一眼,旋即垂首红着脸道:“晚香玉。”说罢扭身朝屋里跑走了。
成去非随后即入,只见一苍然老妪正缓缓摇着纺车,那小姑娘见他进来,附在老人耳畔说了句什么,老人颤颤巍巍起身,眯起眼问道:
“请问这位公子是从何处来?”
成去非沉默片刻,自袖管中掏出那封书函,轻轻抚平一阵,那上头的血迹早已干涸乌烟,而刀鸣马嘶犹在耳畔,只是年轻人的尸骨葬于他乡,血肉应早不在人间,一抔黄土,无墓无碑,碧血丹心,不是小武一人的,而是那无数平凡又不平凡的将士们的。
“老夫人,”成去非只觉含了满口的鲜血,几乎张不开嘴,小武的家书是别人代劳而写,他并不识字,亦不会写字,成去非抬首看了看老人那一双泪眼,只把信塞至老人手中,低声道:
“这是小武给您的家书,我是他的长官,却……”
要如何告诉一位母亲,她的孩儿再也不会回来,只因他的功业,要踩着无数尸骨而上。而她的孩儿,不过是籍籍无名中的普通一员。倘死去的是他成去非,那么史册上会给他空出一笔,记下他的姓名,那么无数个小武,不过是史册上的一串数字而已,成去非不忍不能相看眼前母亲的失望与泪水,却只听那老妇人道:
“原来是将军,他回不来了,是吧?”
成去非道:“我没能把他带回给您,是我的罪过……”
老人干枯的眼中忽涌出两道浊泪,她依然平静:“他为国而死,我没什么好说的,请将军不要自责。”说罢冲那女孩子柔声吩咐了,“阿宝,去给将军弄碗水喝。”
成去非心头陡然狠狠一酸,不仅仅为那年轻人的舍生忘死,更为老母亲的深明大义。这便是国朝的母亲,这便是国朝的儿郎,国难当头,文不爱钱,武不惧死,这本该是国朝的理想,是苍生的理想,然而,终而终之,这份理想,也许注定只是一份理想。
“将军请喝水。”阿宝细细的声音响起,成去非双手接了过来,女孩子眼睛虽清亮,可面皮却是微微泛黄,并无青春的红润,他看了看阿宝,一时出神,阿宝见他迟迟不喝,低首搓着衣角小声道:
“我把碗洗了五遍。”
成去非恍然大悟,忙一口饮尽,把碗递还给她:“阿宝,你家的水很甜,我方才只是想事情,并没有其他意思。”阿宝羞赧点点头,乖顺地仍退回原位。
“这是小武的抚恤,请老夫人收好。”成去非呈上相应钱财,老妇人朝阿宝示意了,阿宝上前接过,置放于窗前的小盒中,听那边老妇人已安排道:
“阿宝,你去送将军。”
成去非默默躬身见礼,再多的言辞换不来鲜活的生命,他亦无意多逗留。阿宝细长的影子看起来伶仃可怜,成去非正欲同她告别,阿宝忽道:
“将军,出去打仗的人如果不能回来了,就会给他的家人钱财吗?”
成去非应道:“是的。”
阿宝眼圈一红:“如果不给,是不是打仗的人还是会回来的?”
话是小姑娘反着推的,成去非不知该如何作答,忽察觉不对:“阿宝,你这是何意?”
“我爹爹三年前也是去并州,我跟祖母小叔叔一直等他,可没人给我家送钱财,也没等到爹爹回来,爹爹是不是迷了路呀?”
阿宝已开始抽噎,成去非突然怔住,似在思索:“小武就是你的小叔叔?”阿宝含泪点头,成去非又问,“你祖母只有你爹爹和你小叔叔两个孩儿?”阿宝再次点头,成去非心底发紧,望了阿宝片刻,小姑娘仍梳着双髻,满面通红,那朵晚香玉早不知何时被碾于脚下,零落成泥,正如她的爹爹,她的小叔叔,一样转眼成灰。
他身上朝服未除,腰间仍佩着水苍玉,遂解下塞给她:“阿宝,好孩子,好好照顾你的祖母罢。”
说着不等阿宝推辞拒绝,折身大步去了,徒留阿宝愣在原地,捏着那块美玉,再次嘤嘤哭泣了起来。
成去非回到乌衣巷时,虞府下的帖子刚到,高僧支林赴虞家之宴,大司徒这是请他过去与会。大司徒曾多次赴庐山拜会支林,如今支林应其所邀算是礼尚往来,支林已于宫中讲学三日,天子、太后及后宫女眷,无一不参会聆听高僧讲道,这接下来,便轮到各大世家了。
屋里已点了灯,成去非立在屏风后边换衣裳边吩咐赵器:
“我不回帖子了,你去虞府知会一声,说我马上就到。”
赵器知他并无此种喜好,不知这回为何答应得如此爽利,正欲领命而去,成去非又喊住他:“找个婢子问问殿下的意思,帖子上请了殿下。”
虞府既请到高僧,他府上本就喜谈玄说易,常高朋满座,今晚定更是宾客如织,既如此,殿下虽是金枝玉叶,但终归是女子,此等场合,殿下要如何出席呢?赵器摇首叹气,匆匆去了。
第191章
殿下的精神十分好。
殿下的神情却依然冰冷如常,她此时装扮绝非符合帝国长公主的身份; 亦不符乌衣巷成府女主人的身份。殿下看起来; 更像是个比丘尼; 成去非不无怪异地想到此,他于是仍以君臣之礼上前拜道:
“殿下,是要与我同行么?”
明芷点点头:“不错。”
有一瞬的静默,成去非伸出手挽她上车:“殿下,请。”明芷似乎略略吃了一惊; 却并未言说; 只借助他的臂力,其间感觉到那犹如生铁一般的强硬来; 这正恰如他本人; 那么这样的一个人,怎会是真心在自己面前伏低做小?明芷的眉间,有轻微讽刺的味道,一闪而逝。
不算宽裕的空间中,夫妻二人相对而坐,彼此维持着于各自来说皆未逾礼的姿态。他的君主; 所行已渐次让他麻木; 尽管会有那么一瞬引起他情绪上的不悦;她的臣子; 双颊不似往日一般有神采,尽管他的神采不过一层冷霜而已,明芷心底忽涌起一丝怜悯:她的臣子,她的夫君; 戴星而出,载月而归,夜而忘寐,昼而忘食。所求不可得,所念不可见,一颗心拖泥带水,不过亦是芸芸众生中挣扎的可怜人罢了,那么,此刻,他八风不动的神态,终究惹得明芷微微一哂,前所未有地先开了口:
“大公子平日里间不容瞬,此番前往,是祛衣受业?还是只为发难?”
成去非未有丝毫迟疑,立即答道:“发难的不是我,而是殿下。”
明芷竟不否认:“我的发难,不过一时无聊揣度,而大公子的发难,则定是有备而来。”
“难得殿下亦有无聊时刻,”成去非看着那双美丽的冰洞,唇角勾出一个模糊的弧度,他似笑非笑,“臣也是一时课语讹言,还请殿下宽恕。”
明芷不置可否,她回敬一丝同样若有似无的笑意:“大公子如今功成名遂,如日中天,不敢不宽恕,痴鼠拖姜,吾不行矣。”
“殿下不必泄气,臣只是个俗人,而殿下,已然成佛。”成去非道,明芷错了错目,待车驾缓缓而停,才点头道:“大公子恭维起人,让人害怕,昨日我闲来翻书,恰读到孟子所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只是不知今晚得道者是谁,失道者又是谁?大公子不好奇么?”
明芷不等他搀扶,自己下了车,脑中再回想起那句“殿下不必泄气”,侧身看了看他,夜色中眸光闪烁,“方才那些话,你放肆太过了,你既还称我一声‘殿下’,便莫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你这个人,说话做事不向来不矜不盈的么?绳愆纠缪不是你一向的准则么?”说罢也不理会成去非是何神情,正欲拾阶而上,忽又扭头补道:
“险些忘记了,你如今有回天之势,是故如此出言无状。不过火尽灰冷,亦是常情。”
突袭一般的诘责,殿下原有如此辩口利辞,成去非默默目送她身影远去,才撩袍举步进了虞府。
月与烛光,荧荧点点,称的是良宵。
宴会设在府上楠木楼中,待成去非到时,众人已把殿下迎到上坐,见他现身,彼此寒暄一番,主宾仍依惯例入座。
支林大师本河南陈留人,先帝年间渡江而来,修佛二十五载,亦精通老庄,常与士人交游,谈玄论道,其人端正严肃,内通佛理,外善群书,是大族们的座上宾,天家亦深爱之。
至于成去非上一回听他讲佛法,已是身在会稽数十载前的旧事了。大师这些年于庐山,背山临流,营造佛龛,又请画工图绘天竺佛影,撰写五篇铭文,供人礼拜,亦是无量功业。
易体玄远,正是名士们开口的最佳辩题。大师亦能由此发端,很快融入其中,成去非凝视大师之余,瞥见殿下,犹如老僧入定般,两眼说不出的空茫无物,殿下在想什么,关心什么,他是难以探测的,就好比方才那一阵咄咄逼人的辞锋,从天而降,前无兆,后无果,起合遽然,好在四周传来的争议打断了成去非的思绪:
“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然总有未形之理,存乎象卦卜筮之外。唯有推而行之,加以通彻了悟,方可极天下之赜。”
循声望过去,是韦家子弟,成去非欠了欠身子,忽就想起了韦少连,他凌然呵斥年轻人的场景历历在目,年轻人每每欲反驳却终落在下风的丧气样也犹在眼前,年轻人留在了风沙侵人的边关,自然同眼前华宴再无瓜葛。
“倒不如化而裁之,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至于象外之意,固非人所能及,强力而致,究有何益?”原是顾曙已在笑驳韦行霈,说得众人一怔,阿灰果清谈佳手,象卦之外的未形之理,几语被他就此点破。
韦行霈一时难以反驳,便沉心细细揣摩,旁人三两低首窃窃私议着,大司徒见争执有了定论,唯恐冷落支林,遂把话题渐渐引向佛理,众人皆重支林修行,顾曙含笑率先开口相问:
“吾辈曾就形神之别激辩,愿听大师高论,以解心中之惑。”
“形在神在,形灭则神灭,不正是你我在此及时行乐的缘由么?”有少年子弟悠然笑道,“夫禀气极于一生,生尽则消液而同无,神虽妙物,故是阴阳之所化耳,既化而为生,又化而为死,既聚而为始,又散而为终。如同薪火,木在则燃,木尽则灰灭。”尾音颇重,顾曙名讳正在其间,少年人顺带打趣了年轻的顾尚书。
顾曙只是笑,而坐上支林则目光深邃,从容应对起来:
“神也者,圆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假数而非数,故数尽而不穷。”
众人顿时听出柳暗花明又一感来,只听支林继续道:“公子既以薪火喻,便说薪火。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前薪非后薪,则知指穷之术妙。前形非后形,则悟情数之感深。”
话至此,众人一阵喟叹,直言大师此番妙论实在让人茅塞顿开。支林面上淡然,满面慈悲相,只含笑不语。
“槛内人有话想请教大师。”成去非骤然发声,引得众人瞩目不已,这种场合他素来寡言,众人皆知他不喜清议,此刻竟有话要说,不过大公子并非不精于此道,当日亦是夺戴凭席的人物,便都存了好奇看向他这边。
“沙门抗礼至尊,正是情不所容,一代大事,宜共论尽之。”
语调不疾不徐,众人一片哗然,本朝有沙门不敬王者故事,支林大师在宫中见天子是无须行君臣之礼的。虞归尘亦稍有讶异,成伯渊此言太过直白,果真,殿下冷冷的目光已扫将过来。
沙门是否需敬王者,早在宗皇帝年间便有一次争执,后不了了之,仍依旧例,沙门无须敬白衣同王者。眼下成去非忽又重提旧事,众人心底一时揣测种种,未免以为大公子于此地发此难,犹如松下喝道,对花啜茶,却听支林已道:
“出家乃方外之宾,迹绝于物,愿协助帝王,教化百姓,故于内虽不重自然亲情,而不违背孝道,于外虽不跪帝王,而不失敬意。”
如此一番滴水不露的话,深得诸人赞赏,虞仲素笑着把话接过去:“良以道在则贵,不以人为轻重,大师正解。”
成去非扬眉一笑:“大司徒既言以道为贵,不如就说这以道为贵。”
席间寂寂,众人皆聚精会神准备一听大公子如何反驳,他肯跟人辩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江左无人不知大公子向来喜欢身体力行,口舌之利,不屑争矣。虞仲素等人亦想趁此窥探成去非如今学识,有意引话,支林则只是侧耳倾听神情,昔日少年人,今日权重者,乌衣巷的大公子既有心要牵扯佛家与世俗伦理之争,亦不得不小心周旋,以保佛家清誉。
“圣人之道,道之极也。君臣之敬,愈墩于礼,如此,沙门不敬,岂得以道在为贵?”成去非轻描淡写二三语,一时竟无人能接话,支林面色平和望着他,目光则幽邃如潭:
“常以为道法与名教,如来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此语一出,众人皆察觉出不同寻常来,有人高声应道:“愿闻大师详解。”
“寻道,一则有先相全而后相离,譬如史载诸多有志于建功立业者,成事方式并不尽相同。二则先相离而后相合,起点虽不同,但目的却仍是一样,两者归宿终究一样。世人只见相异,而不睹其后之相同,如是也。”支林回应巧妙,言之在理,众人感叹之余不免又暗自思想:道理已如此通透,大公子该如何应对?
在众人的注目之下,成去非只是沉静笑道:“大师高妙,去非不能再驳一二。”他忽就念及琬宁来,他的小娘子,兰姿蕙质,她倘是在,定会比他说的精彩,驳的有力,然而他亦深知的是,她过于羞怯的性情却亦注定她只能是他的伴侣,而非同袍。
在座嘉宾不能不惊诧,因这算来是乌衣巷大公子第一次如此放刁把滥,又是第一次如此轻易不经心地拜倒辕门,这阵哗然风起波荡漫过人群,热忱的看客们,多少有些失望,乌衣巷的大公子,实不该草草两个回合就此作罢,虽然这其间的三言两语,亦足够引得众人言三语四,细细品味。
他的才辩不止于此,而才辩背后,所隐藏的,是刚得录尚书事大权的年轻人,在看清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尘之义,父子之情的三宝弟子们,绝不会因一次口舌之会,便肯改弦更张。
成去非不再多发一言,坐上的殿下,仍未发一言,这对世间尊荣的夫妇,座位间的距离相隔并不远,而中间隔着的却是无我相无人相的佛面佛心,一切墙壁瓦石,隔断了成去非同她,同坐中宾客的丝缕关联。
不过这并不要紧,他所恋慕的人,会在家中等他归来,会在他酝酿风暴之际的当下与未来,一直等待、陪伴。
是故,众人很快发觉乌衣巷的大公子依然如昔地沉默下去,那专注的神情,竟也像是真的在认真聆听着、领受着,来自于佛法的高深无际。
第192章
离席后成去非本欲问及几年前并州战事的善后之责,然彼时大将军尚在; 台阁诸事怠惰因循; 这笔账算来不能推到阿灰身上; 游移半晌,还是同阿灰商议了此事。阿灰听言,心底苦笑,这一事倘认真查究起来,并不容易。大将军身死; 当是国朝朝局分水岭; 前情后事,不宜并为一谈; 但并州仍是国朝的并州; 兵士仍是国朝的兵士,如此参差错落,交横绸缪,说到底,要紧处不过在于钱财。
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