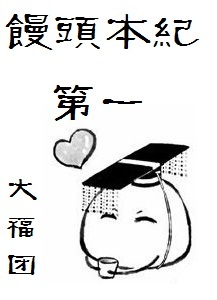权臣本纪-第8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芳,扬声道:
“把百姓先往都水衙门安置,那里地势高!”随即又去寻赵器,“赵器!你去!就说是奉我的手谕!”话说间忽瞧见两个家仆竟也跟来了,知道是福伯的意思,这边赵器有些犹豫:“府衙不肯开门怎么办?”
成去非面上一怒:“他敢!不开门就往死里砸!阿大!你们跟着赵器一起去!”
见赵器还愣着,明白他是在担心自己,遂吼了一声:“还杵在这儿?!”赵器只得去协同步芳安顿百姓,没走几步,一阵狂风扑来,竟携起数丈高的巨浪,越过上头城墙,劈头盖脸往人身上直直砸下来,瞬间冲散众人,那些尚未出口的惊呼淹没在滔滔水中,成去非只觉眼前一烟,咸涩的海水涌了满口满鼻,这一阵彻底击垮了他,整个人重心不稳,很快被卷进洪流之中,好在他水性极佳,扯下那碍事的蓑衣,三两下探出头来往北游去,半途忽觉遇阻,一团东西挡在胸膛处,他只能顺势捞了起来,努力睁眼辨认,竟是一具男婴,孩子早溺死其间,小脸涨紫,没了气息,成去非看得陡然心惊,却也只能松手任由那具小小的尸体漂荡去了。
前头的哭声不绝,突如其来的浪头怕是溺死不少人,成去非艰难拨开四处飘来的农家器物,水中阻力大,又兼大风,他好不易重回高处,脑中忽碾过一道光,捉住身边一看似官吏模样的人:
“去‘入汉楼’!把人往那里送一批!”
“大公子!”步芳不知怎的来到了跟前,竟带着一缕哭腔,“吓死小人了!小人还以为……”
“你婆婆妈妈做什么!”成去非骂了一句,“赶紧带人走啊!”说着回首望了一眼南边城墙,咬牙道,“你找几个人,去把都水台那帮子人从被窝里给我拎出来!就说我在这等着他们!”
石头城这边海水倒灌是常灾,官员们的家宅自然都建在高处……成去非正恨恨想着,只听又是一阵巨响,人群中传来一声声惊呼“城门掉啦!是城门!”
正喊着,只见南头城墙那边一排排高树,忽被飓风连根拔起,烟黢黢一片,整株整株栽倒水中,惊得众人挤作一团,根本来不及躲闪,这些树下来,又不知砸死了多少人!
成去非眼前蒙着白乎乎的轻翳,方才他也只是险险避开这一劫,耳中尽是嘶哑的惨叫,水流仍将人们拨得东歪西倒,前头步芳等人正在奋力高呼聚集着百姓,成去非这会终想起那些商船来,知道定是救不得了,脑中一时晕眩,加上这半日的风吹雨打,竟有些站不稳。
不知过了多久,耳畔人声渐熄,风小了许多,雨势也散尽大半,成去非救起一顺水挣扎的女童,却寻不到她父母人家,只得一直搂在胸口,低声安慰那哇哇乱哭的稚子:“阿囡莫哭……”
再抬首间,终见到一队火把急急朝这边赶来,成去非正想着是不是都水台的人,只觉怀中一空,耳畔忽响起妇人撕心裂肺的哀叫,原这妇人早一把将孩子从自己怀中抢了过去,死死抱紧了上下胡乱扒摸着:“我的儿,我的儿……”妇人口中翻来覆去就这一句,成去非心下稍稍轻松,却见果真是都水台的人近了身。
都水台的长官都水监本听闻府衙被砸,涌进四方百姓,自己的府邸亦是被人破门而入,搞得一肚子火,当知道成去非竟亲自冒雨来监察灾情,吓得忙整了队伍,一路奔来,此刻借着火光,险些没认出成去非:
眼前人黄扑扑一张脸上满是泥浆,头冠早不知掉到哪里去了,身子亦湿得精透,已看不出本来面目的衣裳紧紧贴在身上,实在狼狈得紧,可这双眼睛仍透着让人胆寒的光芒,周围火色一丛丛的,照例挡不住他沉默有顷的这一刹,都水监只觉腿软:
“下官失职……”
本以为等待他的将是一顿恶骂,可奇怪的是,半晌都并无动静。都水台的这些人见成去非不言不语,有胆大的觑上一眼,被那阴冷的目光摄到,再也不敢抬首,一众人垂着脑袋,等成去非发话。
成去非夺过一支火把,朝四下里照了照,积水仍将将近腰,污浊的水面之上飘着人的尸首,畜的尸首,断木,残叶,一**往南涌去,消失在如墨的夜色深处。雨点仍清晰滴在脸庞,而风则彻底止住了,他无声看了半日,才用渐渐冷透的声音道:
“剩下的该如何做,自己看着办吧。”
这一众人愣愣看他远去,一颗颗心仍悬在半空,他就这样走了,更让人心生不安。
乌衣巷成府门前,杳娘本正侧耳留心着,心头忽一阵狂跳,忍不住推了推福伯:“大公子回来了!”说罢两人不约而同起身,几步跨下台阶,把手中长灯举得再高些,哒哒的马蹄声越发近了,两人不由相视一笑,喜不自胜,待成去非身影渐渐清楚了,福伯早携小厮去迎接,杳娘则扭身朝橘园奔了去。
琬宁一直守在橘园,并未离开,具体是什么时辰了她并不清楚,只一双眼睛因焦虑显得格外炽烈,仿佛那里头燃着一簇不肯熄的火。
外头响起杳娘吩咐婢子的声音时,她几乎要跳起来,忙出来相看,铜盆里已注满热水,里头泡着姜片、泽兰、桑枝等物,琬宁见状,鼻头没由来一酸,知道他终于回来了,正想着,脚步声已传来,并不似往日那般轻快,闷闷叩在青石板上,听得人心发沉。
成去非经这一夜早是疲惫不堪,目已不清,耳亦不明,脑中混沌成一团,身子亦早已从内到外凉透。
众人悄然无声而退,室内只剩琬宁一人,而他仍勉力支撑着身子坐在榻边,那一身泥泞肮脏射得琬宁双目隐隐发酸,她忍了忍,上前先替他把那湿透的衣裳一件件褪下来,再拿棉巾细细替他擦拭干净,忽想起他这书房还没围出暖阁,便扯过一床被子把他拢了拢,这才蹲下来去脱那靴子,因在水中浸泡太久的缘故,一时半会难能卸下来,琬宁又怕弄疼了他,不觉急出一头汗,忽听他懒懒道:
“不碍事,你用力。”
琬宁咬牙狠心一拽,果真给拽了下来,里头早灌满了杂草淤泥等物,等那双脚露出来时,早给泡得发白变形,她探手试了试水温,小心翼翼把那双脚续进水里,只见他脚底兀得一动,不禁抬首看他,他神情无恙,只是阖了双目。
琬宁再低头时,却见盆内有丝缕红线,仔细一看,原是他脚上不知何时划破了道伤口,许是砂砾硌的,许是踩到什么,一切不得而知。
她洗的极为用心,柔软的双手同他瘦长的脚□□缠在一起,反反复复揉着,竟让成去非微微有些吃痛,忍不住说她:“你轻点。”
可突然觉得一凉,有滴水珠落在他翘出水面的指头上。他抬眼望去,又是一滴,眼泪从琬宁的睫上溅落,晶莹透亮,再坠入了盆中,整盆水顿时冷得如同初融的冰雪。
成去非叹气:“你哭什么,罢了,我要去歇息。”
说着示意她擦拭,琬宁抹了抹泪,扶他起身,亦被他挡了:“我自己还走得动。”
“您身子凉,不沐浴再睡么?”琬宁担心他受了这大半夜的冻,又是风又是雨的,冷身子进那冰冷的被衾,该如何受。
成去非没有应话,已懒得开口,径直走向内室,脱了鞋子,掀开被角,仰面躺了下去,身子触到床的刹那,只觉身子立刻有了着落,舒适得很。
倒是这床榻,真的冷。
琬宁无声来到他跟前,立了半晌,唇都要咬破了,脸也烧了起来,待攒足了勇气,上前把那盏烛火吹灭,摸索着先在床边坐了,手底抖得厉害,却极力忍着,几下把自己脱得只剩一件贴身小衣,怯怯侧眸朝床上人看了一眼,脸上越发火烫,心一横,紧闭了眼,掀开那被子,紧紧拥住了成去非。
成去非本已昏然睡去,忽觉一具热身子贴上来,心底一惊,很快知道是她,警觉道:“你这是干什么?”
他实在是被风雨侵蚀太久,琬宁亦被他冰冷的身子一激,止不住地战栗,却不肯松手,只喃喃道:“我给您捂捂就不冷了……”
“你,”成去非无奈,“你这岂不是如荀粲惑溺?”
琬宁却只听得他一颗心怦然直跳,不免失神:“大公子,您的心在跳。”她竟存了那么一点绮思,他也是能为他人心跳的人么?
“我又不是死人,它自然是跳的。”成去非声音渐弱,无力同她周旋,一个翻身过来,把她往怀中箍紧了,再也不肯多说一字,只怀抱这团温暖沉沉睡去。
第134章
凤凰四年秋,涛水入石头; 漂杀人户。商旅方舟万计; 漂败流断; 骸胔相望,江左虽频有涛变,然未有若斯之甚。
石头城遭此类劫难,亦非首次,朝堂之上并无多少惊诧之意; 只谈论起当晚巨风; 众人方心有余悸,感慨良久。既司空见惯; 朝廷依照以往赈灾之法; 先遣使检行赈赡,发放救济物资,至于百姓浮尸过甚,高陵附近两千余株大树毁坏殆尽,一时难能诏赐死者材器,又恐引起后续瘟疫等乱事; 遂下诏统一就地掩埋。
待有人提及开仓赈济百姓之时; 众臣之间忽发出一阵微微的骚动; 这其中,自有一半人不知内情,只跟附和此举势在必行,然另有一半默不作声; 并无表态之意。英奴发觉气氛中不妙的端倪,却只把目光在成去非身上淡瞥一眼,任由底下喁喁私语半日,才看着顾曙问道:
“顾尚书来算算这笔账,开仓济民,每户可领几斗米?”
前一阵,秋粮上仓,朝野上下正言丰收,不料转眼风雨伤稼,百姓立有饥谨之虞。只要有心细想,便知眼下国步堪伤,外则战事未息,内则灾荒不断,天灾也罢,**也好,二者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英奴并不是毫发不知,然而这其中掣肘无奈之处,亦非天子独感。
国朝草创之初,并未留意水事。自宗皇帝起,方设都水官府,然河堤谒者不知水势,却是常态。直到皇甫谧任大司农,上表言“水功至大,当与农事并兴”,事情才一度迎来转机,大司农慧眼识人,举荐有方,多有知水者在其职。到钟山一变,人事浮动,都水官府不仅以外行人充之,更是不务王事,此次海水倒灌一事,尚书令如何栉风沐雨早传遍朝堂,不过水灾之事,到底是俟河之清。
顾曙心下无言,可面上仍是寻常,只道:“稻稼荡没,黎庶饥谨,今上怜恤子民,臣深感圣主之德。”
他言之殷殷,英奴听得麻木,双目水波不兴,心里只想你便是少言几句废话,朕也得宽慰,难道要打马虎眼?
“秋务己及,宜加优课,诚如今上所言,穷弊之家,赐以薪栗。臣方粗略一算,可赐痼疾笃癃口二斛,老疾一斛,小口五斗,官仓可堪此重。”
英奴轻吁一口气,手指在膝头点了点:“那便按顾尚书所言拟旨,”说着望向中书舍人,微微颔首示意。
言罢忽叹气道:“前日朕命顾尚书筹量增俸,如今天灾突降,事情有变,朕以为,疆场多虞,眼下年谷不登,其供御所须,当事从俭约,九亲供给,权可减半,至于众卿廪俸,”他有意延宕,目光投向最前面的大司徒中书令几人,众人自然听出天子弦外之音,一时噤声不语,片刻过后,虞仲素持笏而起,道:
“今上一片苦心,臣等惭愧,百官俸禄亦当减半。”
终是说了句他该说的,英奴微微一笑,见众人纷纷跟着附议颂圣,且不管真假,耳目之愉却是有的。
顾曙不禁垂了眼帘,眼波往成去非那边略略一动,思绪翻涌,怕是成去非私下已进言?天公作美,这个口实再好不过,天子几句便让众人哑口无言可驳。
“臣有事要奏。”成去非窸窸窣窣起身,众人目光自然很快聚到他身上来。
英奴摆手笑道:“朕正想如何罚你,你反倒还有事要奏?”
此言听得人摸不清头脑,又见天子笑得语意含糊,只得听他说下去:
“朕的肱骨,如何能轻易舍生入死布衣缓带去水里捞人?岂不大材小用,暴殄天物?倘真出了差池,朕就是拿整个都水台的人殉卿,也难赎卿一人啊!”
原是这话头,众人心知肚明天子所言何事,忍不住轻笑一阵,跟着打趣几句,君臣气氛陡然融洽至此,也出乎人意料,只是众人不曾想,尚书令到底是那煞风景之人,很快,这一时气氛再次变僵:
“圣明无过天子,臣这一事有罪,另有一事,恐罪上加罪。”
不光天子,在座诸位皆听出这话里有意,英奴便渐渐敛了笑:“尚书令说吧。”
“廷尉曾奉旨查仓,事后呈报今上,言都城各仓满囤,实则不然,方才今上命度支尚书筹算开仓赈灾,实恐难行。”
成去非有意无意左右扫了一眼,语调极稳,也不管四下面面相觑的诸官,见英奴神情动了动,便给天子留足够想象的空档。
“廷尉之前查的北仓一案,和这事有关吗?”英奴很快嗅出这其中一丝诡谲,最不愿联想的便是,难道又无粮可调?国朝动辄就空虚到如此地步,这个朝廷到底何以运作到今日的?龙椅上的天子又是何以自处的?
“今上当问廷尉,廷尉来台阁调取账册,臣才知失察至此,官仓储粮实际数目,同归档账册所记,天壤悬隔,臣有罪,罪在臣躬一人,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而臣不明不察,有负圣托,还请今上降罪。”
便是他这人,说起套话来,也是让人害怕的,英奴冷冷瞧着他,说了这半日,雾里看花水中捞月般,到底是何内情,他成去非为何不再说清楚些?
脑中一转,很快清明,好一个百官之本,录尚书事的又不是他,他反倒大包大揽把罪责扛下来了,虞仲素不是韦公,即便当下人人也要尊称一声“虞公”了,大司徒就坐在前头,成去非话已至此,录尚书事的几位还坐得住吗?
果不其然,中书令张蕴很快接言道:
“尚书令当把来龙去脉说明白些,御前奏事,岂能语焉不详?”
话听着有几分不客气,可张蕴神情却恳切,成去非微微颔首,“官仓一事,当由廷尉面圣直奏,非臣职责,臣所言,乃台阁之过。”
言毕顾曙只好出列:“臣有罪,度支岁入有常,现当事物繁多,臣有失细密,致碍当务之急需,还乞今上降罪。”
这是查出什么来了,一个个的,尽在这里装正卖勇,英奴焉能不知?成去非挑这个头,他尚书台一众人自然紧随其后,还不知道这番话到底是针对何人而发,却偏要说的处处替君父着想,言臣子之大义,横竖官仓的事,同朝堂之上这众卿家脱不了干系,是故大司徒光禄勋大夫司隶校尉等人毫无动静?倘真无干系,成去非缘何当众提及?
尚书令到底是精明啊,英奴心底幽然叹息,他有意借题发挥,却又只肯蜻蜓点水,好似一枚石子轻轻巧巧落入水中,早搅乱一池子人心,自己置身事外,大有等人入榖之意。众人见他所言不过冰山一角,知情的不知情的倒出奇一致地沉默,眼下谷粮正是敏感之事。一时殿中寂寂,连呼吸声都能教人生出几分焦躁。
“既如此,廷尉也有罪,一件事,这才多久,就弄得自相矛盾,先言官仓满库,后云账目有错,许自有疏漏之处,却不能不说亦有欺君之嫌,廷尉署这是如何当差的?还请今上明鉴。”虞仲素慢悠悠接了话,不无道理,众人只点头称是,一时又交头接耳窃窃私议起来。
成去非并不接这茬,只道:“廷尉如何奏事,今上又要如何鉴察,不是臣等此时所能妄自臆测的。”
还是这么滴水不露,英奴听得憋闷,这些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事情并未摊开来讲,难道只有天子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