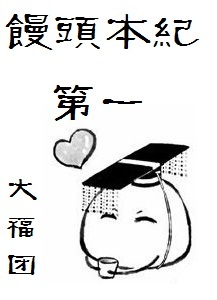权臣本纪-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众人笑成一团,把钱币甩得叮当作响,似是在诱惑那年轻人,年轻人不再做声,而是一步接着一步,往前迈去。他脚步极稳,面上并无难色,众人边数着步子,边大声嬉笑,直到算够了二十步,笑声渐消,一众人频频摇首,直道:“没意思,真没意思!”
说罢便要散去,年轻人见人要走,把东西一扔,上前一个箭步拦住了他们:“五十步我已全部走完,你们不能食言!”
众人冷笑,根本不屑一顾,扬起钱袋故意在他眼前晃了晃:“你倘是肯从我们□□钻过,便都是你的,怎么样?”
“对啊,杨定,敢不敢学韩信?说不定日后也成了人物呢!”
人群中的笑声再次恣肆,有人扬手朝高中抛了一枚钱币,落地丁零零一阵响,滚出很远,有人笑道:“杨定,你的赏钱,可拿好了!”
说罢,一群人扬长而去,杨定的目光立即四下搜寻起来,巧的是,这钱不远不近,正滚到成去非脚下,他便俯身捡了起来,路昱看在眼中,不发一言,只见成去非走上前去,把钱递给了杨定。
杨定毫不犹豫接过来,揣进怀中,这才抬首打量成去非,略觉诧异,眼前人分明也是贵公子模样,只是目中无波,看不透他这是何意。
两人目光相接刹那,杨定心里咯噔一下,道了声谢转身就要走。成去非自腰间解下唯一的配饰,忽喊住了他:“你留步。”
杨定嘴角一抽,却还是转过身来,只拧着眉瞧成去非。
“你应得的。”成去非把配饰给他,杨定却不接,丢下一句:“我不随便要人东西,公子无须施舍。”
“这世上能负重五斛米行五十步的人,并不多见,我今日有幸得见,就不能白看,你要不要,它都是你的。”成去非解释得落落大方,把配饰放置在不远处的石墩上。
玉佩在日光下头闪着温润的光泽,杨定犹豫了片刻,上前抓起玉佩,疾步追了上去。路昱半路截住他,低声快速道了句:
“勿要冲撞公子!”
杨定来不及多想,冲到成去非面前,迎上那一双寒潭冷目,竟一时忘词,半晌才道,“公子同我并不相识,真的只因那五斛米?”
“不然呢?”成去非望着他,并无凌人的气势,杨定却有些不解,眼睁睁看成去非走远,才回过神,忍不住瞅了瞅路昱。
他虽不认识路昱,路昱却认得他。杨定只是名再低微普通不过的兵士,可本事却早已在军中传开。据说有百步穿杨之才,今日得以见到他背五斛米行五十步,也是奇闻了。
只可惜这人不知怎么回事,爱财如命,总是被人戏弄,路昱也有所耳闻,方才一幕看下来,想必是常事了。至于大公子的举动,路昱忽有所得,遂上前问:
“怎么,你很缺钱?”
杨定并不否认,却似乎不想谈论这个话题,闷声闷气说了句:“这和你没关系。”
路昱并不生气,只带笑说:“大公子这个玉佩够你的了!”
既说到成去非,杨定忍不住问道:“那个公子出手这么大方,什么人?”
“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公子有识人之明,亦爱惜勇士。这位公子从不施舍与人,只赏识人才,你是靠真本事得来的,收着吧!”
一番话下来,路昱见杨定面色有变,知道他这种土包子必须把话挑明了才听得懂,遂无声一笑,拍拍他的肩膀:
“听说你射箭功夫不错,我那还有把良弓,要不要来试试?赢了我,那弓送你!”
杨定却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瞪着他,仿佛在判断他话中真假,路昱蓦然想起方才一幕,赶紧解释:“我可没那么无聊寻你开心。”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赢了,我不要弓,换成钱给我,你看成不成?”杨定居然也认真地解释了一番,路昱哑口失笑,定定看着他,叹口气: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还真是这么回事。”
话音刚落,余光瞥见不远处似乎有人在偷窥他们,等他定睛去寻,果然有一狭长脸面的人正往这边张望,一碰上路昱的目光,又迅速避开了。路昱眼波一转,只见杨定眼中掠过一丝不自然,他佯装没看到,轻松一笑:“走吧,好汉,也让我开开眼,瞧瞧百步穿杨是怎么回事?”
口中虽这么说着,路昱早留意了那人长相,目光一沉,心里已有了打算。杨定这人看着像藏了心事,阴晴难测,可实际上几句话下来,也还是个糙汉子,这种人,反倒好入手,路昱脑中再次浮现当日成去非所交代的一事,最初觉得毫无头绪,此刻,竟忽然就有了眉目。
第16章
退朝的时辰早过了,朝阳绚烂,整座太极殿沐浴在久违的春光里,琉璃瓦熠熠生辉,甚是美丽。
太后早已在西堂备了些清淡利口的饭食,见英奴往这边走来,黄裳眼尖远远瞧见了,赶紧进来回话。
“母后何苦等儿臣,这都什么时辰了?”说着,不免皱眉瞪了几眼奴婢们,太后轻轻摆手示意他坐过来:“你不要吓唬他们,”说着示意两边人都退了,独留了黄裳一人在身侧伺候。
“近日见你有些清瘦,今上饮食上要注意,”太后顿了顿,正色看了看英奴,“有些事,哀家不好干预,听说皇上最近很宠那两个司帐?”
英奴正喝着百合粥,拿眼角瞥了一眼黄裳,太后又说:“你不要看他,哀家看你眼窝发青,脚步虚浮,也知道是何缘由。”
“母后教训得是,儿臣记得了。”英奴话说间,念及那两具白皙滑腻的身子,腹底又煎熬起来。太后忽幽幽叹气,听得他不觉有些烦闷,而又得死死压着,太极殿上他分明就是看客,有他无他,众人皆早早定下了主意……他抬眼看了看母后,一如往昔庄重慈爱。
这些日子,他确实荒唐。夜阑人静时,辗转中望见一地的月光,隔着名贵的纱,影影绰绰透进来,喘息声不止,他身子忽然就那么一僵,隐隐忆起最初的那一缕心动,竟不由溢出一滴清泪来,全然为了自己的不能。而那女孩的模样,竟不觉变得模糊了已经。
太后见他出神,眉眼间满是郁郁之色,正想宽慰几句。外头有人隔着帘子道:“大将军有折子要呈给今上。”
这不是刚下朝没多久么?在大殿上不递折子,此刻又来叨扰,太后眉头浮上不悦,丢了个眼色给黄裳,黄裳会意,掀了帘子吩咐:
“太后同今上正在用膳,折子留下就行,请大将军先回。”说着接过了折子。
英奴却丝毫不意外,打开折子的刹那,反倒有股莫名的兴奋,一扫方才的阴霾,是啊,先皇都可以忍,一忍便是这么多年,他有什么不可以的?再说,他的皇叔这下一步如何跟乌衣巷斗,好戏才上演不是么?
这些年,大将军四处打击政敌,最大的动静也就是阮氏一案了,却也收到奇效,先帝就此病倒薨逝。算算这些年战果,可以当成热身,他真正的对手在后头等着,双方心知肚明,只差时日。
乌衣巷四姓可不是阮氏,一个修书谋逆的罪名就呼啦啦撂倒一个世家。
彼时拿下阮氏,英奴一直觉得这一案实在太顺,阮正通连辩解都不曾有过,端的是从容赴死之势。先皇悲恸入骨显然不是装出来的,却对此案也没什么救助的举动,纵有大将军厉威震慑,可帝师被诛,满朝上下皆袖手旁观,也足够让人心寒。
一壁想着,一壁看着手底折子,英奴不禁无声冷笑。
他的皇叔,果真要一点点暴露吃相了。
方才殿上发难,并未占据明显上风,可最后商议赋税一事大家竟也能其乐融融。这转眼间就递了折子,也是雷霆万钧,一点都不耽搁。
目光停在最后一行字上,英奴心口忽一阵翻腾,脑中划过一个可怕的念头:许是阮氏亦有迎合大将军之意?这么一想,连带着多年前宫闱里那点隐秘的传闻,一并涌上了心头。
宗皇帝大行时,跟前只有阮正通一人,等其他几位托孤朝臣赶到时,宗皇帝已驾崩,遗诏是在阮正通手里。一如当日自己继承大统般让人惊诧,当年宗皇帝最为倚重的皇子正是建康王,时人尊称“大亲王”,可最后却是先皇即位,一时间也是朝野哗然。
不过这终归是一则传闻,很快便被压了下去。当晚时间紧迫,阮正通一来无篡改遗诏的空档,二来托孤大臣不止他一人,纵然他愿意,其他人也不见得愿意。朝臣们只能把此归于帝心难测,毕竟宗皇帝成府极深,行事常常让人捉摸不定,有此一举似乎也能说得通。
但后来的事情却证明,大将军是怀恨在心的,否则不会在之后十余年间,最初的几位托孤重臣皆不得善终,表面上看和大将军并无多少关系,可那些不明不白死掉的人,谁也说不清真相是什么。
英奴悠悠把折子合上,似乎突然间就想通了一件事:不管阮正通当初是否篡改遗诏,大将军都不会放过阮家,而阮正通自己也清楚,能真正和大将军抗衡的唯有乌衣巷,阮家在,大将军就永远和乌衣巷斗不起来……
这么看,倒还真有魄力,英奴抬首迎上太后询征的眼神,无谓笑道:“朕当是什么要紧事,大将军自荐其王宁出任并州刺史。”
太后心底一凉,大将军真真按捺不住,这么快就插手西北。先前西北兵败一事,谁人都疑心是他暗地捣鬼,如今直接放台面来了。并州刺史林敏,那是成若敖一手提拔上来的人,这般明显,还真是让人侧目。
“那今上打算怎么办?”太后问,英奴面上越发放松:“母后可知大将军还说了什么?林敏这几年痔病频犯,大将军提议换个环境兴许就好了,说南方气候湿润,要让林敏转任广州刺史。”
这话一出,太后才倒吸一口冷气,好毒的手段!
广州乃蛮荒之地,瘴气丛生,蛇虫遍地,林敏这几年在边境之地确实坏了身子,大将军却正好借此大做文章……
“朕会如他所愿。”英奴把折子往几案上一扔,心里头忽然满了兴致:他要看看下一步乌衣巷是迎面而上呢?还是避其锋芒?
他是像个困兽,手里头没实权,可这斗争的双方却旗鼓相当,他不如铁了心当定这个看客……
想到这,遂又拿起了折子掂在手里,心底冷笑,他的皇叔还等着他表态呢!
春日渐远,大将军府邸依旧繁花簇簇,宾客如云。
诛阮氏,先帝薨,迎新皇,人事变,一一铺排而至,如行云流水,竟有一气呵成之感,大将军亦不免嗟叹光阴之快,眼底却藏着蓬蓬的笑意。
“乐师新谱佳曲《祭河山》,请诸君赏之!”大将军手持酒盏,宽袖一挥,便有伶人依次上台,一曲既起,果真苍冷豪迈。
“此曲格局之大,唯大将军方可匹配之!”底下人遥遥祝酒,大将军睥睨眼底众人,纵声笑起来:“来,良宴可贵,诸君共饮!”
杯盏交错声不绝于耳,这般欢愉场景,大将军醉眼微醺瞧着,斜倚榻上像是喃喃:“如此,才不负良辰。”说罢指尖落在膝头轻轻打起了拍子,坐间忽有人摇晃起身,略显醉态:
“往者不可谏,来者不可追,臣以为,大将军当快马加鞭,再立不世之功!”一番陈辞慷慨激昂,借着酒意,听得人振奋,纷纷跟上附和不已。
大将军哼吟一声,眯起眼睛看着底下人:“兰卿就说说,我该立何功业?”
“大将军应剑指西北!”
坐间忽然寂静,众人听得心头一跳,一时不能回神。西北是乌衣巷成家固有势力范围,经营数十年,成家人功业正立于此地。大将军倘有遗憾,那定是未曾驰骋沙场。亲自趟一趟死人堆,又岂是身处江左庙堂能想象的呢?
短短一句,耳畔便是边声角冷,眼前雁字荒城,大将军嘴角终于绽开一缕笑,借着几分酒力,整个人如同醉玉倾山,大司农皇甫谧凝眸看了看他,并未像他人般跟着高谈,复又置酒,垂下眼帘像是什么也没听到。
满室高谈阔论,指点江山,好不痛快。
直至夜深,留一室残山剩水,宾客尽散,大将军醉态分明,兴致仍在,朝迟迟不起身的皇甫谧瞥了一眼,笑道:“主客尽欢,子静兄为何无动于衷?”
方才喧哗扰嚷的声音消散殆尽,四下里寂寂,皇甫谧听他换了称呼,知道并不是真醉,沉声说了句:“不可,唯西北不可。”
烛光炽烈,大将军听得真切,就势仍倚在榻边,迷蒙之间只看到烛花摇曳,满眼醉红,少年时便熟稔于心的歌谣忽就漫上来,不由脱口而出:
“金戈铁马引箭惊鸿,塞外雪冷关山万重,封侯觅尽谁人入梦,”调子依然清楚,只是末了这一句亘在喉间,自带不祥,而他,本不信这些的。
竟也迟疑了。
皇甫谧比他年长,这歌谣自然更加熟悉。昔年祖皇帝出征边关,营火之间将士们借着烈酒起舞,主簿曾琪就此谱了新曲,正是这首《关山冷》。那末了一句,他自然是知道的。
“大将军好兴致……”皇甫谧捕捉到他眉宇间的一抹神往,心底唏嘘,轻叹一声:“来日方长,大将军不可操之过急。”
“子静兄!”大将军骤然高声打断,“我已四十不惑,子静兄也将知天命,人生苦短,不知我还有多少日月可待?”
他眸中突迸一丝光芒,却又陡然黯淡下去。皇甫谧知他心结,好言继续相劝:“大将军雄心壮志,日月可鉴,只是西北棘手,大将军若是想夺西北军权大可不必急于一时,若是想驱逐异族,开疆拓土,那更要从长计议。”
“西北边关,纷扰不断,成氏毕竟能守得住国门,大将军贸然插手,易陷囹圄,不如先握稳京畿大权,再作图谋。”
肺腑之言,鞭辟入里,他岂能不懂?眼中却有恨恨色,假若不是他那庸碌皇兄无所建树几十年……念及此,手底力道不觉重了许多,却是空无一物,只化作紧握的拳。
皇甫谧知道他已上了折子,可王宁远不是能镇守一方的人才,更何况并州之地,胡汉杂居,又岂是他们这些长居富贵乡的公子才士所能驾驭的?
只是大将军一意孤行,他也没过分规劝。其实他不是不能理解大将军的心情,毕竟西北是他这一生心结所在,即便这次布局有些急进了,也当是多年的一个宣泄吧,而眼下,众人以为看出大将军意图,撺掇着就此插足西北诸事,他却不能再放任不管了。
大将军眸中扑闪着精光,半日都没再说话。
“禁卫军之权最为要紧,大将军可上表奏请领军将军温济之为太尉,再荐您妻弟接任此职。温济之素与四姓亲善,架空他,等于先砍了乌衣巷一条臂膀。禁卫军大权在手,西北我们自可慢慢图谋。”
听了皇甫谧这番话,大将军身子才渐渐松弛下来,默默颔首。
皇甫思虑半晌,又道:“长公子今年虚龄十六,当日成去非入朝辅政也不过这个岁数,吾等将力荐长公子出任黄门侍郎。”
说到子嗣,大将军不由一阵心冷,长子凤宇资质平平,幼子则更叫人伤怀,竟是个痴傻东西,连话也不能言语,人丁零落,不能不叫人痛心,想到这,眉眼处难免有些落寞,皇甫谧只好再度婉言相劝:
“听闻石俊常送美人与海狗肾,身子不可不补,但凡事,总不宜过重过急……”说到这,皇甫谧颇为尴尬,终究是私事,他不好过问,便不再多言。
大将军若有所思,陷入沉默,连皇甫谧也不知他此刻所想了。
第17章
刚入夏,大将军呈了折子,英奴暗叹他的皇叔动作之快,温济之升太尉,位列三公,不过虚名,却也有制可循,唯有允诺。倒是凤宇迁了黄门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