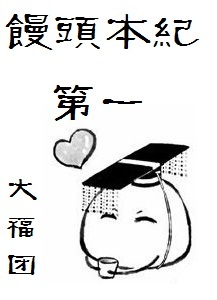权臣本纪-第9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刘氏点点头,来时已弄清,园子外头几株树上的确盘旋了数只,时不时叫唤上半晌,她已命人点了火把上去,并无老巢,那鸟偶一着枝,少顷便振翅而去,不一会,又自回来,如此反复,的确让人心烦,刘氏无法,只能让小厮们举了火把,先停将在树干上头,用来震吓,除此之外,别无好法。
“倘在平日,尚可吟诵一句‘瞻乌爰止,于谁之屋’,此般心境,而后可复得乎?”顾勉眉间黯然,半隐在这并不明亮的一室内,忽觉心酸备至,而眼前唯独伊人可诉,不仅仅是因眼前人是他此生挚爱,更因眼前人是他儿子的母亲,世间所有情感,两人才可谓休戚与共。
枯木寒鸦,夕阳已坠,更添凄伤,刘氏轻轻握住了他的手,果真一片冰冷,这才发觉窗子是开着的,一面起身去关窗,一面道:“富家之屋,乌所集也,是为祥瑞,夫君万不可这会便作灰心之语。”
“祥瑞……”顾勉苍然道,“夫人,子昭怕是回不来了……”
刘氏闻言眼窝骤酸,极力忍着,跪倒在顾勉膝前,颤声不已:“总归是妾教养有失,才使夫君徒遭此忧。”
顾曙扶她起身,叹道:“你我不再有儿孙福,更要自己爱惜自己,夫人不要跪着,快起来。”
刘氏也不掏帕,只遮袖拭了一下眼角,听顾勉接言道:“我怎能怪夫人,到底是我这做父亲的失职,只是,此刻再提,并无亡羊补牢之功。”
言罢心下茫然无措,一时痛心悔恨等各样情绪纷沓而至,不觉间朝四下望去,喃喃道:“我记得子昭幼年时每到春日便喜欢躺在庭院里,一动不动地从午后躺到日落,不过他也甚爱冬日,总是宴起,却依旧学得比任何人都要快,都要好,他就在这写大字,无须我多提点,三岁便拿握狼毫,每日写十章大字,夫人可还都记得?”
声音渐渐融入外头无边的夜色中去,屋内这对夫妻,已相携走过几十载光阴,更多的是甜蜜默契的纷纷过往,然而此刻,却不得不共同咽下这份将死的春心……
第157章
凤凰四年十月十九日的早朝,卯时未到; 百官已站在司马门外集齐相候; 有细心者; 发现独独少了光禄大夫顾勉,便有那素爱打听的低声求问,既有相问的,也就自有请从隗始的,云光禄大夫早已暗中面圣; 发言摧鲠; 乃至吐血,情虑深重; 一时间围作一团的几人你唱我随; 不觉间便弄出些躁动劲来,直到有人忽轻咳一声示意,原是顾冕竟逶迤而来,见他现身,百官缄口,则有大司徒上前问候; 两人相视一眼; 亦不复多言; 虞仲素微微颔首,待百官分班入座,却不料天子却延迟不来,席间声音渐起; 有司提醒一句,亦不见收敛多少,直到天子终姗姗来迟,这才复归安静。
英奴见再无人说话,却是吩咐中书令道:“宣旨吧!”
众人一时屏住呼吸,猜想天子这回是要开门见山,单刀直入,遂皆目不转瞬看向了前方。中书令醇厚的嗓音随即而起:“侍郎顾未明,恃权恃贵,强抢民女民子,妄以权贵之身,窃杀生之权,枉戮百姓二百余人,纵恣尤甚,罪不容恕,国家设法焉得容此?又隐匿千余户人口不报,与国争利,咎由作士,法在必行,兹二罪并罚,赐自尽。钦此。”末了,张蕴的声音陡然有一顿,虽很快续上,但细微的变化仍落在了百官耳中。
圣旨并不长,只把顾未明两宗重罪说清,并未牵涉前头诸多旁枝末节,违禁夜游、侵扰百姓等等名目,实为虚头,定不了他的罪,这道圣旨可谓切中肯綮,刀刀见血。成去非默默听完,静候片刻,方等到大司徒徐徐出列:
“侍郎所行,确是天怒人怨,不杀不足以慰人心,但顾家先人曾随祖皇帝草创百业,居功至伟,子孙倘……”
“司徒大人,”英奴幽幽打断了他,“如若又要提八议,朕可以清楚地告诉众卿,此古所无,何八议之有?方才的旨意,还不够清楚吗?”说着四下一顾,并不单单望着虞仲素,“诸卿打算胁迫朕改口入议?朕倒是想给他入议,朕也没有忘记顾家先人之功,可民心似水,不要说你们了,就是朕,也在这水上头,风平浪静则好,洪水滔天之时,诸卿又何以遁逃?”
天子金口玉言,自有敲打之意,不光是虞仲素面上一阵难堪,其余人等也各抱着一门心思,临近的,相对的,彼此碰了碰目光,再无一人开口。
此刻唯有顾勉咬牙跪地道:“主忧臣辱,臣教子无方,枉为人表,请天子一并降罪……”众人循声望去时,却见光禄大夫竟满头是汗,不知他此刻虽奋力克制,然终到力怠神危之时,身子一晃,整个人就此轰然倒地,一时引得人惊呼连连,有人早出列上前搀扶,殿上登时陷入一片混乱,急的有司高声提醒几回,才稍稍平复下来,英奴冷眼看了半日,才吩咐来人把顾勉送出去给太医瞧。
事情至此,再无可回环的余地,百官唯有纷纷应声领旨,英奴便起身道:“今日恰巧也是立冬,朝下赐宴,众卿各自去领,散朝吧!”
众人便在天子戛然而止的旨意中退去。
成去非出御道之后,特意下车行至高处,扶着栏杆不禁回首望向薄暮之中的司马门,忽然就想起几年前深冬政变时自己对那三千死士的一番话:
今日唯有一句,但凡阻拦者,你们杀尽便是。
尔后死士们纷纷跪地立誓的声音刺透暗夜,至今言犹在耳。而那些人,有一些被去远带往西北,有一些仍蛰居禁军,有一些则远走高飞,忘情江湖,总归是各得所愿。
那么人活一世,可又真的能各得所愿?他伸手触及到的地方,仿佛皆一片温热血迹。
等到回府用过晚膳,冷雨骤至,窗外风声鹤唳,赵器忽入室报道:“虞公子来了。”成去非只抬首相看,虞静斋身上落了几点雨,眉宇鬓角也湿漉漉一片,待他窸窸窣窣坐定,婢子奉上干净棉巾,成去非才道:
“你是为顾子昭的事情而来?”
虞归尘默了片刻,把棉巾一放:“事已至此,何须再言?只是听说顾家世叔醒来复又昏厥,子昭虽是咎由自取,可天下的父母都一样。”
成去非冷冷回道:“那么世叔此刻应能体会庄氏夫妻心境,他的儿子是珍宝,别人的儿子就是草芥么?将心比心,各得其平,今上赐顾未明自尽,而不是斩立决,已经是体恤他顾家的颜面。”
“你去监中见他最后一面了?”成去非问,虞归尘叹息一声:“是,他倒很平静,托我给他备些纸墨,写了一首《鸨羽》给世叔,又单独写了篇《凯风》给他母亲,除此之外,另让我捎带句话说给你。”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成去非忽想到这一句,心下虽并不在意,却道:“他要还是些荒唐之辞,你不用替他传了。”
到底还是嫌恶的意思,虞归尘顿了顿,方道:“他只说了八个字‘肘腋之患,其防可乎’”
大牢中虞归尘冷不丁听他道出这八字时,亦觉怪异,并未多问,只答应他一定带到,此刻见成去非若有所思,遂说:“他还是想见你一面,伯渊,你同他虽算不上竹马之交,可也毕竟相识多年,还是去送他一程。”
夜雨潇潇,反倒更有利于人冥想,成去非沉思良久,终起身出门:“静斋,多谢你来相告。”
“其实我来并不单为此事,”虞归尘跟着起身,成去非回首定定看着他,两人相视有时,虞归尘斟酌开口,“你那日忽又细对一遍修陵的账目,册薄是大司农送来的,你可是又发觉了什么?”
成去非微微笑道:“大尚书不遗巨细,睹微知著,君子见始知终,祸无从起,此思虑之政也。”
“伯渊,连着两个案子,即便再有事,最好还是缓一缓。”虞归尘则不能不劝,“你可知这两事下去,纲纪虽清,你要招多少人怨恨?天宪虽自今上出,但风言风语的,你不难猜测,再者,”他忽觉一阵艰涩,还是继续说了,“司徒府议事,已有人向大司徒言及你专权擅威,使人主壅蔽,自有倾覆之兆,我说这些,只盼你能临行而思。”
成去非反问一声:“司徒大人如何说?”
虞归尘微微一愣,低声道:“司徒大人不置可否。”
宁使网漏吞舟,不为察察之政,镇之以静方是玄学宗主大司徒的为政之道,成去非心知肚明,再看虞静斋时,只道:“静斋,司徒府议事,你身为台阁重臣,不宜露面,我去大牢,你先回家。”
“我已同狱官说好,不过并未点明是你要去。”虞归尘说完,便先撑了伞往家中去了。
冬雨凄寒,戌时末一刻,一辆车马停在廷尉狱前。当狱官终等到这位头罩风兜,一身鸦色便服的年轻公子时,面上虽恭谨有加,但心底总归是叫苦不迭。顾未明是两日后就待处决的重犯,没有天子旨意,本不能随意放人来探监,倘是顾家人亲携上谕而来还在情理之中,但一个时辰前,一位贵公子已然犯了规矩,不但如此,临走还要再交代怕是仍有贵人前来,虽不曾点明,却让人不能提着一颗心,狱官只得耐心相候,看到成去非这一刻,仍小心翼翼在前领路。
通往牢狱深处的路似乎很长。
锈蚀的铁栏,阴森的尸气,惨淡的微光,和着间或传来的死囚抽噎,交织成一幅流脓的画。窗口过高而狭窄,这里常年一丝风也进不来,眼下时令,干冷僵硬的腐坏空气让人憋闷,大约阴曹地府也不过如此,成去非终来到了关押顾未明的狱门前,侧眸吩咐道:“请打开门,我有几句话要同他讲。”
狱官一脸迟疑无奈:“公子您没有今上的手谕,下官实在难能从命,还请公子见谅。”说着就势作揖,这边顾未明听到此间言语,便起身踱步而至,两人目光碰触时,他淡淡一笑:“你还是来了。”说罢对那狱官笑道:
“我横竖是将死之人,难道还怕有人这个时候来害我?烦请暂且回避。”
见那狱官还在犹豫,便说:“上一位公子如何?他也是这样的,不过故人有最后几句话要说。”
成去非罕见他有如此温和之时,看来囹圄之境,当真叫人不得不低头,他这般倨傲的人,也能作此语,更印证此点。
遂兀自解了颌下衣带,那件氅衣随即跌落于地,狱官怔怔瞧着成去非,等回过神来,垂首上前深深一躬:“下官失礼了。”说罢上上下下把成去非检查一遍,趁此时,成去非这才发觉顾未明衣衫凌乱,面容憔悴,一时竟记不起他平日里峨冠博带的模样。
待那狱官退下,身侧再无旁人,顾未明却缓缓滑坐于地,原是他手足桎梏太过沉重,不得不这般。成去非亦不愿此刻居高临下同他说话,遂盘膝而坐,顾未明眼中稍一掠过诧异,很快释然,失神道:
“你为何而来?”
“闻所闻而来。”成去非答道,顾未明哼笑一声,眉眼间终复爬上一抹惯常神色,隔着木栅看着成去非,“没有那八个字,你是不会来的。不过,像我这种人,能有何高见呢?我不过纨绔而已。成去非,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尚可于鸡笼山得尺寸之地,不知来日你可能有一席裹身?”
这样的话一出,连带着他袍底似都透着一阵阴湿的风。成去非面不改色望着他,冷笑道:“这个就不劳顾公子忧心了。”
顾未明亦笑着点头,忽正色道:“我有三事,不吐不快,你知道的,我这人虽在你眼中书罪无穷,但我绝不屑行素口骂人之事。”
成去非心下一动,默默颔首:“我洗耳恭听。”
顾未明微微昂起头,眼中光彩重现:“其一,凤凰元年,荆州许侃的长史缘何能与大将军家奴冲突起来,你可知?许刺史到底被何人所刺杀,你又可知?”
不等成去非思量应答,他很快继续道:“其二,凤凰三年沉船一事,我和你说过了,并非我所为,也不是我手下所为,你信也罢,不信也罢。”
“其三,庄氏夫妇不过普通村民,又是请谁书写的那一手好状词,你又可知?”
言罢复又露笑:“也许有你知道的,也许有你不知道的。成去非,你想方设法想杀我,终如你所愿,你可以走了。”
成去非脑中来不及细想他所言三事,拧眉注视着他:“顾未明,你不是糊涂之人,到了此刻,怎还会说出这种糊涂话?你到今日还认定是我想杀你?你错了,是国法要杀你,是天道要杀你。”
顾未明不禁仰首大笑,他那素来光洁俊美的面庞因此而扭曲,忽又停将下来,死劲盯住成去非:“你难道就不沾‘术’?成去非,不要标榜过高,水至清则无鱼,况且你也不是一池子清水。你别忘了,你的根在乌衣巷,生于斯,长于斯,有些事情,你撇不干净,中领军不是你成家人?尔不闻‘成家军’一说?”
说着偏过头去,声音里浮起一丝毒辣:“你走吧,成伯渊,我自会在前头等着你。”
成去非半晌无言,站了起来,刚一转身,忽闻顾未明又道:“那个贺琬宁,到底是你什么人?”
成去非不意他最后却问出这句,只略一驻足并不回首,淡淡道:“情之所钟。”
也不管顾未明神情是何反应,自己仍系好衣带,大步朝外走去了。
那狱官见成去非过来,忙一路又把他领出甬道,临到门口,赶紧在他上头撑开了伞,冷点冰雹一般砸在脸上,成去非紧了紧氅衣,侧首道了句:“今日多谢。”狱官连连谦让,目送他上了马车,这才长舒一口气来,不禁仰面瞧了瞧顶上乌漆一片天空,兀自喟叹:“又变天喽……”
第158章
就在成去非的马车已驶出几里远时,隐约听见后头有人呼喊; 赵器忙勒停马; 仔细辨别了一番; 扭头朝后望去,什么也瞧不见,不过哒哒的马蹄声倒越来越近,来人近身,一把掀掉雨帽; 把玻璃灯举高了; 赵器才大致看清是送成去非出来的狱官,忙敲了敲外壁:“大公子……”
帘子掀开一角; 风雨随之灌入; 成去非上下看了狱官一眼,那狱官颇为狼狈,雨水顺着脸颊蜿蜒直下,此刻也顾不上,只道:“罪官托下官来告知公子几句话,他原话是这么说的:既然是情之所钟; 便有了这第四件; 阿灰书房里有这姑娘的小像; 正是阿灰亲笔所作,上回宴会,这姑娘也是先去的阿灰书房。”
狱官一字不差把顾未明所嘱咐的道尽,成去非听言; 不由弯了弯嘴角,事到如今,他其实并不愿疑心她的,他告诉自己她是清白懂事的好姑娘,当初隐瞒身世是不得已为之,后来的诸多情意,他能察觉得到,自是发于真心,她并不是虚伪之人,那么,如照顾未明所言,又是何故?他不信顾曙不过来家中偶尔见她两回,就情根深种,他们都不是这种人,再想当日宴会种种,才忽觉事情曲折间不知隐藏了些什么。
“就这些?”成去非问,那狱官点点头,成去非便又问:“阁下可知道我是谁?”那狱官摇首道:“下官一介无名小吏,自然不识贵人府邸何处。”
“可知罪官口中阿灰是何人?”成去非似是满意,继续发问。
狱官抹了一把雨水,谨慎道:“下官出于道义替那将死之人传句话罢了,并不知这阿灰是何人,这些话,下官既传达了,自然是说过就忘记,什么也不知道。”
“阁下很会说话,这样最好,多谢。”成去非略略示意,击了击掌,赵器遂扬鞭而去。
成去非端坐如常,仔细思想一番,忽觉毫无意趣。他是成家的大公子,并非她一人夫君,她倘真是怀了异心,这一回便不是一顿鞭子能过去的。只是他不肯再轻易犯错,一次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