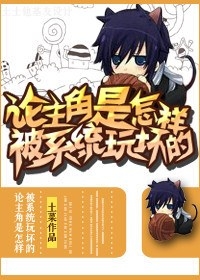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5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是不眠之夜的结果。这座不大的住宅里,经常可以听到吉他的琴声和达雅的歌声
了。
这个获得了欢乐的女人也常常感到苦恼,她觉得自己的爱情好像是偷来的。有一点
响动,她就要哆嗦一下,总觉得是母亲的脚步声。她老是担心,万一有人问她为什么每
天晚上要把房门扣上,她该怎么回答呢。保尔看出了她的心情,温柔地安慰她说:“你
怕什么呢?仔细分析起来,你我就是这里的主人。放心睡吧。谁也没有权力干涉咱们的
生活。”
达雅脸贴着爱人的胸脯,搂着他,安心地睡着了。保尔久久地听着她的呼吸,一动
也不动,生怕惊醒她的甜梦。他对这个把一生托付给他的少女,充满了深切的柔情。
达雅的眼睛近来总是那样明亮,第一个知道这个原因的,是廖莉娅,从此,姐妹俩
就疏远了。不久,母亲也知道了,确切些说,是猜到了。她警觉起来,没有想到保尔会
这样。有一次,她对廖莉娅说:“达尤莎配不上他。这么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
她忧心忡忡,却又没有勇气同保尔谈谈。
青年们开始来找保尔。小房间有时挤得满满的。蜂群一样的嗡嗡声不时传到老头子
耳朵里。他们常常齐声歌唱:
我们的大海一片荒凉,
日日夜夜不停地喧嚷……
有时候唱保尔喜爱的歌:
泪水洒遍茫茫大地……
这是工人党员积极分子小组在集会,保尔写信要求担负一点宣传工作,党委就把这
个小组交给了他。保尔的日子就是这样度过的。
保尔双手重新把住了舵轮,生活的巨轮几经周折,又朝着新的目的地驶去。他的目
标是通过学习,通过文学,重返战斗行列。
但是,生活给他设置了一个又一个障碍,每次遇到波折,他都不安地想:这回对他
达到目的地,不知道会有多大影响。
突然,那个考大学不走运的乔治带着老婆从莫斯科回来了。他住在革命前当过律师
的岳父家里,不断回来刮他母亲的钱。
乔治一回来,家庭关系更加恶化了。他毫不犹豫地站在父亲一边,并且同那个敌视
苏维埃政权的岳父一家串通一气,施展阴谋诡计,一心要把保尔从家里轰出去,把达雅
夺回来。
乔治回来以后两个星期,廖莉娅在邻区找到了工作,带着母亲和儿子搬走了。保尔
和达雅也搬到很远的一个滨海小城去了。
半年过去了。国家开始进行伟大的工程。社会主义已经到了现实生活的门槛前面,
正由理想变成人类智慧和双手创造的庞然巨物。这座空前宏伟壮观的大厦正在奠定它的
钢筋混凝土的地基。
“钢、铁、煤”这三个有魔力的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进行伟大建设的国家的报纸上。
“要么我们跑完这段距离,赶上技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用最短的时间,也建立
起自己强大的工业,使我们在技术方面不依赖于资本主义世界,要么我们就被踩死,因
为没有钢、铁、煤,不要说建成社会主义,就是保住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也
是办不到的。”党通过领袖之口这样告诉全国人民,于是全国出现了为钢铁而战的空前
热潮,人们迸发出来的巨大激情世所未见。“速度”这个词也发出了热烈的行动号召。
在久远的古代,为抵抗贵族波兰以及当时还强盛的土耳其的入侵,哥萨克分队曾驰
骋在扎波罗什营地上,杀得敌人闻风丧胆,如今在昔日的营地上,在霍尔季扎岛近旁,
另有一支部队在安营扎寨。这是布尔什维克的部队,他们决定拦腰截断古老的第聂伯河,
驾驭它那狂暴的原始力量,去开动钢铁的涡轮机,让这条古老的河流像生活本身一样为
社会主义工作。人向自然界发动了进攻,在汹涌的第聂伯河的急流处,给它桀骜不驯的
力量戴上钢筋水泥的枷锁。
在三万名向第聂伯河开战的大军中,在这支大军的指挥员中,有过去的基辅码头工
人、现今的建筑工段段长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大军从两岸向河流夹击,从战斗打响
的第一天起,两岸之间就展开了社会主义竞赛,这是工人生活中的新生事物。
潘克拉托夫那硕大的身躯轻快地在跳板上、小桥上跑来跑去,一会儿在搅拌机旁跟
弟兄们说两句俏皮话,一会儿消失在土壕沟里,一会儿又突然在卸水泥和钢梁的站台上
露面。
一大清早,他那佝偻的身子出现在“吃紧的”工区,直到深夜他才把终于疲乏了的
巨大躯体放倒在行军床上。
有一次,他面对晨雾笼罩的河面,面对河岸上一望无际的建筑材料,看得出了神,
不禁回想起森林中小小的博亚尔卡。当时似乎是一个大工程,同目前的情景相比,不过
是一件儿童玩具罢了。
“瞧咱们这气派,发展得多快,伊格纳特好兄弟。第聂伯河这匹烈马让咱们给套住
了。老爷子们再也不用在这急流险滩上折腾吃苦头啦。给你一百万度电,没说的!这才
是咱们真正生活的开端,伊格纳特。”一股热流从他胸中涌起,仿佛他贪婪地喝下了一
杯烈酒似的。“博亚尔卡那些弟兄们在哪儿呢?把保尔,还有扎尔基两口子都叫来多好,
咳!那我们就把左岸的人给盖啦。”想到博亚尔卡,他又不由得想起了朋友们。
那些跟他一起在隆冬季节大战博亚尔卡的人,还有那些共同创建共青团组织的人,
如今分散在全国各地,从热火朝天的新建筑工地到辽阔无边的祖国的偏僻角落,都在重
建新生活。过去,他们那批早期共青团员,大约有一万五千人。有时在茫茫人海中相遇,
真是亲如手足。现在,他们那个小小的共青团已成为巨人。原先只有一个团员的地方,
如今能拉出整整一个营。
“冲我们来吧,小鬼头们。前不久还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呢。我们已经在前线干开
了,他们还要妈妈用衣襟替他们擦鼻涕。一转眼的工夫,都蹿起来了,在工地上还拼命
想把你撵到乌龟壳里去。对不起,这一招可不行。咱们还得走着瞧。”
潘克拉托夫饱吸了一口河边清新的空气,深深感受到一种满足。二十岁的共青团员
安德留沙·小托卡列夫在左岸第七工段当支部书记,今天晚上潘克拉托夫要把那个工段
“挂到自己拖轮的钩子上”,到那时他肯定也会有这种满足感的。
至于刚才他回忆起的那位朋友和战友保夫鲁沙·柯察金,他现在被抛弃在偏僻遥远
的滨海小城,为争取归队而进行着顽强艰苦的斗争,既有失败的悲哀,也有胜利的欢乐。
阿尔焦姆很少收到弟弟的信。每当他在市苏维埃办公桌上见到灰色信封和那有棱有
角的熟悉的字体,他就会失去往常的平静。现在,他一面撕开信封,一面深情地想:
“唉,保夫鲁沙,保夫鲁沙!咱们要是住在一起该多好。
你经常给我出出主意,对我一定很有用,弟弟!”
保尔信上说:
阿尔焦姆:
我想跟你谈谈我的情况。除你以外,我大概是不会给任何人写这样的信的。你了解
我,能理解我的每一句话。我在争取恢复健康的战场上,继续遭到生活的排挤。
我受到接连不断的打击。一次打击过后,我刚刚站起来,另一次打击又接踵而来,
比上一次更厉害。最可怕的是我现在没有力量反抗了。左臂已经不听使唤。这就够痛苦
的了,可是接着两条腿也不能活动了。我本来只能在房间里勉强走动,现在从床边挪到
桌子跟前也要费很大劲。到这步田地大概还不算完。明天会怎么样——还很难说。
我已经出不去屋,只能从窗口看到大海的一角。一个人有一颗布尔什维克的心,有
布尔什维克的意志,他是那样迫不及待地向往劳动,向往加入你们全线进攻的大军,向
往投身到滚滚向前、排山倒海的钢铁巨流中去,可是他的躯体却背叛了他,不听他的调
遣。这两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还有比这更可怕的悲剧吗?
不过我还是相信我能够重返战斗行列,相信在冲锋陷阵的大军中也会有我的一把刺
刀。我不能不相信,我没有权利不相信。十年来,党和共青团教给了我反抗的艺术。领
袖说过,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克的堡垒,这句话对我也适用。
阿尔焦姆,你会说我信里有许多熔化了的钢铁。本来嘛,我们的生活本身也不是靠
蛤蟆的冷冰冰的血点燃起来的。我要你和我一道相信,保尔会回到你们身边的,哥哥,
咱们还要一起好好干呢。不可能不是这样,要不然,当罪恶的旧世界已经在我们的马蹄
下声嘶力竭地呻吟的时候,国内战争的火红战旗怎么还会使我们热血沸腾呢?如果在棘
手的,有时甚至是残忍的生活面前我们屈膝下跪,承认失败,那我们工人的坚强意志还
从何说起呢?
阿尔焦姆,朋友们听到这些话时,我有时也看到有人流露出惊奇的目光。谁知道,
也许有人会想:他是让理想遮住了眼睛,看不到现实。他们不明白我的希望寄托在什么
地方。
现在稍稍讲讲其他方面的情况。我的生活已形成了一个格局,局限在一块小小的军
事基地上。这就是我的学习——读书,读书,还是读书。阿尔焦姆,我已经读了很多书,
收获颇丰。国外的、国内的著作我都读。读完了主要的古典文学作品,学完了共产主义
函授大学一年级课程,考试也及格了。晚上我辅导一个青年党员小组学习。通过这些同
志,我和党组织的实际工作保持着联系。此外,还有达尤莎,她的成长和她的进步,当
然还有她的爱情,她那妻子的温存体贴。
我们俩生活得很和美。我们的经济情况是一目了然的——我的三十二个卢布抚恤金
和达雅的工资。她正沿着我走过的道路走到党的行列里来:她以前给人家当佣人,现在
是食堂里的洗碗女工(这个小城没有工厂)。
前几天,达雅拿回来第一次当选为妇女部代表的证件,兴高采烈地给我看。对她来
说,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硬纸片。我注意地观察着她,看到一个新人在逐步成长,我尽自
己的全部力量帮助她。总有一天,她会进入一个大工厂,生活在工人集体中间,到那时
候,她就会最后成熟了。目前在我们这个小城里,她还只能走这条唯一可行的道路。
达雅的母亲来过两次。她不自觉地在拉女儿的后腿,要把她拉回到充满卑微琐事的
生活中去,让她再陷入狭隘、孤独的生活圈子里。我努力劝说老太太,告诉她不应该让
她过去的生活在女儿前进的道路上投下阴影。但是,这一切努力都白费。我觉得,达雅
的母亲有一天会成为她走向新生活的障碍,跟这个老太太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握手。
你的保尔
老马采斯塔的第五疗养院是一座石砌的三层楼房,修建在悬崖上开辟出来的平场上。
四周林木环抱,一条道路曲折地通到山脚下。所有房间的窗户全敞开着,微风吹拂,送
来了山下矿泉的硫磺气味。保尔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明天要来一批新疗养员,那时他
就有同伴了。窗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有好几个人在谈话。其中一个人的声音很耳熟,他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浑厚的男低
音呢?他苦苦思索,终于把藏在记忆深处的一个还没有忘却的名字找了出来:英诺肯季
·帕夫洛维奇·列杰尼奥夫,正是他,不会是别人。保尔蛮有把握地喊了他一声。过了
一分钟,列杰尼奥夫已经坐在他的旁边,快活地拉住他的手了。
“你还活着哪?怎么样,有什么好事让我高兴高兴?你这是怎么啦,真正当起病号
来了?这我可不赞成。你得向我学习。大夫也早说过我非退休不可,我就不听他们那一
套,一直坚持到现在。”列杰尼奥夫温厚地笑了起来。
保尔体会到他的笑谈中隐藏着同情,又流露出一丝忧虑。
他们畅谈了两个小时。列杰尼奥夫讲了莫斯科的新闻。从他嘴里,保尔第一次听到
党关于农业集体化和改造农村的重要决定,他如饥似渴地听着每一句话。
“我还以为你在你们乌克兰的什么地方干工作呢。没想到你这么倒霉。不过,没关
系,我原来的情况还不如你,那时候我差点躺倒起不来,现在你看,我不是挺精神吗?
现在说什么也不能无精打采地混日子。你明白吗?这样不行!我有时候也有不好的念头,
心想,也许该休息一下了,稍微松口气也好。到了这个岁数,一天干十一二个小时,真
有点吃不消。好吧,那就想想,哪些工作可以分出去一部分,有时候甚至都要落实了,
到头来每次都是一个样:坐下来办‘移交’,一办起来就没个完,晚上十二点也回不了
家。机器开得越快,小齿轮转得也越快。现在我们的前进速度一天胜过一天,结果就是
我们这些老头也得像年轻时候一样干。”
列杰尼奥夫用手摸了摸高高的额头,像慈父一般亲切地说:“好,现在你讲讲你的
情况吧。”
列杰尼奥夫听保尔讲他前些时候的生活,保尔注意到,列杰尼奥夫一直用炯炯有神
的目光赞许地看着他。
凉台的一角,在浓密的树荫下坐着几个疗养员。紧紧皱起两道浓眉,在小桌旁边看
《真理报》的,是切尔诺科佐夫。
他穿着俄罗斯斜领黑衬衫,戴一顶旧鸭舌帽,瘦削的脸晒得黝黑,胡子好久没有刮
了,两只蓝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一看就知道,他是个老矿工。十二年前,他参加边疆
区领导工作的时候,就放下了镐头,可是现在他的样子,仍然像刚从矿井里上来的一样。
这从他的举止言谈上,从他讲话的用词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切尔诺科佐夫是边疆区党委常委和政府委员。他腿上得了坏疽,这个病折磨着他,
不断消耗他的体力。他恨透了这条病腿,因为它强迫他躺在床上已经快半年了。
坐在他对面,抽着烟沉思的是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日吉廖娃。她今年三
十七岁,入党却已有十九年了。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大家都管她叫“金工姑娘
小舒拉”。差不多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尝到了西伯利亚流放的滋味。
坐在桌旁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他低着那像古代雕像一样美丽的头,正在读一本德
文杂志,不时用手扶一扶鼻梁上的角质大眼镜。说起来叫人难以相信,这个三十岁的大
力士竟要费很大劲才能抬起那条不听使唤的腿。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潘科夫是个
编辑、作家,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他熟悉欧洲,会好几种外语。他满肚子学问,就
连那个持重的切尔诺科佐夫对他也很尊重。
“他就是跟你同屋的病友吗?”日吉廖娃向坐在轮椅上的保尔那边抬了抬头,小声
问切尔诺科佐夫。
切尔诺科佐夫放下报纸,脸上立刻露出了兴奋的神情。
“是呀,他就是保尔·柯察金。亚历山德拉,您一定得跟他认识一下。他让病给缠
住了,不然把这个小伙子派到咱们那些难对付的地方去,倒是一把好手。他是第一代共
青团员。
一句话,要是咱们大家都扶他一把,他还可以工作。我是下了这个决心的。”
潘科夫倾听着他们的谈话。
“他得的什么病?”日吉廖娃又小声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