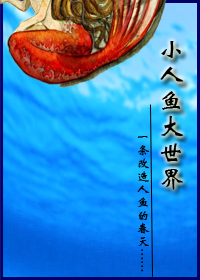悲惨世界-第9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七U字谜
孤单,和一切脱节,傲气,独立性格,对自然界的爱好,物质方面日常活动的缺少,与世隔绝的生活,为洁身自好而进行的秘密斗争,对天地万物的爱慕,这一切都为马吕斯准备了被狂烈感情控制的条件。对他父亲的崇拜已逐渐变成一种宗教信仰,并且,和任何宗教信仰一样,已退藏在灵魂深处了。表层总还得有点什么,于是爱情便乘虚而入。
整整一个月过去了,在这期间,马吕斯天天去卢森堡公园。时间一到,什么也不能阻挡他。古费拉克常说他〃上班去了〃。马吕斯生活在好梦中。毫无疑问,那姑娘常在注视他。
到后来,他能放大胆逐渐靠近那条板凳了。但是他仍同时服从情人们那种怯弱和谨慎的本能,不再往前移动。他意识到不引起〃父亲的注意〃是有好处的。他运用一种深得马基雅弗利主义的策略,把他的据点布置在树和塑像底座的后面,让那姑娘很可能见到他,也让那老先生很不可能见到他。有时,在整整半个钟点里,他一动不动,待在任何一个莱翁尼达斯或任何一个斯巴达克的阴影①里,手里拿着一本书,眼睛却从书本上微微抬起,去找那美丽的姑娘,她呢,也带着不明显的微笑,把她那动人的侧影转向他这边。她一面和那白发男子极自然极安详地谈着话,一面又以热情的处女神态把一切梦想传达给马吕斯。这是由来已久的老把戏,夏娃在混沌初开的第一天便已知道,每个女人在生命开始的第一天也都知道。她的嘴在回答这一个,她的眼睛却在回答那一个。
①莱翁尼达斯和斯巴达克都是公园里的塑像。
但也应当相信,到后来白先生还是有所察觉的,因为,常常马吕斯一到,他便站起来走动。他放弃了他们常坐的地方转到小路的另一端,选择了那个角斗士塑像附近的一条板凳,仿佛是要看看马吕斯会不会跟随他们。马吕斯一点不懂,居然犯了这个错误。那〃父亲〃开始变得不准时了,也不再每天都领〃他的女儿〃来了。有时他独自一个人来。马吕斯见了便不再待下去。这又是一个错误。
马吕斯毫不注意这些征兆。他已从胆小期进入盲目期,这是自然的和必然的进步。他的爱情在发展中。他每晚都梦见这些事。此外他还遇到一件意外的喜事,火上加油,他的眼睛更加瞎了。一天,黄昏时候,他在〃白先生和他女儿〃刚刚离开的板凳上拾到一块手帕。一块极简单的手帕,没有绣花,但是白洁,细软,微微发出一种无以名之的芳香。他心花怒放地把它收了起来。手帕上有两个字母U.F.,马吕斯一点也不知道这个美丽的孩子的情况,她的家庭,她的名字,她的住处,全不知道,这两个字母是他得到的属于她的第一件东西,从这两个可爱的起首字母上,他立即开始营造他的空中楼阁。U当然是教名了。〃Ursule!〃(玉秀儿!)他想,〃一个多么美妙的名字!〃他吻着那手帕,闻它,白天,把它放在贴胸的心坎上,晚上,便压在嘴唇下面睡。
〃我在这里闻到了她的整个灵魂!〃他兴奋地说。
这手帕原是那老先生的,偶然从他衣袋里掉出来罢了。
在拾得这宝物后的几天中,他一到公园便吻那手帕,把它压在胸口。那美丽的孩子一点也不懂这是什么意思,连连用一些察觉不出的动作向他表示。
〃害羞了!〃马吕斯说。
八残废军人也能自得其乐
我们既已提到〃害羞〃这个词儿,既然什么也不打算隐藏,我们便应当说,有一次,正当他痴心向往的时候,〃他的玉秀儿〃可给了他一场极严重的苦痛。在这些日子里,她常要求白先生离开座位,到小路上去走走,事情便是在这些日子里发生的。那天,春末夏初的和风吹得正有劲,摇晃着悬铃木的梢头。父亲和女儿,挽着手臂,刚从马吕斯的坐凳跟前走了过去。马吕斯在他们背后站了起来,用眼睛跟着他们,这在神魂颠倒的情况下是会做出来的。
忽然来了一阵风,吹得特别轻狂,也许负有什么春神的使命,从苗圃飞来,落在小路上,裹住了那姑娘,惹起她一身寒噤,使人忆及维吉尔的林泉女仙和泰奥克利特①的牧羊女那妩媚的姿态,这风竟把她的裙袍,比伊希斯②的神衣更为神圣的裙袍掀起来,几乎到了吊袜带的高度。一条美不胜收的腿露了出来。马吕斯见了大为冒火,怒不可遏。
①泰奥克利特(Théocrite),希腊诗人,生于公元前四世纪。
②伊希斯(Isis),埃及女神,是温存之妻的象征。
那姑娘以一种天仙似的羞恼动作,连忙把裙袍拂下去,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息怒。他是独自一人在那小路上,这没错。但也可能还有旁人。万一真有旁人在呢?这种样子真是太不成话!她刚才那种行为怎能不叫人生气!唉!可怜的孩子并没有做错什么,这里唯一的罪人是风,但是马吕斯心里的爱火和妒意正在交相煎逼,他下决心非生气不可,连对自己的影子也妒嫉。这种苦涩离奇的妒嫉确是会这样从人的心里冒出来,并且无缘无故强迫人去消受。另外,即使去掉这种妒嫉心,那条腿的动人形相对他来说也丝毫没有什么可喜的,任何一个女人的白长袜也许更能引起他的兴趣来。
当〃他的玉秀儿〃从那小路尽头转回来时,马吕斯已坐在他的板凳上,她随着白先生走过他跟前,马吕斯瞪起一双蛮不讲理的眼睛对她狠狠望了一眼。那姑娘把身体向后微微挺了一下,同时也张了一下眼皮,意思仿佛说:〃怎么了,有什么事?〃
这是他们的〃初次争吵〃。
正好在马吕斯用眼睛和她闹性子时,小路上又过来一个人。那是个残废军人,背驼得厉害,满脸皱皮,全白的头发,穿一身路易十五时期的军服,胸前有一块椭圆形的小红呢牌子,上面是两把交叉的剑,这便是大兵们的圣路易十字勋章,他另外还挂一些别的勋章:一只没有手臂的衣袖、一个银下巴和一条木腿。马吕斯认为已经看出这人的神气是极其得意的。他甚至认为仿佛已看见这刻薄鬼在一步一拐地打他身边走过时对他非常亲昵、非常快乐地挤了一下眼睛,似乎有个什么偶然机会曾把他俩串连到一起,共同享受一种意外的异味。这战神的废料,他有什么事值得这么高兴呢?这条木腿和那条腿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呢?马吕斯醋劲大发。〃刚才他也许正在这儿,〃他心里想,〃他也许真看见了。〃他恨不得把那残废军人消灭掉。
时间能磨秃利器的锋尖。马吕斯对〃玉秀儿〃的怒火,不管它是多么公正,多么合法,终于熄灭了。他到底谅解了,但是得先经过一番很大的努力,他一连赌了三天气。
可是,经过这一切,也正因为这一切,那狂烈的感情更加炽热了,成了疯狂的感情。
九失踪
我们刚才已看到马吕斯是怎样发现,或自以为发现了她的名字叫玉秀儿。
胃口越爱越大。知道她叫玉秀儿,这已经不坏,但是还太少。马吕斯饱啖这一幸福已有三或四个星期。他要求另一幸福。他要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
他犯过第一次错误:曾在那角斗士旁边的板凳附近中计。他犯了第二次错误:白先生单独去公园,他便不待下去。他还要犯第三次错误,绝大的错误,他跟踪〃玉秀儿〃。
她住在西街行人最少的地方,一栋外表朴素的四层新楼房里。
从这时起,马吕斯在他那公园中相见的幸福之外又添了种一直跟她到家的幸福。
他的食量增加了。他已经知道她的名字,她的教名,至少,那悦耳的名字,那个真正的女性的名字,他也知道了她住在什么地方,他还要知道她是谁。
一天傍晚,他跟着他们到了家,看见他们从大门进去以后,接着他也跟了进去,对那看门的大模大样地说:
〃刚才回家的是二楼上的那位先生吗?〃
〃不是,〃看门的回答说,〃是四楼上的先生。〃
又进了一步。这一成绩壮了马吕斯的胆。
〃是住在临街这面的吗?〃
〃什么临街不临街,〃看门的说,〃这房子只有临街的一面。〃
〃这先生是干什么事的?〃马吕斯又问。
〃是靠年金生活的人,先生。一个非常好的人,虽然不很阔,却能对穷人作些好事。〃
〃他叫什么名字?〃马吕斯又问。
那门房抬起了头,说道:
〃先生是个密探吧?〃
马吕斯很难为情,走了,但是心里相当高兴。因为他又有了收获。
〃好,〃他心里想,〃我知道她叫'玉秀儿',是个有钱人的女儿,住在这里,西街,四楼。〃
第二天,白先生和他的女儿只在卢森堡公园待了不大一会儿,他们离开时,天还很亮。马吕斯跟着他们到西街,这已成了习惯。走到大门口,白先生让女儿先进去,他自己在跨门坎以前,停下来回头对着马吕斯定定地看了一眼。
次日,他们没有来公园。马吕斯白等了一整天。
天黑以后,他到西街去,看见第四层的窗子上有灯光,便在窗子下面走来走去,直到熄灯。
再过一日,公园里没人。马吕斯又等了一整天,然后再到那些窗户下面去巡逻,直到十点。晚饭是谈不上了。高烧养病人,爱情养情人。
这样过了八天。白先生和他的女儿不再在卢森堡公园出现了。马吕斯无精打采地胡思乱想,他不敢白天去张望那扇大门,只好在晚上以仰望窗口玻璃片上带点红色的灯光来满足自己。有时见到人影在窗子里走动,他的心便跳个不停。第八天,他走到窗子下面,却不见灯光。〃咦!〃他说,〃还没有点灯,可是天已经黑了,难道他们出去了?〃他一直等到十点,等到午夜,等到凌晨一点。四楼窗口还是没有灯亮,也不见有人回来。他垂头丧气地走了。
第二天……因为他现在是老靠第二天过活的,可以说他已无所谓有今天了……第二天,他又去公园,谁也没遇见,他在那儿等下去,傍晚时又到那楼房下面。窗子上一点光也没有,板窗也关上了,整个第四层是漆黑的。
马吕斯敲敲大门,走进去问那看门的:
〃四楼上的那位先生呢?〃
〃搬了。〃看门的回答。
马吕斯晃了一下,有气无力地问道:
〃几时搬的?〃
〃昨天。〃
〃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
〃他没把新地址留下?〃
〃没有。〃
看门的抬起鼻子,认出了马吕斯。
〃嘿!是您!〃他说,〃您肯定是个探子。〃
一地下层和地下活动者
人类的各种社会全有剧院里所说的那种〃第三地下层〃。在社会的土壤下面,处处都有活动,有的为善,有的为恶。这些坑道是层层相叠的。有上层坑道和下层坑道。在这黑暗的地下层里,有一个高区和一个低区,地下层有时会崩塌在文明的底下,并因我们的不闻不问和麻木不仁而被践踏在我们的脚下。《百科全书》在前一世纪,是个坑道,几乎是露天的。原始基督教义的一种未受重视的孵化设备……黑暗,它只待时机成熟,便在暴君们的座下爆炸开来,并以光明照耀人类。因为神圣的黑暗有它潜在的光。火山是充满了黑暗的,但有能力使烈焰腾空。火山的熔液是在黑暗中开始形成的。最初举行弥撒的地下墓道,不仅只是罗马的地下建筑,也是世界的坑道。①在社会建筑的下面有着形形色色的挖掘工程,犹如一栋破烂房屋下的错综复杂的奇迹。有宗教坑道、哲学坑道、政治坑道、经济坑道、革命坑道。有的用思想挖掘,有的用数字挖掘,有的用愤怒挖掘。人们从一个地下墓道向另一个地下墓道互相呼应。种种乌托邦都经过这些通道在地下行进。它们向各个方向伸展蔓延。它们有时会彼此接触,并相互友爱。让-雅克②把他的尖镐借给第欧根尼,第欧根尼也把他的灯笼③借给他。有时它们也互相排斥。加尔文④揪住索齐尼⑤的头发。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或中断这一切力量向目标推进的张力和活动,那些活动同时在黑暗中往来起伏,再起,并从下面慢慢改变上面,从里面慢慢改变外面,这是人所未知的大规模的蠕动。社会几乎没有意识到这种给它留下表皮、换掉脏腑的挖掘工作。有多少地下层,便有多少种不同的工程,多少种不同的孔道。从这一切在深处进行的发掘中产生出来的是什么呢?未来。
①基督教在四世纪以前受到罗马帝国的仇视,教徒常被杀害,因而在地下墓道里秘密举行宗教仪式,宣传教义。地下墓道原是废弃了的采矿坑道。罗马人火化尸体,而基督教徒一定要埋葬尸体,废矿道便成了基督教徒的墓地。
②让-雅克是卢梭的名字。尖镐应指他的笔。
③有一次第欧根尼白天提着灯笼在雅典街上走,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
〃我找一个人。〃
④加尔文(Calvin,1509…1564),法国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新教宗派之一……加尔文教的创始人,这一宗派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利益。
⑤索齐尼(Socin,1525…1562),又译苏西努,意大利宗教改革家,倡导〃上帝一位论〃学说。
人们越往下看,所发现的活动者便越是神秘。直到社会哲学还能认识的一级,活动总还是好的,再下去,那种活动便可怕了。到了某一深度,那些洞窟孔道便不再是文明的精神力量能钻得进的,人的呼吸能力的限度已经被超出,魔怪有了开始出现的可能。
这下行梯阶是奇怪的,它的每一级都通到一个哲学可以立足的地下层,在那里,人还可以遇到一个那样的工人,有的是高明的,有的不成人形。在扬·胡斯①的下面有路德②,在路德的下面有笛卡儿,在笛卡儿的下面有伏尔泰,在伏尔泰的下面有孔多塞,在孔多塞的下面有罗伯斯庇尔,在罗伯斯庇尔的下面有马拉,在马拉的下面有巴贝夫③。并且这还没有完。再往下去,朦朦胧胧,在不清晰和看不见之间的分界线上,人们可以望见其他一些现在也许还不存在的人的黑影。昨天的那些是一些鬼物,明天的那些是一些游魂。智慧眼能隐隐约约地见到它们。未来世界的萌芽工作是哲学家的一种景象。
①扬·胡斯(JanHus,约1369…1415),捷克宗教改革的领袖,布拉格大学教授,捷克民族解放运动的鼓吹者,被控为异教徒后被处以死刑。
②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
③巴贝夫(Babeuf,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
一个处于胚胎状态的鬼域里的世界,这是多么离奇的形相!
圣西门、欧文、傅立叶,也都在那里的一些侧坑里。
所有这些地下开路先锋几乎经常认为他们彼此之间是隔绝的,其实不然,有一条他们不知道的神链在他们之间连系着,虽然如此,他们的工作是大不相同的,这一些人的光和另一些人的烈焰形成对比。有的属于天堂,有的属于悲剧。可是,尽管他们各不相似,所有这些工作者,从最高尚的到最阴狠的,从最贤明的到最疯狂的,都有一个共同点:忘我。马拉能象耶稣一样忘我。他们把自己放在一旁,取消自我,绝不考虑自己。他们看见的是本人以外的东西。他们有种目光,这种目光搜寻的是绝对真理。最初的那个有整个天空在他的眼睛里,最末的那个,尽管他是多么莫测高深,在他的眉毛下却也还有那种苍白的太空的光。任何人,不问他是干什么的,只要他有这一特征,便应受到崇敬,这特征是:充满星光的眸子。
充满黑影的眸子是另一种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