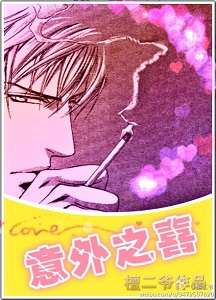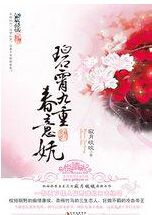虚线的恶意-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除了公视之外的民营电视台,联播的台数成了母台的权力象征,也影响到营业收入。
所谓的联播网,是指有两家以上的电视台同时播出同一个节目。电视节目的制作,不论何种类型,都需要庞大的经费,地方台如果独力制作,风险太高,于是便接收母台的节目,直接在当地播出。
公共电视的优势,就是节目能在全国各地播出,民营电视台为了对抗这个优势,必须尽可能的掌握全国的地方台。过去中央电视台和东洋电视台被称为两大民营电视台,就是因为他们充分运用先发优势,在组织联播网方面领先其他电视台。首都电视台虽然较晚起步,但从八十年代后期,便因大量掌握了全国的UHF(高频率电波)台,地位急速上升。
过去首都电视台周三晚间九点,是传统的连续剧时段。撇开收视率不谈,曾多次赢得艺术节及民间播映联盟奖等奖项,甚至在两年前就预约了大牌编剧家的剧本,夸耀这个节目的水准。然而,轻薄短小的趋势也影响到连续剧,节目的价值变得完全以数字来衡量。当连续剧的平均收视率降至12%以下时,当时的后制部经理便向董事长提出改革的建议。
根据资料,周三晚间父亲在家的比率较高,于是一九八六年起便废除传统的连续剧,开始推出新的报导性节目。那就是“Nine to Ten”。
长年从事战地报导的老资格特派员长m文雄,被拔擢为节目主播,而和长m个人特色一致,标榜以游击战术作报导的节目,也得到了社会的肯定。
节目的架构是仿照美国CBS【注】的热门节目“六十分钟”。采用有杂志式之称的制作方式,将数则不同的话题像杂志一般组合起来,并且大量采用现场报导,以增加临场感。这点也是完全从原版学来的。
【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27年成立。总部设在纽约,美国三大商业广播电视公司之一。——欧阳杼注
“Nine to Ten”的成功,多少也应归功于时势。
节目开播数年内,正好发生菲律宾政变、柏林围墙倒塌、昭和天皇去世、波斯湾战争开打等大事。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原来是娱乐媒体的电视,开始被社会肯定为报导媒体。长坂没有错过这种时代趋势,尽量用浅显易懂的言词,配合图表的辅助,解说艰深难懂的新闻内容,让老人与小孩也能理解。
一般人往往以为电视媒体是在八十年代后期才开花结果,事实上,这种趋势在七十年代便已埋下伏笔。
七二年六月,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结束了长达七年又七个月的任期。他在临别记者会上表示:“我讨厌报纸,报纸没有正确传达我说的话,老是加以曲解。我希望透过电视向大家讲话,请报社记者现在离开这里。”
这番发言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在谈判琉球归还问题时,由于外务省机密泄漏,公文被报纸一字不漏的登了出来,所以首相讨厌报纸可说是其来有自。尽管如此,他的发言仍然象征着电视媒体的地位已经凌驾于报纸之上。
这时,美国开始在新闻及纪录片的采访中使用日本制的家用摄录影机。一九七一年,他们又率先采用小型照相机和录影带组合而成的“ENG系统【注】”。日本在一九七五年昭和天皇访美时正式将之引进国内,在不断的改良下,它的轻巧与机动性,使得新闻及连续剧等节目的制作力,产生革命性的进步。
【注】ENG系统(Electron News Gathering),俗称为现场单机采访组。——欧阳杼注
经过七十年代电视媒体的成长期,在动荡的八十年代,以新型报导节目的姿态称霸周三晚间九点的“Nine to Ten”,即使如今节目已播出十一年,仍可平均获得百分之十三到百分之十六的收视率。如果节目时间内发生了劫机事件之类的新闻时,收视率甚至会冲到百分之二十以上。
如果百分之一的收视率可换算为七十万人,关东地区被选为收视率调查的样本家庭,大约是从一千五百万户中,用统计学随机抽样选出的三百户而已。平均五万户取一户的比率是否能代表全体,有些统计学者表示可以,也有学者主张这种统计毫无意义。
另有数据显示,三百个样本,在以分钟为单位的收视率中,会产生±4~5%的误差。要减少±4~5%的误差,只要增加样本数就行了,但这牵涉到收视率调查公司的经营成本,一直难以实现。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广告公司以鞭策电视台的姿态引进了“个人收视率”这种东西。
配合家庭结构,在收视率测定器上加上“爸爸”、“妈妈”、“爷爷”、“小孩”等按键,坐在电视机前的人,在开始看节目与看完时按一下按键即可。这种方式,不是在计算以户为单位的收视率,而是实际了解哪个年龄层的人正在看节目。
这的确是关心商品客层的广告主才想得出的点子,不过这种样本数超过家户收视率一倍以上的调查方式,使得节目审核变得更加严格。一旦这种操纵广告的个人收视率变成主流,可以预期古装时代剧将会逐渐消失,迎合年轻人口味的节目则会日益增加。
这么一来,报导性节目恐怕也将变得更娱乐取向。
个人收视率的引进,以及数位多频道——现在的电视界正处于这两股改革的浪潮中。
“Nine to Ten”的几个单元中,最能提升收视率的就是“事件检证”。由少数精锐组成的特别采访小组,追踪报导当周最热门的事件,然后浓缩成五分钟的特辑。
节目曾针对陷入胶着的杀人事件展开独特的推理,被褒奖为“五分钟推理剧场”;另外,也曾针对工业废弃物处理场的兴建,攻击政府官员涉嫌贪污舞弊;或是在别台发生自导自演丑闻后,对首都电视台做自我检视,为节目塑造出充满战斗性与强硬作风的形象。
这五分钟的影像剪接,就是远藤瑶子的战场。
瑶子将脚踏车停放在电视台内的停车场,锁好车,一边从口袋掏出贴着照片的工作证给警卫看,一边走过他身旁。
平常早班是在上午十点进电视台,剪接十一点半播出的午间新闻。晚班的工作则从傍晚六点的新闻开始,一直要到夜间新闻结束才能下班。隔周休假两天,一个月顶多休息七天。
沿着楼梯走到地下室,先走进寄物间。平常台里随时都有十名剪接师在,其中七成是男性。寄物间旁有一张上下铺的单人床,用帘幕和寄物间隔开,由于这样违反消防安全法,所以对外并不承认这是可以留宿的地方。薄薄的棉被看起来像梅干菜【注】,不知道多久没晒了,且残留着有人睡过的痕迹。房间后面有淋浴设备,但女性过夜时很少使用。
【注】梅干菜是享誉海内外的一种客家乡土菜。秋末冬初,菜园里的芥菜抽了苔,它姆指粗细,顶带花蕾,形如秋萄,脆嫩味甘。经晒软、腌渍、压石、发酵(约1周)、曝晒、发酵、扎成球状、储存 等步骤后,即可食用。——欧阳杼注
瑶子将皮包放进寄物柜锁好,一走进剪接部门,便看到赤松早已坐在剪接设备前,望着今天的采访带的小标题。赤松虽然属于“Nine to Ten”制作小组,但也被派来跟瑶子搭档制作午间新闻。
“远藤小姐早。” 棒槌学堂·E书小组
“早。”瑶子在老位子坐下,开始看母带的标题。
那是某政治团体集资后用途不明的疑案。在现场记者的指示下,摄影师拍下的市谷区风景,重现在荧幕的扫瞄线上。
如果凝神细看,电视荧幕是由五百二十五条横线切割而成。横线并不是实线,而是由点组成的虚线,这些虚线组合而成的荧幕,很像那种用细线精织而成的图案。
瑶子一边旋转控制钮,快速浏览带子,一边将可以使用的画面记在脑海中。从现场拍回来的影像,第一个观众就是像瑶子这样的影像剪接师。在剪接作业中,头一次接触影像时的感觉比什么都重要。
政治团体要募集资金时,一定会以代表该团体的政治家为号召。观众在直觉上,应该会想先听听那个政治家的解释。
如果是普通的新闻,通常会按时间顺序,先给观众看该团体位于市谷的办公大楼全景,接着是警方执行搜索的画面,然后是在记者的麦克风包围下,政治家愤怒无比的表情,但是瑶子却开门见山的从政治家的怒吼切入。
先从涉案人的辩解开始,再从后面的事件说明中,让观众发现他的辩解有多么虚伪,以加深观众的印象。强调高额利息及保证还本的集资方式,使一对老夫妇上当,将准备养老的存款全数投入。瑶子决定把他们的怒吼声放在一分半钟影像的最后一幕。
“这个老太太的脸部会打上马赛克吗?”
“会。”
“为什么拍摄时不避开她的脸部呢?用马赛克遮住脸,岂不是会让观众觉得被害人好像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这会影响到证词的可信度。”
“听说是拍摄完毕后,她本人才说不可以照出脸。”
瑶子不禁咋舌。但是赤松又不是现场制作,责备他也没有用。
关键的辩解镜头出现了。关于集资来的款项中,有一亿五千万被挪作政治活动费与私人用途的传闻,政治家神情激动的加以否认。
“我要从这段辩解开始,最后的表情会用停格画面,你在那里插入短音。”
短音是一种配乐,用短短的音符作段落的区隔,达到结束前段说明的效果。马赛克处理与配乐之类的琐碎加工,是在办公室后方独立的剪接室进行。
“你看这样好不好?在政治家说到一半时开始融入音乐,在报导最后,咚一声来个结束。”赤松夸张的摆出指挥家的姿态说。
“你要放什么音乐?又是你拿手的‘魔鬼终结者第二集’吗?”
新闻报导也常用电影原声带配音,因为电影原声带常竭尽所能的发挥戏剧化的亢奋感。
“那种没水准的配乐,请你去别的地方搞。”
被瑶子无情的否决,赤松只好噘着嘴说:“遵命。”
瑶子讨厌背景音乐。那不仅会抹杀影像本身的特色,只要选曲一不小心,便会赋予画面与事实偏离的意味。比方说,如果将辩解得口沫横飞的政治家脸部特写,配上充满悬疑气氛的弦乐音效,原本一件单纯的诈欺事件,便会显得人命关天。
“有三个地方要上字幕吧。政治家的名字、团体名称和往来银行的名称。”
“银行的名称好像还不能公开。”
赤松在一旁朗读旁白稿。预设为一分半钟的影像中,主播要读的稿子早就写好了。
“啊,刚才的镜头再让我看一次。”
交互看着小标题与荧幕的赤松,打断瑶子的作业。
“瞥方收押的纸箱底突然破掉……你看,就是这里,警察手忙脚乱。”
散落满地的文件似乎要被风吹跑了,便衣警员连忙四处捡拾。
“这个镜头跟事件有什么关系?”
“是没有,可是你不觉得这个画面流露出警察的人性吗?”
“警察的人性和这个事件又有什么关系?你的意思是,就算跟正题无关,也要用滑稽的镜头吸引观众是吗?我懂了,只要有趣就行了,是吧。”
“你不要说得这么刻薄嘛。”赤松一头热劲顿时冷了下来。
瑶子不理会他,将警察手忙脚乱的镜头快速略过。
“准备好了吧,我要开始剪接了。”
“麻烦你了。”
瑶子将大略看过一遍的影像逐一挑出,加以剪接。赤松将脸伸向前,以几乎碰到瑶子脸颊的距离盯着荧幕。才四月天便穿着夏威夷衫、散发出体温的这个男人,令人有种窒息感。
旁边的剪接机前,年轻的女剪接师在执行制作的指挥下,正在剪接俗称“垫档花絮”的风景区热闹景象。春天的满眼新绿、走在登山道上的一家大小、正在吃饭团的儿童特写……这是剪接新手一定会接到的工作。
就像一旁的年轻女孩一样,瑶子也曾经历过这种把制作人的话句句当作圣旨,一挨骂就眼泪汪汪的时代。
女剪接师几乎毫无例外的会有一个仰慕执行制作的时期,那是因为在深处地下的工作场所中,和制作人像地鼠般挤在一起,比制作人的老婆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还要久的缘故。然而到了某个时候,会突然深刻领悟到“这只是工作上的交往”。在吃尾牙等剪接室之外的场合同席时,会发现制作人男性的一面、家庭生活的一面,而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当女剪接师发现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太多时,便会意识到彼此只是每日并肩看着荧幕影像的同事。
“刚才那个手忙脚乱的镜头,我觉得很好嘛……”
赤松还在嘟哝。幸好不必对这个男人抱持憧憬又遭到幻灭,瑶子觉得轻松多了。
赤松虽然对手下的助理耀武扬威,但对瑶子的态度却大不相同,不但亲自泡咖啡,还常说些“分发到新闻部,在远藤小姐身边学习,一直是我的梦想”之类的奉承话。直到最近,瑶子才渐渐明白,赤松说他祟拜自己,似乎并不是在拍马屁。
那你说说看,我到底有什么魅力?瑶子有时也想这样问他,不过这样相处起来似乎会更有窒息感,所以话到嘴边,还是咽了下去。
“我问你,你大学念什么的?”大致剪接完毕时,瑶子抱着闲聊的心情问道。
“你怎么问起这个?”
瑶子丢给他“只是随便问问而已”的表情。
“日本的新闻节目职员,多半是像我这样通过严格的求职竞争,进入电视台以后,才开始学习做新闻的方法。”
仿佛是想预先堵住瑶子的批评,赤松试着替自己的能力有限辩解。
“如果是在报社,地方记者通常要磨练个四年才能调到总社,但电视台的新人教育简直是速成班。这如果是在美国,可是白热化的激烈竞争,幸好我是生在日本。”
美国电视联播网的从业人员,大多是从大学时代便彻底学习新闻传播,大学毕业后也多半先在地方电视台累积经验。只要有实力,三十岁出头便能挤进大都市的电视台。然而,只有少数人能在竟争中脱颖而出,多数的电视台记者,在三十五岁左右便被强制调往地方电视台。由于在大学受过记者基础教育的人才实在太多,所以电视台可以雇用年轻又廉价的实习记者,然后像卫生纸一样用过即丢。
“你知道‘清除恶意’这句话吗?”
好像是在哪里听过的新闻专业术语。
“美国的大学生,在四年的新闻专业教育中,反复被教导要清除malice,也就是‘恶意’。换句话说,就是要培养能力,去确认记者是否在有意识的恶意中伤或是在潜意识中让画面潜藏恶意。他们从方法论开始,反复训练该如何从言词与影像中清除恶意。”
据说他们常在课程研讨会中讨论报导伦理的问题,像报导评论中使用的副词与形容词,是否含有过度渲染的语句?摄影机是否刻意作某种隐喻?影像剪辑的过程中,是否涉入太多主观看法等。
“你到底想说什么?”瑶子没有停下手边的作业,向赤松问道。
“不,我没别的意思。”
“你是不是想说,你在副教授父女惨死事件报导的体验,若是在美国,人家学生时代早已当作考试题目体验过了,你却在现场出其不意的受到冲击,觉得很窝囊,是不是?〃
“好吧,就算是这样吧。”
“你觉得自己听命于充满恶意的女剪接师,非常可耻。”
“我可没这么说。” 棒槌学堂·E书小组